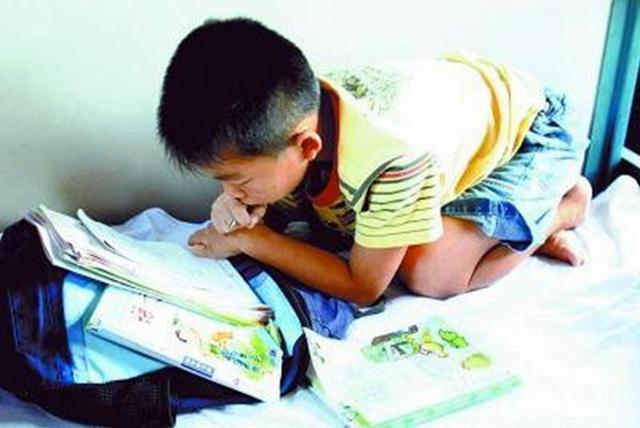不是不是,当然不是!
今天继续转载,各位接着阅读!
看吧,下面这篇,相当精彩,说的是德民兄当年考研的故事。
“这个问题,应该去问‘四人帮’!”
好家伙,对于考官提问,竟敢如此回答!
然而,他还竟然考上了!
这就是当年,李德民的考研!
“这个问题,应该去问‘四人帮’!”
青龙刀 青龙刀笔记

1997年11月17日,人民日报在第五版右上角“恢复高考制度20年回顾”专栏,加框发表文章《难忘那次口试》。全文如下:
难忘那次口试
人民日报评论部 李德民
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创办,招收首批新闻研究生。7月,初试之后取得资格的考生到北京复试。复试有笔试,还有口试。主持对我口试的“考官”是人民日报资深记者白夜、傅真。他们的姓名、身份是事后知道的,当时对考生保密。
“考官”端坐在主席台上,题目装在信封里。我从一摞信封中抽出一个。从毛泽东的新闻思想到斯诺、里德的新闻作品,一一回答。除了规定的试题,“考官”还有提问,学生还得回答:
“你是哪个大学毕业的?”
“我是武汉大学毕业的。”
“学什么专业的?”
“学图书馆专业的。”
“毕业后到哪里工作?”
“在农场劳动。”
“大学毕业怎么到了农场?”
“这个问题,应该去问‘四人帮’!”
回答最后一个问题的态度显然不恭。但话已出口,难以收回,录取与否,听天由命吧!
我1964年考上大学,上了半截,开始“文化大革命”,闹闹哄哄。拖到1968年12月毕业时,大部分学生被送到农场,接受“再教育”。后来,又“再分配”。从1968年到1978年,大学毕业10年后,我才有机会报考研究生。当时,我已34岁,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
复试一个多月后,我收到了录取通知书。到北京后,我知道了考分,其中口试得90分。这是高分。1981年,读完研究生分到人民日报社工作,方知白夜、傅真都是老干部、老报人。傅真早在“七七”事变之前就走上革命道路,今年80岁。白夜前几年去世了。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遭受残酷迫害。
难忘那次口试,难忘两位恩师。
上面即是 《难忘那次口试》。想想有点后怕,主考若非傅、白二位恩师,险!人说性格决定命运,好运或恶运,往往也是碰。“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是啥性格就啥性格吧!别难为自己。
这篇文章是时任人民日报教科文部副主任杨振武编发的,他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他为我留下一段记忆,拂去岁月灰尘,想起考研往事,感慨万端。
考研,是原来想都不敢想的事,连大学本科都没读到头,实际上就是个高中生,考上大学而已。但我要孤注一掷,要赌上一把。
在这个几十人的小厂,月薪52.50元,27斤粮食指标,膝下幼儿嗷嗷待哺,家乡老父水深火热,没年没月,没油没盐,这样熬一辈子?
我爱看报纸,听广播。在三湖农场劳动锻炼时,武大挍友尤竹君回常州探亲时,给我捎回一个半导体小收音机,天天听。后来收音机被农民偷走了。他们以为是贵重物品,其实才三十多块钱。
在郧西县印刷厂当校对员、调度员时,订阅人民日报、湖北日报和郧阳报,主要我看。工人常来拿报纸卷烟叶抽,包馒头带回家。我从人民日报上看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招收新闻研究生的消息,也有同学告知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招研究生的消息。
考北京,还是考武汉?反复掂量,倾向于北京。
为什么?在大学虽说是图书馆专业,其实,今天下乡,明天下厂,接着又是“文革”,没学到什么。对新闻倒是有点兴趣。
在郧西县我见过郧阳报的记者,这是当年见过的最大的记者。看他们气宇轩昂地出入县革委会大门,看他们抱着双臂、叼着香烟同县革委会主任、人武部政委称兄道弟,大方、从容而神气。我意识到,新闻离政治近,离官员近,离权力近。
这种“近”,是我的迫切需要。家父因所谓历史问题蒙不白之冤,受无妄之灾,要解决问题,必须找官。在印刷厂够不着官,即便到图书馆也有相当距离。干新闻吧!
可是,人家凭啥让我干新闻?研究生考得上吗?悬!我有自知之明,至少有三个“硬伤”。
一、不是新闻科班,是图书馆学。
二、不是干新闻的,连县通讯组、广播站、郧阳报都没干过,是印刷厂的调度员、校对员。
三、最要命的是,政审表上,家庭出身栏目中,白纸黑字填着俩字:“地主”。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真如俗话所说:“运气来了,门板都挡不住”,1978不讲出身,上帝开了一扇门。
事情两面看,要懂辩证唯物主义,有“硬伤”,也有强项。
我爱看报纸,听广播,这即新闻。另外,我写文章出手快(在北京复试时,写通讯,两个题,二选一,三个小时,我哗啦啦把两个题目都写了,每题各得90分,拿它180分,当然只能算90分,这是最高分)。中小学时常举行作文比赛,头名多是我的。
考新闻,有信心。但到县教育局报名时又犹豫起来,忐忑不定,患得患失,北京?武汉?武汉?北京?反复权衡……从口袋里摸出一枚硬币,朝天抛,落到地,看看哪面朝上,决定北京或武汉。两次朝上的竟然都是武汉!不对,再抛一次,北京!

感谢印刷厂尚改成厂长,给了我一个月的假期复习功课,感谢县委宣传部王兴华副部长,借我几本新闻方面的书,他在郧阳报工作过。感谢县教育局王萌炳局长,他清出一间最大的办公室,摆五张桌子,四角坐四个考生,我用中间的八仙桌,共5名考生。教育局青年干部刘国瑛监考,给每位考生泡一杯绿茶。山区小县,民风淳朴,重视教育,情深意重。
考前考后我都吹牛,我当然考得上!如果我考不上,中国又有谁能考得上?意在鼓勁,还有点阿Q。有人在等着看笑话,话说得难听。这是激励的动力。
1978年春夏,我家窗台花盆里辣椒火红,西红柿累累。

明天要上考场,今晚听说城关镇大场子里放电影《杨门女将》,豫剧,看看。

好兆头!好轻松!好从容!
郧西县5个考生,只有我一人接到复试通知。感谢邮路畅通,感谢小兄弟石立国拿到社科院复试通知后,及时送给我。我的好朋友、好兄弟,想起当年桩桩往事,德民泪流满面。
接到复试通知后,有一个月的准备时间。这一个月,恶补俄语,到京后方知,复试不考外语。
踏上赴京复试的路程,到武汉转火车北上。在汉江边的硚口军工医院大哥家住一天,大哥陪我在汉江堤上散步,嘱咐注意事项。我要下水游泳,他不准,怕淹死,我说,不游就考不上!下水了,游个够,他在岸上盯住。他忘了,小弟1966年夏曾横渡长江,从武昌司门口下水,到汉口滨江公园上岸,14华里。武大图系6801班仅德民一人。这绝非吹牛。

大嫂看我没件像样的衣服穿,翻箱倒柜找块白“的确凉”布,请裁缝赶制一件白短袖衬衣。口试时,穿的是它。
车到北京站,复试通知写得清楚,搭22路公交车,从哪上,到哪下,但我奢侈,一出火车站,雇辆三轮车,让他送到北师大。
当年北京踩三轮的“祥子”比今天的“的哥”态度好得多。一路没话,我跷着二郎腿坐在三轮车上看北京街景,并不繁华,但帝都气象,心向往之。
送到北师大,车费两块钱。
考生安排到腾空的大教室住宿,一个教室大概住二三十人,一人一块铺板,一张草蓆,一条被单,一个枕头,吃学生食堂,白面馒头玉米面粥和咸菜。讨厌的是,没地方洗澡,而我汗多,不洗澡就没法睡觉。没办法,只有深夜蹲在公共卫生间四方水泥池里,打开水龙头冲个痛快。北京是地下水,刺骨冷。我家有哮喘家族病史,冲水冲病了。
复试结束后,我把提包放在铺板上,抱病从北京乘火车到宣化纸厂买纸,对方摇摇头,我说声再见,转身到宣化火车站,当天返京,到北师大提包回郧西县。
这是印刷厂会计员万绍南大哥对我的照顾,赴京复试给个宣化买纸的出差机会,省几十块钱,连一分钱住宿费都没花,白住北师大。他知我穷,几十块钱是大负担。
朋友是天,是地,人不能没朋友。
参加复试的“铺板兄弟”淘汰了一大半。当年10月入校后,听北京考生说,他们住在家里,不受北师大那份罪。谁叫咱北京没家呢?我知足,北师大。
回想北京复试,难忘傅真、白夜两位恩师,也难忘丁浪女士,她是人民日报文艺部名编辑,面试时做文秘工作。丁老师2021年夏初逝世,享年89岁。还有在考场监考和发试卷的谭力老师、沈文英老师,早已逝世。42年过去,他们永在德民心里,到天堂,我鞠躬。
1978年10月,我刚住进中国杜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宿舍,滿面春风、气宇轩昂的周扬等领导到我们宿舍看望学生,穿一身剪裁合体的银灰色中山装,他是社科院领导。
他问我:“你大学学什么专业?”我答:“图书馆专业。”他自言自语地说:“图书馆……也到新闻了……”我心里想反问一句:“您是黑线人物,怎么又红了?”但话没出口,沉默之,已经来了,退不回去了。
这次对话,周没给我留下好印象,想起鲁迅骂的四条汉子。
不写了,写不下去了,德民欣逢那个春风扑面的时代,幸遇那么多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