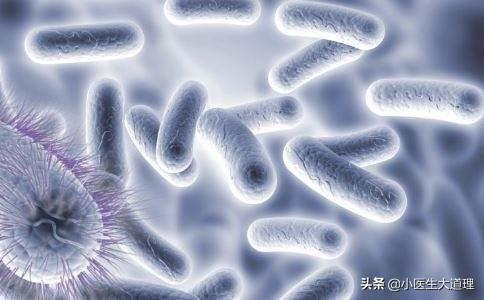嬉皮精神从未在时尚T台上缺席过,要说变化,那便是从单纯的反抗进阶为单纯的我行我素。
记者/杨聃
嬉皮士的爱车停产了
不久前大众宣布明年停止生产标志性车型甲壳虫,一时间引发了大批“回忆杀”。我一直想开辆甲壳虫,像伍迪·艾伦在自导自演的电影《傻瓜大闹科学城》(Sleeper,1973)里饰演的米勒斯·门罗那样“误打误撞”开启一段旅途。这款如同树蛙一般造型的小巧汽车,在有些人看来是文艺青年的标配,有些人认为它是叛逆精神的代表。
当阿道夫·希特勒委托费迪南德·保时捷在20世纪30年代设计甲壳虫时,本打算让所有的雅利安家庭都能拥有,其低廉的价格在当时相当于一辆摩托车,没想到德国民众没有买账。在事与愿违了几十年之后,甲壳虫成了与可口可乐相当的全球商品。它的成功不全靠“性价比”,还取决于对不同文化想象力的捕捉。在德国,它代表了战后的“经济奇迹”,并帮助推进了欧洲的全民汽车时代到来;在墨西哥以及整个拉丁美洲,它象征着经济动荡下所必需的坚强韧性。难怪荷兰莱顿大学的欧洲史教授伯恩哈德·列赫尔(Bernhard Rieger)用了400多页的一整本书《人民的汽车》,从文化的角度来讲述这款单一车型。
20世纪一款汽车的流行自然离不开其最大市场——美国,要知道60年代美国市场的汽车销量占世界总销量的48%。他们普遍喜欢体型宽大、线条凌厉的款式,就像不断加长加宽的福特野马那样,这与体型小、车身圆润的甲壳虫所呈现的完全相反。从1949到1963年,甲壳虫几乎看不出外形上的变化,大众的广告中甚至还标榜了它在设计上的一致性。如果没有那条幽默的广告标语“往小了想”(Think Small),甲壳虫在美国市场的表现恐怕要以惨淡收场。
纽约一家小广告公司DDB为了节约成本,用黑白印刷广告来呈现甲壳虫,本该用浓墨重彩渲染的车身形象几乎只占了不到十二分之一的版面,其余空间通通留白。这跟其他同期颜色鲜艳、排版丰富的汽车广告相比南辕北辙。当它恰到好处地出现在挤不进小车位,以及加油把钱包掏光了的窘境时,却显得实用极了。美剧《广告狂人》第一季中就有追溯“往小了想”的桥段,身为创意总监的唐·德雷柏(Don Draper)和同事们讨论甲壳虫的新广告时,有人说印刷品上车子小得连样子都看不清。这则广告界的经典案例不仅位列20世纪最佳策划,还将广告创意引入了全新的方向。
与此同时,甲壳虫在60年代还撞上了免费的宣传机会——嬉皮士运动。经济适用的甲壳虫满足了他们“在路上”的需求,与福特雷鸟不同的是,青少年只需要在暑期勤奋一点就有能力攒一辆。1967年“爱之夏”,十多万人涌入旧金山海特-阿什伯里区。像《San Francisco》歌词中描绘的那样,无论男女都披散着头发,头上别着鲜花。他们或赤脚游荡在街头,或躺在金门公园的草地上聊天,街道与陌生人家的地板即是他们的住所。摇滚歌手无时不在免费献唱,人们吸食着大麻,自由地恋爱,甲壳虫也点缀其中。
一年后的沃尔夫斯堡,工厂每年要生产100万辆甲壳虫。迪士尼也推出了不少甲壳虫主题的电影:《The Love Bug》《Herbie Collection》等。据统计,1970年大众在美国出售的近57万辆甲壳虫有80%都被嬉皮士画上了多彩图案。对于伍德斯托克那一代质疑主流文化、叛逆、追求自由的年轻人来说,驾驶造型不依惯例的甲壳虫或者它的表兄——大众小巴T2,是对美国汽车制造商所推崇的大型“汽油贪吃鬼”家庭雪佛兰的一种抗议。80年代,孩之宝(Hasbro)拍出了系列玩具动画片《变形金刚》,其中的重要角色大黄蜂可以变形为甲壳虫。然而,在迈克尔·贝的电影版拍摄时因大众拒绝合作,大黄蜂换成了如今的雪佛兰。
甲壳虫在80年的历史中起起落落,其销量曾超越福特T型车,成为第一款达到2000万销量的车型,当然,这也不是它第一次面临停产。两次石油危机之后日本小型轿车的受欢迎程度陡增,导致大众在1978年宣布德国工厂停产甲壳虫。不过第一代甲壳虫并没有在全球范围下线,直到2003年仍在墨西哥和巴西表现不错。2011年,第三代甲壳虫的设计更现代了,可外形却抛弃了可爱的圆弧风格,市场活力比1998年推出的二代(也被称为“披着甲壳虫外衣的高尔夫”)还差。《纽约时报》认为此次甲壳虫停产也与其六七十年代的拥趸淡出主流消费市场有所关联,即便大众官方表示,不排除将来重新启用甲壳虫车型的可能,毕竟流行趋势总是周而复始,但仍然让人不禁发问,嬉皮士风格式微了么?
=====================$$$=========$$$=========$$$=====================
不只有爱与和平,还有Sleazecore
从“垮掉的一代”演化而来的嬉皮士对非传统的生活方式比时装更感兴趣,他们开车到阿富汗和印度,转向东方国家寻求启迪,一路上顺带吸收了佛教等教义,譬如《摩珂迦罗颂》。如此不可避免地产生一种从异族获得灵感的装束,包括五颜六色的阿富汗外套、寓意“爱与和平的权利”的印花图案及象征物。除此之外,对资本主义商业化社会的反叛在嬉皮士中掀起了DIY风潮,他们讨厌规模生产的商品,喜欢用扎染和牛仔上的刺绣显示个性。他们不在服装上区分性别,女人不穿文胸等表现都能看出其对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趣已然增加。流行音乐明星如吉米·亨德里克斯、鲍勃·迪伦和贾尼斯·乔普林都对嬉皮士的生活方式“尽过一份力”,他们穿着紧身丝绒长裤,在吸食LSD腾云驾雾时获得灵感。
在与“爱之夏”几乎同期的大洋彼岸,“I Was Lord Kitchener's Valet”和“Granny takes a trip”等嬉皮士服装店在伦敦迅速发展起来。相比之下,英国嬉皮士有型得多,并最终出现了西亚·波特这样可以定义嬉皮士风格的设计师。美国学者埃尔伯特·古德曼认为,英国的嬉皮士是典型的花花公子。他们着迷于微小的服装细节,就像汤姆·沃尔夫笔下吹毛求疵的纽约律师,其特色表现在衬衫的领角上和定制的夹克开叉上。
嬉皮士带一点东方哲学、诗歌、摇滚乐和迷幻剂混合的新时装风格持续了20多年。Gucci设计的大胆印花至今仍值得收藏,同样是波西米亚的拥护者的还有之后的安娜苏。事实上,嬉皮士风格从未在时尚中缺席过,干酪包布、土耳其长袍、喇叭长裤、鹿皮绒和流苏不断在T台回潮。Gucci 2016年的早秋系列在时尚总监亚历山德罗·米歇尔(Alessandro Michele)花哨明媚的复古偏好下,让花草鸟虫重新绽放在喇叭裤上。这份有力的号召与蜂拥而至的刺绣热潮弥漫在了街头风格的运动球鞋上。
去年,曼哈顿艺术与设计博物馆举办的展览“反主流文化下的手工服装”,对嬉皮士在黄金年代里如何用服饰表达和构建自我做了一番探索。展品包括卡斯·埃利奥特(Cass Elliot)在Mamas & the Papas乐队期间的演出服,民谣歌手约翰·塞巴斯蒂安(John Sebastian)穿去伍德斯托克的装扮,以及那些“出生普通”但“达到设计高度”的设计师们的手工定制服装。策展人迈克尔·瑟普莱斯(Michael Cepress)希望通过展示过去16年来出于兴趣收集的衣服和配饰,讲述嬉皮士们如何用灵修“审视内心”,用音乐和大型集会表达政治立场,用释放天性的集体生活与世俗保持距离。“不幸的是,它仍然能和当下所面临的问题产生共鸣。”艺术与设计博物馆助理馆长评论道。
最近牛津词典收录了一个潮流新词Sleazecore,自2014年的Normcore简约休闲风之后,时尚界对这股用形容词加core的造词方式乐此不疲,去年的Gorpcore甚至被列入2017年的“年度词汇”候选。Sleazecore顾名思义为邋遢(Sleazy)风,其引领者是贾斯汀·比伯。具体是怎样一种风格呢?油头出街,帽衫裹体,裤脚拖在地上……总之看起来像校园毒贩、街边毛贼就对了。《华尔街日报》对此表示不解,现如今的男性时尚为何游走在宽松肥大和邋遢凌乱之间?巴黎T台上,Margiela的鞋子看上去像被卡车碾压后又重新用胶水粘起来的感觉;Prada、Vetemonts等品牌的高级成衣发布会上也有不少Sleazecore的单品,放眼望去或是些对比强烈的颜色,或是些看起来不该出现在一起的图案组合。
《亚文化:风格的意义》的作者迪克·赫伯迪格认为,“垮掉的一代”和嬉皮士都喜欢表达与贫穷的神秘关系,前者故意衣衫褴褛,后者的欧陆服饰具体表现了街头巷尾的黑人们的传统抱负。他们的风格表象归根结底来自于一系列复杂的认同和对主流文化的反抗。如此说来Sleazecore何尝不是嬉皮风的进阶版本,从单纯的反抗变成了单纯的我行我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