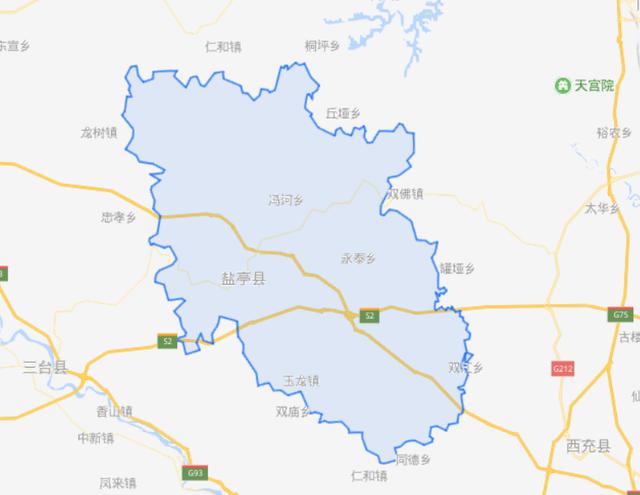文/班布尔汗
对中国人来说,元朝是一个奇异的存在。在学术界,元史可算是各断代史中被研究得最为透彻全面的,大师辈出,名著充栋,用纤毫无余来形容都不过分。但学术与民间的隔阂,使得元朝在民间总是一种大而化之、模糊不清的印象,各种传说误解多如牛毛。不论是早已有之的“人分四等”“九儒十丐”“十户用一把菜刀”,还是网络文学兴起后产生的“初夜权”“摔头胎”等等,都将之描绘成一个黑暗压抑的恐怖时代。
近年来,随着美国学者杰克·威泽弗德的《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日本学者杉山正明的《忽必烈的挑战》等书的热销,元朝又被他们描绘成一个大有现代化风格、有着全球化思维、缔造了全球化商业网络的时代。
也许,黑暗也好,全球化也罢,都是人们有着一个先入为主概念,将元朝视之为一个特殊的时代。而因为视之“特殊”,便总是会寻找、描述乃至放大其特殊。似乎这个由游牧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的另类,对其在中国历史上该处于什么样的位置而予以忽略,于前无继,于后无续,异军突起,又迅速消失于历史中。
历史是复杂的、立体的、丰富的,有着不同的面向和层次。用“特殊”来看待一个时代,貌似深刻,实则有些偷懒。我其实还是希望能够有一个简单、清晰、黑白分明的答案。这会让自己有一种看清一切的自信,可实际上除了“特殊”的噱头之外,并无所得。看元朝,便要先放下这“特殊”,用平和的心态去看待,去了解其复杂,才能不吹不黑,得到些真东西。
前所未有局面下进行各种调试元朝政策多变、皇位更迭频繁、施政宽纵怠惰这些缺点,与社会环境宽松、文化多元开放、商业繁荣、宗教自由等优点,都来自于元朝处在一个“调试时代”,其盛其衰,其成其败,其兴其亡,均是在前所未有的局面下进行各种调试的结果。统治地域囊括前代未能达到的区域,内部多种文化并存,中原帝制与草原封建的传统都要顾及,因此需要杂糅各法,元朝的所谓行汉法和维持漠北旧制的矛盾,其根源即在于此。“人分四等”这样的误解,便是在这调试时代所遗留的问题。

这种调试时代,在历史上不乏先例。例如人们通常将“秦皇汉武”并称,而两位帝王之间的时代便是调试时代。秦始皇统一六国,结束了延续近千年的封建,而代之以集权皇权,将周制变为秦制,何尝不是空前的大变局,即使以当时已知世界各文明相比,都算得极为特殊了。可这步子迈得太大,并不能短时间内完成。秦朝二世而亡,汉朝继起,虽然要坚持集权皇权,但也不得不有所倒退,还是要保留封建。最后使得封建再不足以合理合情地威胁集权,则是汉武帝时代最终完成。
而另外并称的“唐宗宋祖”,唐太宗大兴科举,是将选官的权力完全收归皇帝,而不再如之前那样,皇帝只有任命权,察举权却在世族。毕竟世族尚未完全衰落,唐朝的科举并未完全实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的设想,世族仍能很大程度把持官僚体系。直到宋朝,经过黄巢之乱与五代十国,世族彻底衰落,宋太祖及其子孙才真正用科举做到选官任官皆出自皇帝。
至于在最终完成之前,调试时代总免不了混乱。秦朝短命而亡;汉初异姓王之乱、七国之乱便是封建走向集权的代价;而唐朝科举难以真正公平,关陇、山东、江南亲疏有别,乃至藩镇之乱、宦官乱政,也都不能不说是世族走向衰落,皇权进一步加强过程中的代价。元朝也如秦、唐一般,在调试中摸索前行,最终带着调试未能完成的遗憾而崩溃。后来者汲取其经验,完成了调试。它其实并不特殊,只是历史走到一个阶段时必经的过程。
种种误解和溢美这本《细读元朝一百六十年》便是无视元朝的特殊,将之作为与其他朝代一样,既有其特色,又有着历史传承的朝代来撰写的作品。在将其历史掰开揉碎呈现给读者的同时,把曾经的种种误解和溢美都予以澄清。
人们会看到,被神化的蒙古铁骑,并非是亘古未有的天降神兵。其耀眼的战力与战绩,是结合着草原民族的特点、超强的组织手段和大力吸收历史与其他民族文明成果,才锻造出来的。若非所有人被完全动员起来成为这架军事机器的一部分,全力为战争服务,蒙古人的便携式给养方式,以及快速机动的作战方式,最多只能自保,要想冲出草原去征服世界是完全不可能的。
一生灭国无数,缔造战神传说的成吉思汗,也有着众多无奈和妥协。他虽是自己缔造的国家的最高统治者,须臾间可决定千万人的生死,但因为传统的力量,“形式上权力和帝国归于一人,即归于被推举为汗的人,然而实际上所有的儿子、孙子、叔伯,都分享权力和财富”,而这些无奈和妥协也决定了蒙古帝国与元朝的命运。
面对祖先的帝国不可避免的分裂,忽必烈看似继承,实则开创,变蒙古帝国为元皇朝,“定官制,立纪纲”,“留意治道,固属开国英主”。但在其煌煌威仪,赫赫武功之后,也有着无力感,因为他和他的子孙算得走一步看一步,并无现成的治国方法一劳永逸。从他开始,元朝便在蒙古法、回回法与汉法之间进行调和,以适应空前的大一统形式。调试意味着动与乱,而动与乱之间有巨大的自由空间。
历朝历代都重农抑商的政策被改变,元人对经商趋之若鹜,“工商淫侈,游手众多,驱垄亩之业,就市井之末”。不但“小民争相慕效,以牙侩为业”,原本对商业嗤之以鼻的士大夫,也认为“胸蟠万卷不疗饥,孰谓工商为末艺”,大加赞赏从事商业,认为是具有“仁、智、勇、断”的“四德”的事业。南人北上经商,北人南下行贾,乃至出国经商航行万里,人口流动频繁,规模巨大,朝廷对社会的管控就形同虚设。以至于推翻元朝的朱元璋,评价元朝之亡,认为“其失在于纵驰”,所谓纵驰,就是管控不善。
人们会了解,元朝尊孔重儒,在孔子原有的“至圣文宣王”之上加“大成”二字,使孔子在中国历史上达到至尊至圣的地位。历代儒门先贤都被赐以封号——“加封孔子父齐国公叔梁纥为启圣王,母鲁国太夫人颜氏为启圣王夫人,颜子兗国复圣公,曾子郕国宗圣公,子思沂国述圣公,孟子邹国亚圣公,河南伯程颢豫国公,伊阳伯程颐洛国公。”
程朱理学被定为官方意识形态。“明经内四书五经以程氏、朱晦庵批注为主,是格物致知修己治人之学。”至于讲授儒学的书院,“上凌宋,下躐明。宋以下一千年来之书院林立,惟元最盛,莫与伦比”。
与此同时,科举却不兴盛,读书人大多哀叹“空岩外,老了栋梁材”,以至于后世有人坚信元朝“八娼九儒十丐”。儒士地位很低,这其中的矛盾与原因究竟何在?大量文人从象牙塔走出,在市井中寻找自己的出路。继唐诗、宋词之后,中国进入了更自然、更接地气的元曲时代。王国维先生评价元曲的特色,曾说:“元曲之佳处何在?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 为什么“最自然”?因为那时是文人最“没人管”的时代,不仅是现实中用官爵名利来进行“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的管理,就是在思想上也化解了不少“治国平天下”的自我期许,于是便彻底“自然”了。
摒弃看似复杂实则将历史简单化的心理人们会知道,在那个时代,君王和将军们金戈铁马、开疆扩土确是舞台主角。但在主角周围还有更多人物,甚至比主角更为传奇,留下的影响更为深远。以古稀之龄万里西行,与成吉思汗留下“一言止杀”佳话的长春真人丘处机;将禅宗带入蒙古,并将自己弟子留给蒙古皇室,使之成为一代名臣的印简海云法师;将少林寺修建到漠北草原,死后被尊为国公的雪庭福裕禅师;将藏传佛教东传,并使得徒子徒孙都成为大元帝师的萨迦班智达;来自意大利,在元朝成为中国第一个天主教总主教的孟高维诺;在印度、波斯、元朝、高丽之间折冲樽俎,掌控海商的传奇豪商孛哈里;以一己之力两次远航,途经二百多地区与国家,直达非洲东海岸,并留下详细记录的儒生旅行家汪大渊,还有“曲圣”关汉卿、色目大诗人萨都剌等等人物,让那个时代精彩纷呈。
人们更会发现,一些似乎不是问题的问题,其实也远不是那么简单。蒙古帝国和元朝的关系究竟如何?究竟元朝的时间该如何计算?元朝的疆域是否空前绝后?是否真的可以超越之前的汉唐和后来的清?元朝的人口到底有多少?是否真的是高峰后的低谷,没能恢复到前代的水平?元朝征日本与安南失败,真的是因为“神风”和热带雨林气候吗?现代蒙古人天天离不了的蒙古奶茶,是从元朝就开始喝的吗?也许看完本书,读者会有原来如此的感叹。
当然,读史不是为了猎奇,一本不吹不黑的元史作品也并非执着于“翻案”与“澄清”。我所希望的,是读者能够通过这本书摒弃那种看似复杂实则将历史简单化的心理,看到一个曾经真实存在、有特色而并无所谓“特殊”的时代。这个时代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继承了前人的成果与错误,也将新的成果和失误留给了后人。
今天的我们,不得不承受历史留下的负担,也顺理成章享受着历史留下的果实。那我们回望历史时,就如爬上山坡的时刻回望曾经的路,看清坎坷,看清坦途,领略风景,然后才有真的自信走向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