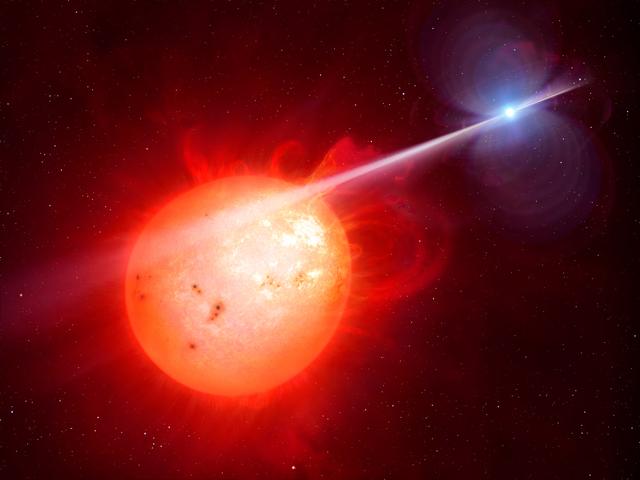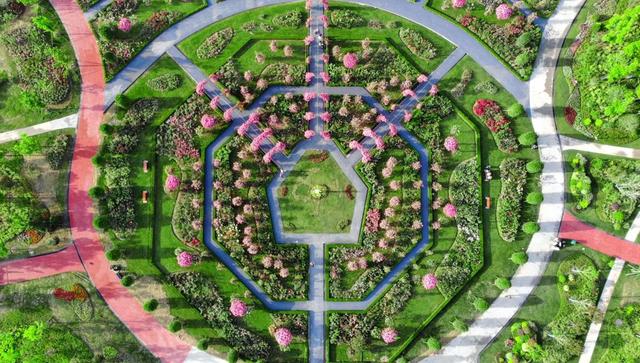上个世纪80年代中卫北大街
陈老师
马号西巷有一个高大的砖雕街门楼子,顶如庙脊,两边马头墙上镶着长方形的松竹砖雕,周边配有已字花装饰,十分气派。厚重的大门色暗结实,门扇中间的金属兽头锈迹斑斑,仿佛撕咬野物后留下的血迹,有些瘆人,表明门前冷落鞍马稀。大门后面五六米处,有一个砖雕影壁,雕着一个大大的福字,四周云纹配置,有八只蝙蝠飞向中心,显示出曾经的富贵。
影壁西边有个小门通向正院,堂屋坐南向北,屋顶为砖瓦建的磙脊形,门窗都是木雕格子,还有几幅镶嵌花草。屋基高出院面三级台阶,屋里供奉着先祖牌位。院中厢房有走廓相连,门窗也都有鱼虫装饰,精细考究,虽然颜色已旧,但不失原建时的雅致。院子地面用青砖铺成,西北角地漏被一块雕成通宝钱形的石板覆盖。这是一座“藏在深闺人未识”的豪华四合院。影壁东边,也有小门通往东院,那边是库房、厨房、长工房、农具房、圈棚等等。
这家主人姓陈,曾在县城应理男校教过书,人们尊称他为陈老师,年约五十多岁,黑脸黄牙,眼睛迷离,似未睡醒。干柴枯柳般的身体撑不展他灰旧的长袍,微风吹过,衣服便被揭了起来。学校知晓他是瘾君子后,便以“师者,传道、受业、解惑也”为由,解聘了他。
据说陈家先祖从耕读走上官路,清朝时兴旺发达盖起了院子。选址的阴阳抬轿子:“你家离文庙不过数丈,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子孙一定会继续沿着‘耕读持家久,诗书继世长’发展下去”。然而世事难料,陈氏家族人丁不旺,到陈老师这代时,他竟成了百亩田中的一棵独苗,溺爱造就他与鸦片为伍,于是卖地、卖家具、卖首饰等等。尤其老婆死后,他在乡下教书的钱换不回几个烟泡。后来人们在北巷不见了他的身影,原来是他把房子卖给了中宁县的大户魏雨三。正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这是中国封建时代家族兴衰的基本规律,概莫能外。
无能最是穷秀才。一管烟枪吸尽了万贯家产后,他完全丧失了师道尊严,见人就伸手,以致亲友、熟人、曾经的学生见了都躲,实在到了“无颜再见江东父老”的地步。
黄河之水天上来。三百多米宽的一河水,向新墩玛头冲来,被青石砌成的巨大稳固的码头顶堵后,流急浪高地向东南方向流去,它侧后的洄水湾有两个蓝球场般大小,其中最大的一个漩涡比牛车轱辘还大,但凡被漩进去的树木枝干,便不见了踪影。陈老师曾在新墩和炭场子两所学校教过几年书,深知“近山辨鸟音,近水知水性”,也见过河面飘过的尸体。中卫有句俗语:“炭沫子是四块石头夹一块肉,埋了没死;排子匠是黄河没盖,死了没埋。”人到绝望之时,只求速速一死。于是便眼晴一闭,纵身一跳,想在新墩码头的激流中鸣呼哀哉,以了结屈辱的一生。
命运与他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他枯枝败叶的身体,如朽木般在洄水湾漂浮而不沉底。河边人发现后,架排子把他救起。小城消息传播快,人们的评论不少:“人死了是个解脱,他虽没死,可今后怎么活啊!”恨铁不成钢的人说:“这样的败家子该死!”善良人说:“龙王爷不要,怕他教坏了龙子龙孙呢。”戏谑的人说:“瓦罐不离井口破。陈老师还是被烟枪击毙了。这虽是他走上的家破人亡的毁灭之路,但给为人师表的崇高职业,带来了巨大损害,也给文化古县蒙了羞,教训是何等深刻啊!”
绣楼
站在鼓楼上鸟瞰城北,各家的四合院一色土黄,堂屋高出厢房,呈磙脊状,恰似黄河波浪,向南滚滚而动。高庙如乾隆下江南的多层楼船;文庙的藏书楼兀立如海上仙山;山陕会馆及戏楼,在绿树掩映中犹如孤岛;近处一家的二层木楼,似一叶扁舟,随波逐流。这在视野中,却是独一无二的。
北巷中有一水井,在小楼东五六米处的墙外,它是北巷几十户人家的生命之水,但凡如淘井砌护井台等大事,都由大家商议,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都能尽快地完成修整,毫不影响人们的生活。邻里关系的和谐,表现了古城人“温良恭俭让”的深厚文化内涵。
这家人的大门向东开在小巷内,虽不很显赫,但长方形的院内却有约二十间屋子,且都有走廊相通。堂屋顶上便是那个有三大间的二层木楼。据老年人讲,这家的祖先曾经发达过,木楼先是主人的书房,后来让给女儿做了绣房。那时我们几个小伙伴充满想象,竟用王宝钏和薛平贵的故事来相比,只觉得这家不如秦腔《三击掌》和小说《薛平贵征西》中,丞相府的豪华。木楼上看不见小巷的行人,下面又有水井,怎么能抛绣球给心上人呢?后来随着女儿的出嫁,男主人的去世,此楼的风光不再。楼柱已歪,门窗变形,楼顶的砖瓦也在风雨飘摇中,有的已经掉落,成了危楼。一家大户变成了三家小生意人。可谓大树一倒,枝叶飘零。
据老年人讲,北巷有一户“官家”,大门近似牌楼,高大威武,气势雄浑。砖石雕花的二门里边是院子套院子,房子连房子的深宅,富丽堂皇,神秘莫测。后因随着清政府的衰亡,加之子孙不思进取,骄奢淫逸而败落,大门和房子被拆卖得七零八落,只剩下几间摇摇欲坠的破屋。但凡值钱的木料门窗都卖了,就连屋顶的瓦,墙上的长砖,台阶上的条石,院子里的方砖也全都撬开卖了。秦腔有出折子戏叫《周三掰砖》的台词说:“一辈子当官,十辈子掰砖。”这是对封建官僚的强烈诅咒。后来这家门口,只剩散放着几块破损得没人要的大石头,在诉说着历史的沧桑。真格是: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
说书
人中卫的文化底蕴,在于兼收并蓄地不断发展。
20世纪40年代,有同学说,剧院广场上新来的说书人很有水平,讲得生动有趣,众口称赞。我这个好奇少年竟成了书场的常客。
一个旧方桌上,放着一个惊堂木,一把折扇,算是道具。桌后坐着一个四五十岁的男人。国字脸,长发齐耳,中分两半。面色灰黑,牙齿锈黄,唇薄口大嗓音沙哑,额头宽阔,微有亮色,眼珠黑白分明,像是个有知识的人。
桌前十步远处,有七八个旧长凳,围成半圆形的空场子,凳上坐着穿戴较为整齐的半大老头,后边站着几排中青年人,个个聚精会神伸着脖子,像是春秋季节龙宫湖边的长脖雁。
他讲《三国演义》时,先来一个亮相:双手抹脸三次,似乎表现面如红枣,右手向外一伸,用扇子做柱状,像是并立青龙偃月刀。眼睛向下微闭,左手一捋长须,活脱脱关云长再世;讲《岳飞传》时,做一个撩衣露背,双膝似跪的动作,宛如岳母刺字——精忠报国;讲《水浒传》时,把旧袍长摆搭肩,双手抱扇,两眼圆睁,弯腰弓背,恰如倒拔杨柳;讲侠客义士之时,他把腰带扎紧,突然做个向上一窜的动作,要飞檐走壁了……
他以说评书为主,有时还唱几句秦腔、眉户、道情、小调以助兴,无不绘影绘声,引人入胜。
每每讲到紧要处,他双手握扇,似长矛直刺对方盔甲上的护心镜,并发出嘶的一声,正当人们忘情地以为有一将帅倒地时,他却把惊堂木一拍,稍停片刻才说:“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他拿起桌上的旧氈帽,翻过来走向听众:赏光、赏光。坐在前排的人纷纷掏钱,后排的人也有给钱的,有的人借故走开。
收完钱后,他坐下来边喝水,边和熟人说几句话,随后扇子一展,惊堂木一拍,三步走向场中开始表演:“话说一枪刺出,还没等近人之身,突然当啷一声巨响,大刀已将长矛拨开,两位将军你来我往,马蹄声嗒嗒嗒响个不停,尘土飞扬,战鼓咚咚,士兵喊声震天……”激烈的混战被他演绎的惟妙惟肖。
艺术的感染力,在于艺术家对社会生活的深刻认识与细节的具体真实的描述,使青少年受到教育。据说有的同学约几个好友,曾到高庙的关公铜像前学“桃园三结义”。有的说:“如果日本鬼子不投降,我也会像岳飞那样去反侵略”。还有的说:“我要学武术,长大了打报不平,杀富济贫。”更多的同学每年正月十五闹元宵时,县城西大街塑有奸臣秦桧的土坯像,腹中砌空,填满下河沿的烟炭,点燃后奸臣的眼、口、耳中向外冒火,叫做“火烧秦桧”。许多人向他吐口水,小孩子用石子土块打他,以示愤恨。数百年来,中卫百姓的忠奸观念十分分明,这也是文化古县的地方文化特色之一。
说书人姓高,名玉山,陕西口音,俗名叫高家氓娃子。借住在北巷那个“官家”破败大院里,两小间透风露雨的小房是他和老婆的家。大人们说,他挣的钱全从烟枪里冒跑了。
同学不理解:评书中英雄的高大伟岸的气象哪里去了?躺在破炕上,吸鸦片烟时,像个干枯的虾米龟缩着,面目丑陋,惨不忍睹,为什么?
人性两重天,吸毒害死人。
一九五O年国家禁鸦片烟,高玉山新生,评书成为中卫的一张文化名片,他被尊为民间艺人。
马号
唐朝时吐蕃东扩,一度切断了丝绸之路的南北道(即从长安过甘肃中部到达武威)于是萧关西域道(东道)应运而生。它由长安出发,过陇山(宁夏六盘山)到萧关(唐时萧关已由固原东南,北迁至海原的李旺堡),谓之萧关道。再向北偏东到达灵州(今吴忠市区)、再由灵州到凉州(今甘肃武威市),名曰灵州西域道(北道)。而中卫正是这条丝路上的重要驿站。驿站是古代传递京城到地方消息和接待往来官员的地方,“以供过客,而不受其报”,因此圈养一些马匹以供使用。为了管理方便,将马匹及圈棚编号,即为马号。清末民初,随着清朝倒台和电报的推广,驿站逐渐退出历史舞台。马号被拆除后变成了空场子,但名称还是被保留了下来。它离北巷不足百米,人们便利用其地开设早市,交易民间的生产、生活物资及熟食早点等杂品。
古城早市有个特点,即天蒙蒙亮开市,太阳一树高散市,人们称为露水集。因它不误农耕,所以赶集的人头攒动,比肩接踵。一位老人给我讲了一个发生在马号的故事,虽经半个多世纪的风雨沉淀,但却还历历在目:
有天早市上,一个全身戴孝的青年被打得口鼻流血,染红了一片孝衣,宛若雪地红花,令人心疼。青年人气盛,紧握拳头,冲上去要讲理。老人怕他吃大亏,拉住低声告诫:“现在的社会,哪儿有理可讲。先不要惹这个瘟神,家里的急事还等着你回去办呢。”
再看那个打人的家伙,高个子,长吊脸,头戴礼帽,架着眼镜,身穿黑色长袍,右手持文明棍,凶神恶煞地说:“我不但要打你,还能抓你坐班房,为什么你家死了人不交人头税?”天哪!国民党真的成了“刮民党”,难怪有对联说:“自古税多如牛毛,而今只有屁无捐”。
刘善人打圆场:“这个年轻人不懂事,看他焦急的样子,像是赶快买点东西去发丧呢。”说完让年轻人交钱免灾。他无奈掏出沾有鲜血的钱,这本是对野蛮无人性的控诉,然而不知廉耻的打人者却嫌不够,要让他再掏再借。年轻人说:“我实在没有了,县城又没亲威。”宋居士代他求情:“他已没钱发丧老人了,饶了他吧,阿弥陀佛。”
你道打人的是谁?他就是中卫的税务官,因脾气暴躁,仗势欺人,常踢人打耳光,所以有人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辛家驴蹄子。恶有恶报,解放后被人民政府镇压,古城人拍手称快。
中卫的历史文化悠久,从石器到石蜡,从岩画到长城,从丝路到铁路(高铁、高速公路),从“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到沙波头5A级景区,从黄河排子到香山机场……虽然走过了漫长而艰苦的历程,但改革开放取得的辉煌,却是有目共睹的。我少年时代衰败的北巷旧貌换新颜,变成了高楼林立,商贸繁荣,直通火车站,成了还有休闲娱乐广场的高庙北大街。它与新鼓楼和高庙共同见证了古城大发展的每一步,至今还继续讲述着古城的历史和文化。
新鼓楼北巷地处古城文化的核心地带,它西北比邻文庙(内设中卫中学)、应理男校、应理女校和端甫学校,东靠宁夏省立中卫师范学校。占尽了天时、地理、人和的各种有利文化条件,形成了地灵人杰的特殊地位,传承了文化古县的艰苦奋斗、仁义礼智信等优良传统。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北巷出生的人,他们经历了“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锻炼于阶级斗争风浪中,奉献在改革开放的事业上”。他们发挥自己的聪明才干,是公认的县区乃至其他省市的单位骨干,有的是工农商等业的技术高手和劳动模范;有的被聘任为高级教师,教授,高级工程师,农艺师,兽医师,主任医师;还有的被选任为科、县、厅各级公务员。他们不忘国家的培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成就了“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中卫文化的新局面。现在虽然他们早已退休,但“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故乡情结,还在心中永驻。

作者简介
王非凡,1938年生,宁夏中卫人。西北师范学院函授部专科毕业。曾任中宁县教师、公社干部、县广播站编辑,后调任银南地委宣传部干事、纪委专职委员、地区文联原主席,宁夏回族自治区作协原理事。出版《益群长歌》《非凡短笛》。执笔与友人合作出版了《杞乡传奇》《牛首佛光》等,还发表了多篇文章。现居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