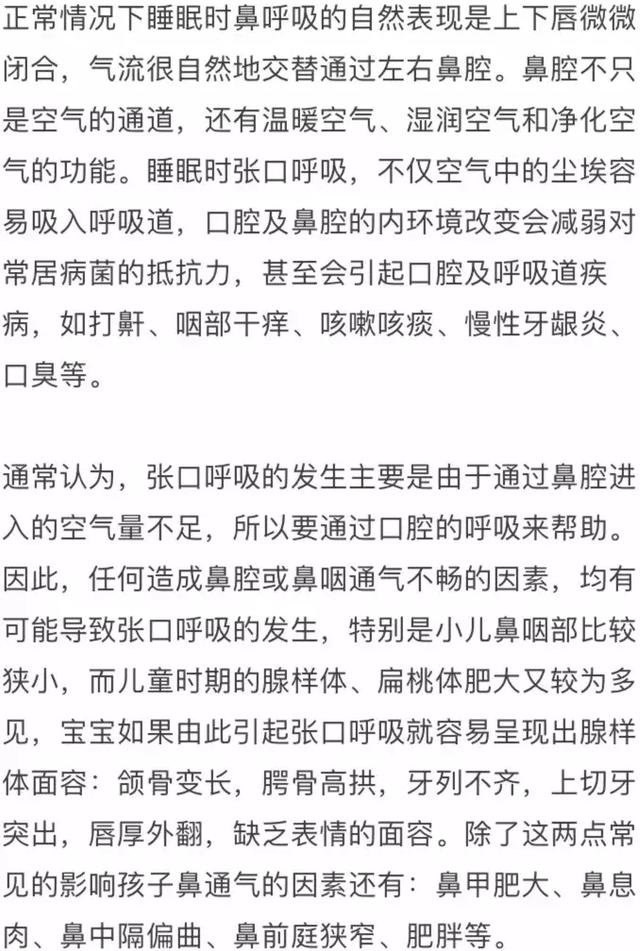作者:Lyroat
现实生活中,我们每个人时时刻刻都在面临一些选择,比如今晚吃金拱门还是开封菜、是打一局dota2还是玩一会星露谷,这些选项都是由我们自己主观给出,不会造成多大影响,所以很快就能做下决定。
同样,这些选择也出现在游戏中,它们可能仅仅是选择要不要给NPC一个苹果让他制作喜欢的料理、可能是选择是否打开一个不知会冒出怪物还是宝物的箱子,或是去决定带哪一只宝可梦进行旅行。这些选择一般不会在游戏结果上给我们带来影响,同时,此类处于虚拟世界的选择,也不会为我们带来现实中的物质损失,更不会在精神上给我们产生任何压力,
但是,当我们面临那些身不由己、违背价值观,或是会产生风险的选项时,做决定就变得非常艰难,有时还可能会陷入抑郁的情绪,无论是在现实还是在游戏中。
在我的游戏历程中,有两款游戏让我非常痛苦:《Beholder》和《This War of Mine》。

监控和战争的背景、反乌托邦的题材,都为我带来了一种非常压抑的心情。其黑暗、灰色的画面也让这种压抑更加深刻。同时,游戏为玩家提供的选择,更是令人难以接受:是做一个检举者活在压迫之下,还是做一个在暗流中伺机待发的反抗者?是通过掠夺而存活,还是去保持自我并等待死亡?你必须作出选择,无法逃避。
《Beholder》中的道德选择
妻子安娜不停地向你抱怨新生活的艰难,她的头上每冒出一次“叹号”,你就知道你那可怜的钱包又要出事了。从几十块钱的电视修理费,到几百块的收音机,再到最后几千块的电热器,一次次的需求将你推向了崩溃的边缘。
当然,你也可以不必理会她,直到你可怜的妻子走出家门,被游行示威的群众踩踏致死……你会因为你错过的选择而难过吗?还是会为再也不会出现的“叹号”而感到欣慰?

《Beholder》是一款由俄罗斯团队Warm Lamp Games开发的一款策略类反乌托邦性质的游戏。游戏中,玩家是一名在极权社会中被政府安插的楼管,必须监视每一位租户,偷听他们的对话,并向你的上级报告他们,同时,还必须要向当局报告会密谋颠覆政府的任何人。
“这是一款关乎道德选择的游戏”,在此前我对《Beholder》团队市场部叶甫盖尼先生的采访中,他这样说到,“你可以耗尽全部精力解决租户的全部需求,也可以偶尔敲他们一笔,还可以作为政府的眼线将所有租户送入监狱。我们不会告诉玩家到底什么才是正确的。我们给了玩家所有的选择,而玩家作为同样受极权主义迫害的房东卡尔·斯坦,在如此紧张的环境下会做出怎样的选择,才是我们所期望看到的。”
是的,现实生活中你可能并不会因为邻居家藏有违禁书籍就将他举报,可如果在极权主义充斥的社会中,你会吗?你会因此举报他?还是写封恐吓信,然后敲他一笔?或是悄悄买本书藏在他家,然后再写信敲诈?
相信我,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违禁品只是一个苹果,你也不会放弃敲诈的机会的。不然,死的就是你。

“我们想看到的,是玩家在游戏中作为一个普通人——卡尔·斯坦,在充满压力的环境下所做出的选择。那些你不得不做,而又违背你个人意愿的选择,你可以说这一切都是独裁统治者的错。在反乌托邦背景下独裁者那疯狂而又愚蠢的决策,可以帮助我们创造一个更加紧张的环境,同时,也能看到玩家会做出如何困难的决定。”叶甫盖尼补充道。
那些违背你意愿的选项、你不得不做出的决定,以及极权政府、受监视和反乌托邦这三个元素的串联,让这部作品给人的体验变得非常灰暗。在面对这种情况时,你会做出怎样的道德选择?
《This War of Mine》中的生存选择
远方的炮火轰鸣,打破了这个寂静的夜晚,躲在这个战后废墟中的你,并没有睡的多么享受。你躺在那个破破烂烂的睡袋里,手边放着一把自己改造的手枪,防止某个同样为了生存而来的幸存者来抢夺你珍贵的口粮和饮用水。
半睡半醒中,你听到了房外传来的急促的脚步声。惊醒,拿起手枪,慢慢挪动到楼梯拐角处,你微微探出头,发现了那个传出脚步声的男人,他身着深色衬衫,穿着牛仔裤,把头上的帽子压的极低,手里握着一把小小的匕首。
你知道,在这种战乱的环境下,任何人都会为了生存不惜代价。男人小心翼翼的搜寻着什么,抽屉里没有、衣柜里没有,最后,他在沙发下的纸箱里找到了你费了好大周折才拿到的唯一一瓶药物。你的心中很清楚,你不能让他拿走这个,于是你跑过去和他进行了一番打斗,但男人并不想放弃,于是你冲动之下,让他尝了下子弹的滋味,倒在了血泊之中……

《This War of Mine》游戏截图
次日,你像往常一样出门寻找物资。你注意到路边有一个无助的小男孩,你们对视了两秒,他走向前来用手揪住了你的衣角,问到:“你有见到我爸爸吗?我生病了,他昨天为了给我寻找药物来到了这边,但知道现在都没有回来,这是他的照片”。你脸上一怔,对男孩说到:“抱歉,我没见到过”,抑郁、自责、愤怒和绝望,陪你度过了余下的日子。
物资的匮乏、幸存者之间的相互攻击,游戏中阻挡在玩家面前的生存选择,让《This War of Mine》成为了第二款给我造成痛苦抉择的游戏。
当你面对持有饮用水的老妪时,你是选择强硬的夺过那瓶水,让她面临死亡的威胁,还是放弃这次搜寻?你看到的是男人来搜刮资源时对你产生的威胁,但却不能了解到他背后的难言之隐。
这款基于萨拉热窝战争改编的游戏,让我们了解到了战争的残酷,以及伴随战争而来的那令人难以面对的、痛苦的生存选择。但,这并不应是我的战争。

《Frostpunk》中的政策选择
《Frostpunk》出自《This War of Mine》开发及发行商 11 bit studios,是一款社会生存题材的游戏,它考验人们在被逼到灭绝的边缘时,能做什么。
在一个终极的冰霜世界里,人们研发出蒸汽动力技术来对抗极度严寒。作为城市管理者,必须妥善管理居民和他们赖以生存的基础设施。领导者的决策能力将面临挑战,同时,人的道德以及符合人们对于良好秩序社会认知的基础将频繁受到质疑。
游戏中,为了解决问题、优化管理,你需要制定各种政策,然而这些政策,时常会与你的道德观念相违背,对你的同理心产生一定的打击。
为了保证供暖,我派遣了一队工人去收集煤炭。极度寒冷、饥饿和劳累,让这些工人苦不堪言,几天后,便有人支撑不住这种强度的工作,有的手背冻伤、失去知觉,有的感染上疾病。
这时,在我面前出现了两种手段:根治疗法和维持生命。选择根治疗法,病人会被截肢,从此成为一个残疾人,但这至少能救他的命,而且也不会将传染病扩散;选择维持生命的话,那他就会永远躺在病床上,靠机器为生,然后慢慢死去。

我心想,这算什么选择?是根治还是维持,不应该由病人来选择吗?但没办法,这就是现实的残酷。
二者选其一,我选择了根治疗法,在这种需要相互依靠的生活环境下,我不能失去这些人们,我们需要互相依靠和关怀。
于是,那些患有重病的人民因为政策决定而被截肢。其中有这么一位,引起了一段小风波。
这是一位固执的老人,医生说他非常执拗,就算死在这里,也不愿截肢。他们给了我两个选择:1. 按住他为他截肢;2. 随他去。我知道,如果随他而去的话,那么老人很可能就因此而自暴自弃,躺在冷冰冰的宿舍床上,让痛苦消耗掉他仅存的意志。
于是,我选择了强行给他截肢。手术很顺利,老人并没有死去。而我依然还在思考,根治疗法是否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但相比死去,这可能还能够接受吧”,我安慰到自己。
几天后,我收到了一封感谢信,信中写道:感谢你当时的决定,虽然被截肢了,但我仍然还活着,谢谢你,我现在过得还不错。
这封感谢信为我带来了些许慰藉,但没多久,一起自杀案就冲散了这自以为是的心安。
一周前,一位父亲找到我,他说他年轻气盛的女儿独自跑到了荒野上,在这天寒地冻的世界里,独自一人没有带干粮,恐怕活不了多久。父亲恳求我,让我同意他出去寻找女儿,可是我拒绝了——因为我没有足够的口粮提供给他作为旅途支撑,我也不能选择放任他不管让他去荒野送死。于是,我叫人按住了他,让他留在城市里……
而就在刚才,在我正在因为“截肢”事件做的决定而感到微微满意之时,我突然被告知这位父亲自杀了,只留下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这是我跟孩子团聚的唯一方式”。

由于一定的限制,我不得不做出这些缺乏人文关怀的选择,成为一个铁腕领袖。这是我为民众能做的唯一选择。
紧接着到来的,还有是否为了提高生产而使用童工、是否为了民众的温暖而消耗大量煤炭,以及是否为了大家的安全而让一部份工人放弃劳作成为警卫……

这些政策、行为的选择,几乎都在与玩家的同理心相矛盾,无一不挑战着玩家的底线。
但此刻,为了仅存的这一小批人类,这些矛盾与缺乏关怀的指责需要你独自承担。

为何要有如此痛苦的选择?
《Beholder》中的道德漩涡,《This War of Mine》中的生存窘境,和《Frostpunk》中的政策抉择,无一不让我感受到此类游戏的“恶意”,为何这些游戏要让我们如此难受、痛苦?
或许,这就是游戏带给我的另一种思考吧。
这三款游戏让我知道,游戏不仅仅是像猎魔人杰洛特那样魔幻、像战神克雷多斯那样传奇、像星露谷的鹈鹕镇那样安逸,它们用灰暗的背景、违背意愿的选项和痛苦的结局让我感受到了另一种游戏体验。
游戏将玩家带入到一个极端的环境中,对玩家产生心理上的压迫,并且利用了大多数人的同理心和那种在认为自己犯错后所产生的愧疚感,来让玩家产生到这种痛苦——即使这些极权主义、战争和极端寒冷环境可能并没有出现在自己身边。
这种心理学上的策略,让我们通过不断地尝试来寻找到一个最优方案,会为了寻找道德上的平衡而花尽心思:通过一次次小心翼翼的选择和操作,让卡尔·斯坦那些可怜的房客能够存活下去,并且还能让家人免遭疾病和死亡的威胁。尽管我们已经进行过了无数次的敲诈,但在那种情况下,这可能是唯一的万全之计了。
同时,这种关乎道德、生存的选择,让我们与游戏之间的交互、体验更加深刻,当你的选择会造成一些难以补救的后果时,这会让你思考更多。
或许你曾因为《Beholder》中的极权政治而感到窒息,或许你曾因为《This War of Mine》中间接杀害幸存者而感到难过,或许你会因为《Frostpunk》里缺少人权的政策制定而感到苦恼,但请不要拒绝,这只是游戏中的选择。
以下是萨拉热窝战争——《This War of Mine》的故事背景——中的真实故事:
帕夫列由于失血过多死在了黑市的街边,狙击手的子弹刚巧穿过了之前某颗子弹打出的凹槽,击中了他的腰部。
他帮助的这个女孩子的父亲叫做尼基柯维奇。这个家族管理着狙击手大街上的黑市交易。女孩顺利找到了父亲,天亮后父女俩把这个好心的陌生人运到公园的公墓草草掩埋。
尼基柯维奇在帕夫列的上衣口袋里发现了他的日记本,得知了这一家人的悲惨生活。为了报答这个陌生人,他带了一些食品和药物去交给了米涅娃。他最多只能帮到这,他不能冒险把陌生人带回自己家的基地,即使是妇女和孩子。
塞尔维亚族叛军围城不允许任何补给进入城内,任由古城萨拉热窝的市民自生自灭。帕夫列死后一个月就爆发了大规模的饥荒,他的两个孩子死于营养不良和疾病感染的双重折磨之中。丧夫又丧子的米涅娃变成了一个疯子,死于两军的交火线上。
四个月以后,萨拉热窝的秋冬之际开始,由于缺乏木柴,很多市民在烧光家里的家具和书本之后只能忍受刺骨的寒冬。无数人死于寒冷导致的疾病,尼基柯维奇的女儿、父亲和舅舅都被死神用高烧带走了性命。
围城战打了四年,塞族领导人宣布停战的那一天,尼基柯维奇穿上西装,来到公园公墓向父亲、舅舅、女儿和那个叫帕夫列的陌生人报告这个消息。但是一切都已经迟了。
虾丸君:
这些仅仅是你迫于游戏资源所作出的无奈之选。
但也不要忘记,对阴暗的极权主义说“不”、向残酷的战争发出抗议,以及对缺乏基本关怀政策的不妥协。
更多文章请移步菜单栏“虾丸主线”和“虾丸社区”游览
如有投稿或合作意向可发至geekgaming@163.com邮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