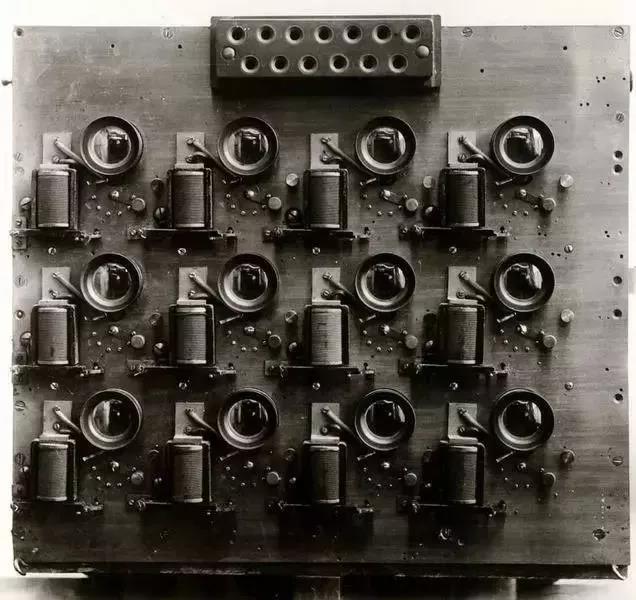我应该对学生如此说 ,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我可以什么都不会说?以下内容希望对你有帮助!

我可以什么都不会说
我应该对学生如此说
刘世颂
《一只窝囊的大老虎》是人教版四年级上册的一篇课文,作者叶至善。文章是回忆他童年在一次全校周会演出扮演老虎的故事。故事围绕着“豁虎跳”而展开,演哥哥的小朋友一直认为扮老虎一定要有“豁虎跳”,而老师却认为不一定要“豁虎跳”。“我”按老师的指导、排练、演出,可正式演出时却“砸”了。作者行文中一直没有道出演“砸”的原因,而是以“为什么不会豁虎跳就不能扮老虎呢?为什么没豁虎跳就会惹起哄堂大笑呢?我至今还不明白”而结尾。备课之时我查阅了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黄金课堂.四年级语文上册》、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小学教学全解.四年级语文上册》和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全易通.小学语文四年级上册》等几种不同版本的教师备课用书,也百度了许多老师的教学设计。主流观点:一、演“砸”了的主要原因是“我”演出时太紧张,都不曾提到与“豁虎跳”有关。二、文章的主题是作者对童年生活的美好回忆和怀念童年时代的“求真”精神。
我总觉得以上观点有不妥之处。
期间,我正好看中国音乐学院副院长周海宏教授《走进音乐世界》的讲座。
周教授说,很多人之所以不去听严肃音乐、高雅音乐、经典音乐主要原因就是觉得“听不懂”、“不知道音乐表达什么”。这其中有伯牙、子期“高山流水”“知音难觅”的许多功劳,他们的故事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对音乐的认知,给人们和严肃音乐之间挖了一条鸿沟,使人们不敢轻易结束严肃音乐,还有一个更直接的原因:我们进行的音乐普及、教育工作,“基本上都以乐曲解说为核心”。不知不觉地这种观念就进了大家头脑,“严肃音乐和通俗音乐不一样,它是有着深刻的思想内涵,要欣赏它你就要理解它,要理解它就要了解时代背景、作者背景等等,甚至还得学点乐理知识”。经年累月的宣传,电台、电视台、书籍、杂志、报纸、节目单等等各个层次的教材充斥了这样的内容,结果人们就对此深信不疑,形成了思维定势。其实,音乐内容的理解是主观的、模糊的、多种多样的。同一个作品不同的演奏家对作品的理解都是千差万别,何况我们?所以我们在听音乐的时候没有必要非得听出形象、哲理等等东西,那是一个误区,那个误区给人们欣赏音乐构成了很大障碍。
听过周教授的讲座后,我豁然开朗,绝不能人云亦云。这篇课文,作者对童年往事的回忆既有甜蜜——班主任的支持,也有苦涩——演哥哥的小朋友三番五次的责备,台下老师、同学们一见我爬上场就哄堂大笑。他们的哄堂大笑真的是因为我“笨拙”地表演吗?不是。请看原文:我知道推我的是老师,立刻弯下身子爬上场去,嘴里啊呜啊呜直叫。只听见台下一阵哄堂大笑,笑得我脸上一阵热。(此处敲黑板)他们的笑是因为他们见到了一只爬上场而不是以“豁虎跳”跳上场的老虎。他们和演哥哥的小朋友一样,都觉得不会“豁虎跳”的老虎就是笨拙的。因此,真正“砸锅”的原因是除了班主任之外,他们都认为演老虎就得会“豁虎跳”,不会“豁虎跳”就不配演老虎,当时连“我”也奇怪的认同了——“是啊,要是我会豁虎跳,这场戏就不至于砸锅了。”后来“我”常去动物园观看老虎,一直都没见到过老虎“豁过什么虎跳”。于是,作者便在文章结尾处抛出这样的疑惑:为什么不会豁虎跳就不能扮老虎呢?为什么没豁虎跳会惹起哄堂大笑呢?我至今还不明白。我认为“至今”应该是指到作者写此文为止,所以我认为本文不仅是对童年时代“求真”精神的怀念,更应该是批判僵化、呆板、消极的思维定势,警示人们“一棵树上吊死”的做法,弘扬灵活、开放、积极的发散思维。
听严肃音乐就得理解他们的内涵,表演老虎就得会“豁虎跳”,这都是思维定势在作祟。周海宏老师在说,叶至善老师也应该是如此在说,我更应该对学生如此说,对自己说。
简介:刘世颂,网名世公页,江西省万年县人。70后,80年代师范生,平凡之人。常拾笔,笔随心走。偶瞅着夕阳的余晖念着朝霞的缤纷。涂涂画画只为描摹生活,片纸只字只为记录瞬间,给生活留些回忆,无他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