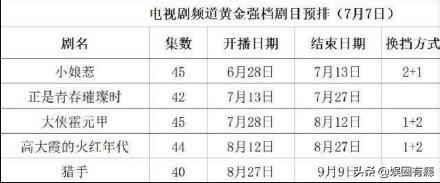——遂宁音乐发展简史

音乐,伴随着人类的出现而产生。不管社会如何发展、社会文明如何变化,音乐始终贯穿着人类的生活。
一代又一代的遂宁人在劳作、生活中也形成了自己的音乐样式,洞经音乐、蓬莱大乐、船工号子等。一代又一代的遂宁音乐人汲取着这些传统音乐的精华,将遂宁的音乐路越拓越宽广。
三大传统音乐 积攒宝贵财富
在清代以前,遂宁音乐人以卓越的才华创作了大量如蓬莱大乐、洞经音乐、象山花锣鼓等形式的音乐。今天,这些都是后人宝贵的音乐财富。
洞经音乐的起源颇具传奇。据史料记载,乾道四年(1168),蓬溪人刘安胜在蓬溪县宝屏山(今赤城山)写成《文昌大洞仙经》5卷,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因谈演《文昌大洞仙经》而形成了闻名中外的洞经音乐。元代著名道士蓬溪县人卫琪,号中阳子,隐居蓬溪县蓬莱山。他幼好道术,洞测玄妙,在蓬溪县蓬莱山为《文昌大洞仙经》作注。公元1310年,曾任南平綦江等处军民长官的卫琪上表将《大洞仙经》献给朝廷,被元朝皇帝首肯,在全国普及。该经名声大震,各地争相翻刻,谈演《大洞仙经》。为此,洞经音乐也随之流传,至今在云南、江苏四川等地仍有演唱。
蓬莱大乐流行于遂宁市及边沿地带。“蓬莱大乐”作为巴蜀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被誉为“巴蜀文化精品”“东方神乐”。相传,此乐由我国周朝时宫庭乐师发明,流传到唐代开元年间,唐明皇听到此乐高昂悦耳,演奏队型壮观,气势磅礴,特命为“大乐”,专供皇帝登基和帝王出巡时使用。明末,有一青年乐师因战乱出宫,后到中江定居,用他的技艺建起了一支乐队,于是世代相袭,光绪年间传入蓬溪。20世纪初,四川的中江、金堂、蓬溪、射洪、南充诸县十分兴盛。原蓬莱大乐的节奏欢快,气势热烈喜庆,融北方锣鼓阳刚之气和四川民间打击乐柔媚秀丽风格于一体,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后经蓬溪县文体局组织专人发掘整理,依据传统模式,结合巴蜀文化特点,重新制作乐器,创制新曲牌“五洲庆瑞”,改进乐器组合,调整鼓乐队形,使得“蓬莱大乐”演奏时场面更加恢宏。人们盛赞“蓬莱大乐”为四川的“威风锣鼓”。
象山花锣鼓系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四川古代十分有特色的音乐,创始于清朝,由当年象山民间鼓乐手组成‘公堂’(即乐队)开始在民间流传。花锣鼓的乐器由大锣、大鼓、大钵和四个马锣组成,节奏跳跃,后来花锣鼓靠家传或同族组队流传下来。
多种民间音乐 丰富群众生活
我们的先辈们在长期的劳作中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号子,如船工号子、石工号子、各种叫卖调、打夯歌……在我们今天看来,这些号子也是不可多得的传统音乐财富。
涪江号子是流传在涪江流域(绵阳至重庆合川)的传统民歌。在木船航运时代,每当逆江而上或者船过险滩的时候,船工们就得拉纤。为了协调步伐和鼓舞士气,船工们就在号子声中掌握行进节奏,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就逐渐形成了“涪江号子”。
因处于临江码头,遂宁商业繁荣,小商小贩特别多,在街市、乡村,各种各样的叫卖调比比皆是。由于各种商贩的叫卖特点也不同,因此,流传下来的叫卖调品种繁多。另外,过去的很多商品有季节性,所以叫卖调还给人们带去了时令季节的信息。
据史料记载,在分水镇这片古老而肥沃的土地上,石工们在开山采石、修塘筑坝、修桥筑路、营造梯田、盖房造屋时,呼喊着各种不同节奏的歌谣,便形成了拥有独特韵味的石工号子。
吸取传统精华 唱响遂宁之歌
在当代,一代一代的遂宁音乐人如颜孝平、熊宗德、翟昌权、周光国、何训有、何训田、高垣根、曾擎和一些遂宁音乐新秀等在汲取传统音乐精华的基础上,谱写了大量脍炙人口的遂宁歌。
1986年,由熊宗德创作的《遂宁啊,故乡》唱响遂宁的大街小巷。当年,第一个升入太空返回祖国的美籍华人王锡爵(祖籍四川遂宁)回乡探亲,遂宁市政府专门为王锡爵举办了热烈的欢迎晚会,到会的还有中央、省市领导,晚会的主题音乐《遂宁啊,我的故乡》就是由熊老先生作曲,著名词作家刘俊明作词。在王锡爵回乡访问的电视记录片中,该曲被改编为背景音乐,受到遂宁市有关领导及王锡爵先生本人的高度评价。而高垣根所作的《歌唱遂宁八勇士》《风儿轻轻吹》《明珠之歌》等歌曲也让世人通过歌曲加深了对这座城市的了解。
2009年,在“5·12”特大地震周年祭之时,由曾擎作曲,著名歌唱家谭晶演唱的《人间遂宁》,唱出了人们对逝者的哀悼,对生者的祈福。2009年5月7日在遂宁新闻网率先推出后,迅速蹿红网络,成为全国各大网站、论坛社区热门转载内容。据曾擎介绍,在5·12汶川大地震一周年之际,推出这首歌,表达的是跨时空的挚爱和人间永恒的真情,人间从此遂心遂愿、福寿安宁。”
这些年,我们听到许多和遂宁相关的歌曲,《归燕吟》《涪江梦 中国梦》《遂宁谣》《爱上遂宁》《美丽遂宁我的家》……一代又一代遂宁音乐人用音乐符号唱出了自己对这座城市的深情。
(全媒体记者 徐金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