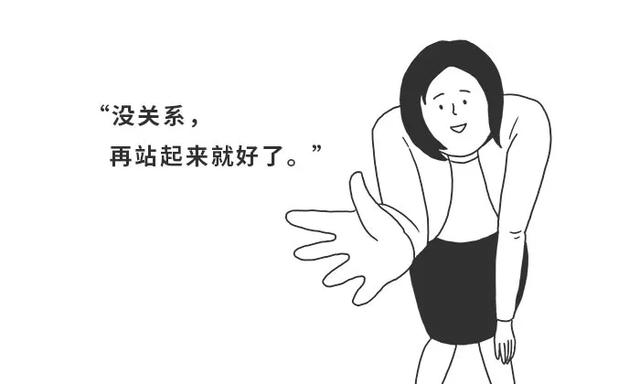编者:继5月20日深港书评“在深圳写作”栏目上发表了作家王国华的创作谈后,他的“城愁”概念愈加兴起。何谓“城愁”?王国华说,是因为旧城改造,老城消失,新的小区拔地而起而产生的怅惘和失落吗?会有一些,但一定不是全部。如果愁绪仅仅是换了一个附着物,从农村院子里的老牛转移到都市公园里玩过的碰碰车,这样由“乡愁”转来的“城愁”,自然是简单了。
在王国华心里,深圳已然是故乡,而绵长又深刻的“愁”才是对故乡无法释怀的情感。王国华在本文里将这种情感化为一个一个小细节,诉说深圳对他的影响,诉说他的文学如何“塑造”了深圳。
“城愁”即故乡
■王国华
爱上深圳
我与深圳的关系是从一个一个小细节开始的。刚到深圳那段时间也有很多不适感,比如酷暑时身上总是发黏,出去转一圈回来就要冲凉。饮食上不适,吃什么都不可口。这里有国内最全的“地方美食”,但偏执地说,都要或多或少做点手脚,以迎合更多人的口味。一些生活习惯也不适应,东北人被认为酒风洒脱超然,但饭桌上也有自己的规矩,由尊至卑,一个一个发言提酒,秩序井然,这里却是三杯过后就打乱仗,闹闹哄哄。
不过,不适很快被另外一些内容冲淡了。比如几乎所有卫生间都配有手纸,无论公园还是城中村的苍蝇馆子。半路内急,到街边一饭店借用厕所,服务生毫不犹豫地打开门。乘坐公交车时没零钱,到附近一个小卖店换,店主客客气气地给我换了,如果在其他城市,你一般得买点东西才行,跟你不认不识的,干嘛帮你忙,万一你是骗子拿假钱蒙我怎么办?这里对待陌生人的态度,远没外地人想象的那么冰冷生硬。
据说这是深圳人做生意的精明,把你当成潜在的客户,乐得帮你一把。但这种与人为善,久而久之就会成为民风。而在若干号称有人情味的城市,热情是送给自己认识的人、熟悉的人或者本地人的。你一不小心暴露了外地口音,只能处于被动挨宰的境地。旁观者即使知道店主坑你,他也下意识地向着店主说话。甚至,他也是刚刚被店主坑过的,只因你是外地人,他就想看你的笑话。你不得不小心翼翼,时时担心被坑被拒绝。
另一个是各行各业的服务意识。比如我到现在仍坚定地认为长春的出租车司机是全世界最差劲的司机,没有之一。拒载、故意绕远、加价、抽烟、说脏话、开车煲电话粥……他们创造性地发明了很多出租车之恶,并一以贯之地坚持下来。不否认他们中间有好人。我一年打一百次车,遇到十次,概率才十分之一,不高,但足够让我提起他们就厌烦。反正每次打车的时候,我都心中不爽。在深圳,完全不用有此顾虑。同理,深圳出租车司机也不全是好人,但比起我去过的其他城市,动辄拒载、坑人的司机比例小多了,小到可以忽略不计。
▲“饺子李”是我的文字中极少提到的具体的人。老板开心地跟我合影。
在深圳不用顾虑的事还有一些。无论多晚都能买到东西。很多便利店24小时营业。在饭店不用顾虑被服务员瞧不起或者训斥,你花十块钱也能享受到真正的大老板一样的服务。一天,我们一行人到一个路边店吃饭,饭后开始打扑克,一直打到凌晨两三点,服务员就在旁边坐等,后来困得趴在桌子上睡着了,也没撵我们走。这在其他地方是奇迹,在深圳却是常态。当然,我们也体谅人家的不易,给了他一笔不错的小费。
那些让你不爽的出租车司机,坑你的小摊小贩,跟你耍态度的窗口阿妹,欺负你家孩子的小混混,压榨员工的私企老板,任何城市都有,深圳肯定有。但还是那句话,你在深圳碰到的概率比较低。不是说深圳人素质比外地人高,而是从管理上对那些欺人太甚的人有相对成熟的惩罚机制。因此,在这里你不必一出门就提起一颗心来准备战斗。当你到其他地方走走,生活一段时间,多遭遇几次无缘无故的戾气后,才会意识到深圳跟它们是不一样的。
▲深南大道上无数次留下我的背影,你一定注意不到。
到远方去
一个人,一出生便是脱离,离开一个封闭的空间,到了一个开放的大空间。呼吸舒畅了,眼睛睁开了,可以看到飘渺的没有尽头的天空,听到风声雨声雷声笑声和哭声,但他内心有着与生俱来的不安全感。渐谙人事,他就必然寻找一个可以重新安放此身的所在。这个所在,有可能是出生之地,更有可能在遥远的地方。
我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在华北大平原上的农村度过。血液里淌着阳沟里浇地的水流,脑瓜顶上飘着落下来的硬币大小的枣树叶子,说话也脱不了一村一口音的方言。大平原,说来似乎有诗意,尤其对那些从没到过此地的人。多年后,一位山区朋友再三对我发感慨:我到你的故乡了,路上好平啊,连个坡都没有。我以转移话题做了回答。我不能对他说,我非常不喜欢那个地方,我不肯把“故乡”二字用在它身上。
从认字开始,我心里就开始描摹一个未曾谋面的远方并筹划如何抵达。村庄在我成长经历中的关键词是封闭、狭隘、物质匮乏、争斗、猜忌,等等等等。我向往与此相反的词汇。既然自己生活的地方找不到,那一定在另外一个地方,即城市。这个城市最初在我心中乃乡镇所在地,一个是阜城县蒋坊乡,一个是泊头市(原为交河县)西辛店乡,分别距离我们村两公里和三公里,逢年过节赶个大集就是人间艳阳天。然后是县城、地级市。犹记当年在衡水街头,看到一对穿着售货员制服的青年男女坐在花坛边怯生生谈爱的场景,心悸不已。想,什么时候也能拥有这样的生活。我一步一步往外走,那个美好的“故乡”没有落在具体的一个地方,而是随着视野的拓展不断变化。
▲幼年一度向往的蒋坊乡大集。摄于2017年10月
总之,我要到远方去。
高考填报志愿时,我选择了很多南方的城市,武汉、南京、苏州、上海等,只填写了一个北方城市做替补。等待音信的那些日子,有一天半夜梦见自己在东北厚厚的雪地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行走,四野无人。突然惊醒,满头大汗坐起来。三天后我收到了东北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而在长春读书、工作的十八年间,不知为何,我经常想象未来在深圳的生活,细节都想到了。那时候我根本没到过深圳。住集体宿舍的几个月期间,我们发牢骚嫌条件不好,一个从深圳返乡的同事开心地说:“这已经非常不错了,我在深圳住在铁皮房里,简直能把人热死,深圳真不是人呆的地方”。即使他这么说,也遏止不了我的想象与期待。当时的执念或许来自于零星从报刊上读到的深圳奇迹,或者说我内心里生长着不安于现状、渴望奇迹的因子。身未到,居然已将其视为“吾乡”,此身安处是吾乡。
人要想象,大胆地想象。时间长了就会变成现实。
源于深圳的“城愁”
每个周末,我都流连于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山川河流、公园、社区。我走进敞着门的祠堂,打量雕梁画壁,和雕塑对视,时间一长,雕塑就能张开嘴。我站在榕树下面,一根一根抚摸那些随风飘荡的棕红色气根,用它缠住自己的手指头,慢慢地裹紧。我在刚建成的过街天桥上走来走去,成为最早留下脚印的人。
有一段时间,我到处寻花。每一朵花都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我要和它们聊天,只需半个小时就了解了它的一生。我要蹲下来甚至趴下来才能看清它们。那天刚刚下完雨,我两手撑在地上,掌心沾满了泥,凑近那一株黄鹌菜,感觉到它善意地向我侧过身子来。旁边跑步的人不知我在做什么,也不问。这样真好,大家都沉在自己的世界里。为了找到更多未知的花朵,我会带一个背包,一整天在山林里晃,背包里带着充电宝、面包、矿泉水、双飞人、速效救心丸等。三瓶矿泉水喝完,嗓子仍然冒烟。后来我写了二百多种花,凑成了一本书。我实际看到的远远多于这个数。不知在其他城市是否能遇到这么多种类的花。
▲冬日的大沙河畔。数次来此踏查的我,也成了风景的一部分。
后来我又去追寻深圳的水。水的形态有哪些?河、湖、海、溪、瀑布,还有井。我一个人骑着共享单车沿茅洲河狂奔,大雨哗哗地浇下来,无处躲藏,浑身湿透。我开车拉着妻子去看马峦山瀑布,走错了路,在一条狭窄的单行道上前行,两边的树枝直扫车窗,差点找不到掉头的地方。妻子事后告诉我,她吓得掌心都是汗。
我对每一个陌生的地方都充满好奇。我用手去触动它,用鼻子去闻它,用脸去蹭它,和它长久地坐在一起,感受它的气息从地面生发出来,悄悄渗透到我的身体里,成为我身体的一部分。当我一一叫出那些花朵的名字,对它们的习性越来越了解之时,我就进入了它们,进入了深圳的内里,我和这座城市贴在了一起。我心中渐渐产生了一些愁绪。这是安定下来以后的闲愁,是淡淡的,无由的忧伤。它不苦。
飞向天空
最初的行走还真不是为了写作。时间一长,心中所想再也压不住,便写了出来。这就是我的“街巷志”系列。“城愁”两个字非我首创,却是我倡导和推广的。街巷是支点,城愁是灵魂,它们是一个整体。越来越多的人接触到我的“街巷志”,接受了“城愁”两个字,但也看出一些端倪,具体表现为两个。
一个是,“为什么你的书中写了那么多事物,很少写人”?确实,一篇几千字的文章,即使有人也是路人,几乎很少提名道姓指出某个人,更没有一个完整和曲折的故事。我得承认自己是有意为之。前些年不是没写过,关于人和人之间的恩恩怨怨,前因后果,人际关系,酸甜苦辣,翻来覆去就那么点事,自己都写恶心了。我的文字要向天空飘去,向地下潜去的。它们要空灵,要接近神,人类的污浊之气很容易污染了它们。须知,万物并非死寂,人气远离之后,它们在自己的空间里就会七嘴八舌地发言。动物、植物、水、天气、地铁、建筑、海浪、城中村,它们边说边飞,带着我的文字一起飞。其实一定有人隐在万物体内。几十万字的书写,怎么可能没有人?只是主角变成了配角,配角变成了主角。我得尽量把握着一个尺度,让具体的人的故事远离它们,保持万物相对的干净和纯粹。
另一个是,“你写的深圳跟我想象的,见到的怎么不一样”?刚听到这个问题,我第一反应是:莫非自己写秃噜了?后来一想不是这样的,深圳本来就具多样性,东部和西部,大鹏和福田和龙华,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经济差异,人口差异,历史、地貌差异,甚至精神状态都极不同。行业分布,有的地方是所谓白领聚集,有的地方聚拢IT和金融,有的地方遍布厂妹。在宝安总是忙忙碌碌,一进入大鹏半岛,停下就要躺平,除了安安静静地吹海风吃海鲜喝啤酒,什么都不想干。虽然现在已无关内关外之分,心理上的差异还没消失。一位罗湖的朋友听说我住在西乡,就说“好远哦,我从没去过”,我回复说,开车不过半小时。它们都称为深圳,却没有一个所谓的深圳概念可以覆盖全部的现实存在,所以无论你怎么写,只能写出一部分深圳,获得一部分共鸣。有些大而无当的词汇,当个笑话听听就行,别拿来使用。
▲在大鹏新区半天云村里,被树木侵蚀的旧屋,将永远活在我的文字中。
这种个体的深圳反而让我获得了解放。我无需亦步亦趋跟着当下的一切走,我可以塑造一个我自己的深圳。“塑造”,这个词好大呀,深圳已经在这里,需要我塑造吗?深圳可能需要华为,需要大疆无人机,需要华侨城来塑造,你王国华是干什么的?我要说,一个文化的深圳,当然需要文化人塑造。尤其是文学,此乃艺术之根。我的塑造体现在哪里?举个例子,我在地铁车厢里看到有人坐在你的肩膀上,那个人就是前些年上班时猝死在地铁口的一个白领。我看到榕树上住着一群人。我要在平峦山的树林里挖一个陷阱,等着有人掉入并与我发生连接。我在南山区铜鼓路上找到一条很大很大的长椅,等世界末日来临时,这就是我要避难的地方。我看到香蜜湖里的水飘了起来,是湖畔一只水鸟把它拽起来的,而那水鸟可能就是我指派的,我自己又浑然不知……是的,我的一个一个遇到,一个一个想到和一个一个记录,便是我塑造的深圳。深圳需要传说。我赋予这座城市忧伤和传说。
我潜意识里的使命感越来越强。那些即将倒塌的旧屋,一个个消失的老市场,要永远存活在我的文字里。只要是打开我的书,它们就生动地跳起舞来。那些未来的日子,在我的文字里提前出生,茁壮成长。那个“未来”到来时,它会抄起我的文字镜,反复地照,眨一眨眼,问那面镜子:你的主人是谁?
▲宝安七十三区夜市。我写完之后不到一年,它已消失了。
安身即回归
在深圳,我的心灵得以安放。我已大大方方地称之为故乡了。这座城市有一句让人心动的口号:“来了就是深圳人”,我则直接将“街巷志”系列中的一本命名为《深圳已然是故乡》,与之相呼应。这么一句大白话,其实还是稍微冒险的。有那么一些奇怪的人,脑子里总有奇怪的想法,诸如“子不嫌母丑”“故乡的山水养育了你”“最美还是故乡人”“我的故乡我维护,谁也不能骂”……将他乡当作故乡,在他们眼里不啻“认贼作父”。虽懒得搭理此类言辞,但还是应该把我的态度亮出来,一、你随随便便把某地当妈,我可不一样,我只有一个妈,在一个小村子里生活。二、不管你是什么水养大的,但我喝的是父亲挑来的水,没喝过你家的水;三、美人有很多,为什么一定是“故乡”的呢?听某人大谈自己的故乡,他跟另一个人说,咱们××(省名或者县名)的人就是老实。我心里想,可我知道你并不怎么老实。以地域遮脸的人,大有人在。四、你如果在地铁或者公交车上大喝“××(省名或者市县名)人真是傻×”,且你长得瘦小枯干,可能会有人站起来跟你叫板,甚至揍你一顿。但你在深圳的地铁上来这么一手,根本没人正眼看你。即使旁边的都有深圳户籍。那些誓死捍卫“故乡”的人,不一定多爱他们的“故乡”,是他们真没什么可捍卫的了,需找个事物来盛放人性恶的一面,因为在此旗号下,可以干很多伤天害理的事。五、我从不以生活过的地方出过什么名人伟人为自豪,也不为家乡的所谓名山大川而自豪,那里面没有我的任何努力,他们的光彩也不能给我个人带来一分一毫的荣耀。他们是他们,我是我,各自独立。
此刻以深圳为故乡的我,仍坚持以上原则。这种状况带给我的改变是,回头打望自己长期生活过的地方,曾经的压抑和不爽、抵触和反感,渐渐熄灭了。身有所依,心态便平和。
我怎么可以舍弃和忽略那种缘分呢。无论河北阜城,还是吉林长春,都塑造过我。我的饮食习惯,吃面、吃饼、吃咸菜、葱姜蒜;我的性格,急躁、心软;我的身体,粗壮,都跟这两个地域有抹不掉的联系。即今日将深圳当成故乡,亦得益于当初那儿的友人的鼓励。
我开始用方言和老家的亲人、朋友交流。这是我大学毕业后,一直到现在,二十多年刻意排斥的语言。普通话和方言岂止表达的变化,更会间接影响到思维,此正是我要坚持普通话的重要原因之一。奶奶八九十岁时,我跟她讲普通话,交流完全无障碍。一百岁后,奶奶耳朵越来越背,一句话跟她讲好几次都听不明白,转换成方言,立刻听清了。耳朵不用消化。现在跟母亲聊天,隐隐约约也有了类似迹象。我揪着自己的嘴改回方言,真如一门新语言。不过我也借此一点点在回归曾经的土地。
我和妻子在网上大量购买东北日常食用的冷面、煎饼、炉果、洋葱、黄瓜甚至生菜叶。电商成全了我们,东北胃口得到抚慰。虽然离开了东北,但依然在东北消费,为东北的GDP做贡献。
以前生活的地方,用具体的事物驱逐你,岂非令此肉身得安处?而若无深圳的皈依,又何来阜城和长春的回望?
但深圳不会是宇宙的尽头。某种意义上,它和蒋坊乡、西辛店乡没什么区别。以前是怕得不到它,此时也不敢保证已经拥有了它。它是我此时的心灵栖息地,不一定永远是。它会变化,我也会变化,将来或许它抛弃我,或者我再寻他方。一个人的心灵故乡,绝非一时一地。你,我,他,一辈子都在逃离和追寻。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追求或会钝化,脚步慢下来,甚至倒退回去,都不好说。
滚滚人流中的一粒沙,让风吹,让雨打,明明可以改变的非常有限,但还是要拼命挣扎……
王国华近年作品
《街巷志:行走与书写》
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
2018年11月
《街巷志:深圳已然是故乡》
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
2020年8月
《街巷志:深圳体温》
海天出版社
2021年11月
来源|晶报APP
编辑:陈章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