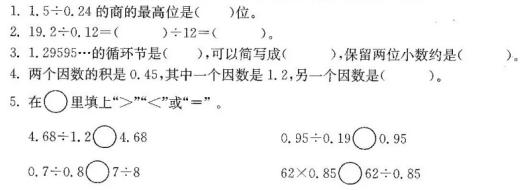2020年4月11日,工作人员在国药集团中国生物新冠疫苗生产基地质量检定部门对新冠灭活疫苗样品进行检测 张玉薇摄/本刊
生物安全威胁,使国防突破陆、海、空、天、网的疆界,拓展至“生物疆域”范畴,世界主要国家都在加强“生物新国防”建设
“生物安全的定义得到扩展、内涵得到充实,国家治理思路也实现重大优化。我国生物安全治理进入了最受重视的新历史时期”
面对生物安全的潜在风险和战略挤压,守牢我国生物安全疆域需直面应对策略、管理体系、经费投入和科技支撑的4大挑战
文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张冉燃
在2016年被“点将”进入生物安全的研究领域后,张卫文感觉这个行当的变化当得起四个字:“天翻地覆”。
张卫文是天津大学化工学院教授,生物安全战略研究中心主任。该中心是目前国内高校唯一的生物安全战略研究中心,也是教育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唯一涉及生物安全的战略研究基地。
张卫文告诉《瞭望》新闻周刊,2016年,作为科技部选派专家,他首次跟随外交部参加在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禁止生物武器公约》会议。此后,他又4次参加该会,并在《禁止生物武器公约》2018年专家会上,作为特邀技术专家之一就生物科技与安全做大会发言。
在他的印象里,西方国家那时就已经很重视前沿生物技术的安全使用,并把建立国际生物安全新秩序作为重要工作内容,但国内还更多侧重于生物科技发展,对生物安全关注不够,也缺乏系统讨论。
变化倏忽而至。2019年1月,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中央提出,我们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安全两件大事,既聚焦重点、又统揽全局,有效防范各类风险连锁联动。
作为安全的重要一环,生物安全引起决策层高度关切——2020年2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明确,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系统规划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
从决策层开始,社会各方对生物安全都表现出极大关注。张卫文记得,2020年3月,他和同事第一次在天津大学化工学院开设有关生物安全和伦理的课程,授课规模不超过60人。“我原本担心这门课内容太专,没人感兴趣,实际上学生选课积极性非常高,报名火爆。现在天津大学已同步推出两门涉及生物安全的全校选修课,授课规模达到每学期300人以上。”
生物安全为何引得上上下下高度关注?中国生物安全形势究竟如何?守牢生物安全疆域,我们面临哪些挑战?
“下力气完善”
在以往很多人的认知里,生物安全的样貌其实相对模糊,基本等同于传统的细菌战、传染病及动物防疫等。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杨霄表示,2010年以前,我国对生物安全风险的传统认识,主要是三分法,即从三方面描述生物安全威胁:一是生化武器军备控制,二是生物恐怖主义担忧,三是大规模传染病威胁。
在他看来,这种认识有很强的传统时代色彩。他解释说,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人类对生物安全风险的认识逐步形成了这样三类。而现在,生物安全的研究领域已经大大扩展,涵盖了防御生物武器攻击、防范生物恐怖袭击、防控传染病疫情、防止生物技术误用和谬用、保护生物遗传资源与生物多样性以及保障生物实验室安全这“四防两保”,从重要性上,生物安全被纳入国家安全体系的总体框架。
“这意味着,生物安全的定义得到扩展、内涵得到充实,国家治理思路也实现重大优化。我国生物安全治理进入了最受重视的新历史时期。”杨霄说。
首要表现是中央高度关注。北京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朱康有说,在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后,2021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强我国生物安全建设进行第三十三次集体学习,给各级政府、相关部门树立了标杆、提出了要求,传递出清晰的国家意志。
其次是领导有力。朱康有说,我国有关生物安全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较多,但多为行业主管部门制定的部门规章,缺乏系统性、全面性和协调性,2020年10月,我国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它的颁布实施是一个里程碑,标志着生物安全进入依法治理的新阶段,在生物安全领域形成国家生物安全战略、法律、政策“三位一体”的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
最后是投入坚决。张卫文表示,生物安全有关的战略、法律和政策对应了资源配置,在生物安全公共投资方面,我国近年维持了一定额度的投入。
以保障国家生物安全的重要防线——生物安全实验室等科研设施为例,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人表示,要争取尽快实现每个省(区、市)都有一个生物安全三级(P3)水平的实验室,每个地级市争取实现有一个生物安全二级(P2)水平的实验室,以大大提高重大疫情快速检验检测、快速响应的能力。
目前,各地正加紧建设P2实验室,投资金额从几十万元到几百万元不等,数千个实验室正在建设或已建成。在一些地方,全球生物安全等级最高的P4实验室也在规划建设之中。
“不光是生物安全实验室,可以说在生物安全诸多领域,能想到的地方近几年国家都在下力气完善。”张卫文说。

生物新国防
国家下力气完善生物安全的背后,是相关议题不断升格。
中科院上海巴斯德所研究员王小理认为,当前生物安全出现了新的“事态”“势态”和“世态”,使其在国家战略安全中的地位进一步提升,这也促使生物安全进入新的“时态”。
新“事态”是指局部领域和特定方向的生物安全风险剧增。王小理说,目前生物安全威胁已从偶发风险向持久威胁转变,威胁来源也从单一向多样转变。比如可能出现更多的重大新发突发传染病疫情,外来物种入侵加剧,以及生物技术谬用、生物恐怖活动增多等。
新“势态”是指生物安全风险的影响危害趋深。目前生物安全的威胁边界已经从局限于少数区域,向多区域、全球化转变,范围也从生命健康拓展到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战略利益等。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其影响早已溢出公共健康领域,诱发一些国家和地方经济生产等失衡、失序,甚至演变为不同程度的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等。
新“世态”是指频繁发生的生物安全事件,使国防突破陆、海、空、天、网的疆界,拓展至“生物疆域”范畴,世界主要国家都在加强“生物新国防”建设。
2018年,英、美两国先后发布国家生物安全战略。美国这份名为《国家生物防御战略》的文件更开宗明义提出:“管理生物事件风险是美国的核心重大利益。”2019年3月,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关于该国在化学和生物安全领域的国家政策基础的法令。在王小理看来:“这表达出美英俄等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对生物安全议题的强烈关注,以及抢占战略制高点的意图。”
生物安全的“事态”增多、“势态”加深和“世态”告紧,也推动我国生物安全进入新的“时态”。王小理说,“时态”的含义类似于窗口期,是说我国正面临提升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能力的时间窗口。“在这个宝贵时机里,倘若以‘过去时’的眼光评估当前的生物安全局面,缺乏对生物安全‘未来时’的前瞻,势必与重大战略机遇失之交臂。”
王小理认为,当下及未来的生物安全已经表现出至少3个新特点:
其一,新的安全风险形态。可以预计,未来生物安全风险来源将更加广泛、相互交叉,危害将进一步累积叠加、聚集扩散。生物风险可与网络安全、经济安全等融合交织,形成网络生物安全、生物经济安全等形态。与此同时,既有生物安全类型也可能呈现全新面貌。
其二,新的危害发生规律。既有生物安全风险形态的发生规律已出现升级换代的趋势。国际知名智库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研究报告指出,利用人工智能技术、3D打印技术、机器人技术等,对传统生物武器加以改进,能使其具有更强的毒性或耐药性、更灵巧的施放方式,更能适应气候、地形等外部环境的变化,具有潜伏期更长、更难以溯源和检测等特点。
其三,新的话语权争夺场域。国际生物安全和生物军控领域涉及国家利益、世界格局,是举足轻重的全球议题。目前,显示度较高、关注生物安全的智库数量超过30家,他们多以西方国家的安全和利益为起点,纵横捭阖重要国际场合,试图掌控生物安全领域的国际话语权和制度、标准制定权。
挑战几何
面对生物安全潜在的巨大风险和战略挤压,守牢我国生物安全疆域需直面应对策略、管理体系、经费投入和科技支撑4大挑战。
挑战之一,应对策略需要拓宽全局眼光。
朱康有说,从抗击SARS、新冠肺炎疫情等表现看,我国相关部门和学术界对生物安全往往还停留在部门性、区域性认识,急需拓展全局性推演、对抗和博弈的视野。
挑战之二,管理体系有待提升协同能力。
杨霄说,生物安全危害防控涉及人员、技术、装备、制度等多方面协同,协调难度大。跟其他国家比,我国的生物安全更牵涉卫健、疾控、生态环境、市场监管、农业农村等多个部门,研究力量也分散在卫生、国防科研、中科院、高校和企业等诸多系统,有多部门、多层级的协调机制,需要不断完善统筹抓总的体制机制。这种实践的部门和研究的力量均相对分散的情况,使防控既有薄弱环节又有重复布局,导致部门之间、系统之间协同性不强、融合度不高,不能完全适应生物安全跨学科、跨部门、跨国界的特点。特别是具体到科学领域,如果科研是科研,政策是政策,容易带来脱节。目前,相关部门、地方政府、科研机构、高校、高精尖企业等已经在推动生物安全资源的有机整合,但因理念、安全、体量、规则等多种原因,能力聚合、聚变的程度仍然受到一定限制。
挑战之三,经费投入有待长效支持。
张卫文说,从政府公共财政预算对生物科技研发投入的体量看,我国近年虽维持一定规模,但投入总量距离美国等的投入水平仍有差距。
2020年,《旗帜》刊发时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白春礼的署名文章。文章认为:“我国在生命健康领域的研发投入与世界强国差距巨大。美国最大的三家药企强生、辉瑞、默沙东的研发投入总额就相当于我国全年研发总支出的10%。科研投入的不足使得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研发能力不强、产品质量不高,一些关键药品和重要医疗设备受制于人。”
这篇题为《为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提供有力科技支撑》的文章,还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例写道:“科技攻关要实现全面和彻底的防护救治,就必须对病毒穷究其源、探明机理,这需要基础研究和多学科交叉融合来支撑,涉及流行病学、病毒学、传染病学、基因学、药物学等众多基础学科。这些基础性工作需要和平时期的长期积累和稳定支持,要着眼于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技术储备等方面构建长效性科技攻关机制。”
挑战之四,科技支撑急需有力加强。
据张卫文介绍,科技创新在防范生物安全风险、维护国家生物安全中的作用非常关键,但无论是基础研究,还是技术水平、产业能力,我国客观上仍与发达国家存在不小差距。我国仍有一些产业发展的基础生物材料、底层生物技术等未能突破,一些产业共性技术供给体系缺失,一些生物安全相关硬件和装备无法自给等。比如关乎患者生命的重症医疗设备ECMO等大型体外生命支持系统,及其上下游原材料和核心部件的研发能力均有不足,相关产品尚不能实现国产有效替代。
储备头部人才
迎接上述4大挑战,离不开高端人才的聚拢。
“我们需要更多生物安全领域从事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等的高端人才,尤其需要思考生物安全这道大命题的战略科学家,特别是在生物安全的重大战略方向、重大科技项目上。”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受访者说。
该受访者认为,生物安全领域缺乏战略科学家的原因并不复杂。一方面,不少研究人员有海外求学背景,他们接受的是西方学术训练,习惯的是西方创新体系,很难突破既有框架。“某种意义上,他们的学术是嫁接在西方主导的学术科研根系上的,根据中国国情转化与创新难度较大。”
另一方面,我国自己培养的生物科技人才,则可能因为“土壤”“气候”等原因,缺少搞战略研究的意愿。“社会期待战略科学家,但大家还没有对战略科学家形成准确的定义,也很难具体描述对战略科学家的期望,这就不容易为战略科学家提供明确的支持。缺少清晰的评价标准、缺少实际的经费支持,战略研究就难得到科研人员追捧。搞战略研究听起来很体面,但可能没利益、没前途。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生物安全的战略研究也面临这些问题。”前述受访对象表示。
在朱康有看来,加快生物安全人才储备、强化生物安全战略研究能力,当务之急是要完善生物安全人才培养体系。他解释说,从现有专业设置看,教育部刚刚调整国家安全为一级学科,生物安全应是一级学科下的二级专业方向,但目前基本上还没有高校开办生物安全系或生物安全专业,这意味着即使有教授相关课程的老师,但在评价、晋升等实际问题上仍存在不确定性,不利于生物安全领域人才的成长。
“生物安全是非常核心、非常有价值的政策研究领域,需要心怀国之大者的有识之士悉心耕耘,也需要适宜的‘土壤’‘气候’环境让这些有识之士获得良好成长。说到底,全球生物安全领域在应对实践上尚没有模板,中国有独特的制度优势,到了我们站出来拿出解决方案的时候。此时此刻,迫切需要有胆有识的人才挺身而出,科学报国、战略报国。”朱康有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