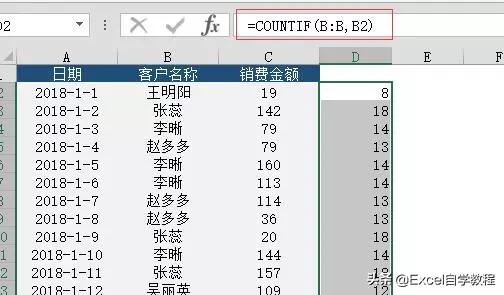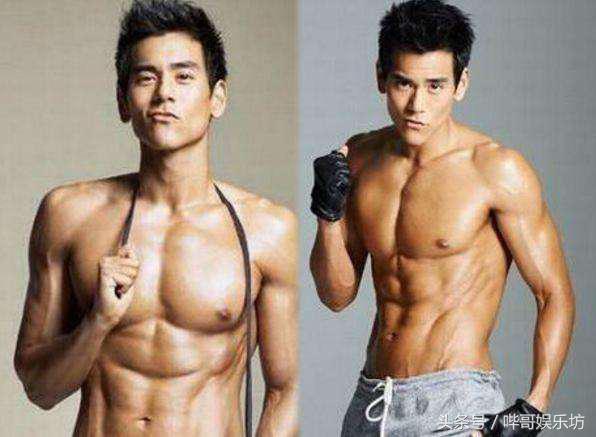较之温庭筠词和柳永词,苏轼词中的女性形象有了很大的拓展。与此相对应,苏轼词女性书写的角度和方式也呈现出与温庭筠词和柳永词不同的一面。总体来看,温庭筠词注重描绘客观的外在事物,极力铺写女子居处的器物陈设和女子的妆容衣饰;柳永词侧重描摹女子丰富的内心世界,表现女子大胆追求世俗情爱的强烈愿望;苏轼词重视传达女子的神韵气质,赞美女子超凡脱俗的风姿和高尚美好的品质。
温庭筠词“富有装饰性,追求装饰效果”,具有错彩镂金的特点。温庭筠在书写女性时,常常把女子的活动范围限定在室内,对室内的器物陈设进行不厌其烦的铺写,对女子的妆容衣饰进行细腻入微的描摹,而很少直接表现女子内心深藏着的情感,“论其笔法,则是客观的描写,非主观的抒情”。如果想知道词中究竟要表现什么样的感情,往往需要读者自己去体会和联想。最典型的是《菩萨蛮》:
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鹧鸪。
词中的“鬓云”“香腮”“蛾眉”“绣罗襦”“金鹧鸪”等一系列词语,都是对女子妆容衣饰的客观描摹,只有“懒起”“弄妆”“梳洗”等几个词语写到了女子的动作。女子慵懒地起床,弄妆画眉,梳洗打扮,她内心深处到底在想什么,作者并没有明说,需要读者自己去想象和补充,因此不同的读者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清人张惠言从中读出“感士不遇”和“《离骚》初服之意”,近人唐圭璋从中读出“孤独之哀与膏沐谁容之感”或许就与温庭筠词本身的歧义性有关。
与温庭筠词的错彩镂金、雕缋满眼不同,柳永无意于对女子的妆容衣饰进行精雕细刻的铺写,他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描摹女子的内心上,注重表现下层女子大胆追求世俗情爱的强烈愿望。最典型的当属《定风波慢》:
自春来、惨绿愁红,芳心是事可可。日上花梢,莺穿柳带,犹压香衾卧。暖酥消,腻云亸。终日厌厌倦梳裹。无那。恨薄情一去,音书无个。早知恁么。悔当初、不把雕鞍锁。向鸡窗、只与蛮笺象管,拘束教吟课。镇相随,莫抛躲。针线闲拈伴伊坐。和我。免使年少,光阴虚过。
此词以通俗浅近的语言,描摹了一个独守空闺的下层女子的内心世界。由于独守空闺,女子内心寂寞无聊,即使看到春天的美景也觉得那是“惨绿愁红”。红日高照,她仍然高卧不起,秀发散乱,她也懒得梳妆打扮。如果说词上片的“暖酥消,腻云亸。终日厌厌倦梳裹”还带有温庭筠《菩萨蛮》中“懒起画峨眉,弄妆梳洗迟”的痕迹的话,那么词的下片则完全是温庭筠词未曾有过的景象了———写女子内心强烈的悔恨,近乎内心独白。她后恨当初没有把情人的宝马锁起来,好让他与自己日夜相伴,长相厮守,免得光阴虚度。
苏轼《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其一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他认为,赋诗论画不能一味追求形貌的相似,而要讲究生动传神。在这种文艺思想的影响下,与温庭筠和柳永相比,苏轼在书写女性时,相对减少了对女子妆容衣饰的描摹,而增加了对女子神韵气质的刻画,往往能够做到生动传神,曲尽其妙。如《浣溪沙》:
旋抹红妆看使君。三三五五棘篱门。相挨踏破蒨罗裙。
通过“旋抹”“看”“相挨”“踏破”这一系列动词,把农村女子的天真活泼、可爱好奇刻画得十分生动传神。她们匆匆忙忙地抹上红妆,三三五五地挤在棘篱门前。为了一睹使君的风采,甚至踏破了别人的红罗裙。
苏轼在描摹女子的舞姿时,也往往不拘泥于形似,而是善于运用巧妙的比喻和新奇的联想,生动地传达出女子高妙超凡的神韵和风姿。下面三首《南歌子》皆是如此:
空阔轻红歇,风和约柳春。蓬山才调最清新。胜似缠头千锦、共藏珍。
柳絮风前转,梅花雪里春。鸳鸯翡翠两争新。但得周郎一顾、胜珠珍。
趁拍鸾飞镜,回身燕漾空。莫翻红袖过帘栊。怕被杨花勾引、嫁东风。
第一首,“空阔轻红歇,风和约柳春”两句,突出女子舞姿的轻盈优美,仿佛轻红从空中飘落,仿佛细柳在春风里摇曳。第二首,“柳絮风前转,梅花雪里春”两句亦是如此,突出女子的体态轻盈、婀娜多姿。第三首,前两句是比喻,写女子舞姿灵动,如鸾鸟在镜中飞舞,如燕子在空中飞荡。后三句是想象,担心女子体态太过轻盈,会像杨花一样随东风飘去。
此外,温庭筠和柳永在书写女性时,往往带有强烈的男性的观赏和把玩的色彩。与温庭筠和柳永不同,苏轼有着比较进步的女性观,对女性抱有尊重和欣赏的态度。在苏轼心目中,女性往往是美好的化身,具有非凡的魅力。因此,他常常在词中赞美女子高尚美好的品格。如《定风波》:
谁羡人间琢玉郎。天应乞与点酥娘。尽道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万里归来颜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这首词是苏轼为友人王定国的歌妓柔奴而作,赞美柔奴的高尚品质。“尽道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运用夸张和想象的手法,突出柔奴歌技的高超绝妙,她的美妙歌声像清风拂过一般,可以使岭南炎海变得清凉。“万里归来颜愈少”,写柔奴对岭南艰苦的生活甘之如饴,因此归来后仍然容光焕发,甚至看起来更加年轻。“此心安处是吾乡”,赞美柔奴身处逆境仍然乐观旷达的可贵精神。
又如《西江月》:
玉骨那愁瘴雾,冰姿自有仙风。海仙时遣探芳丛。倒挂绿毛幺凤。素面翻嫌粉涴,洗妆不褪唇红。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
这首词是苏轼为悼念朝云而作。全词借咏梅以悼亡,运用象征手法,巧妙地将咏梅和怀人融为一体。既写出了梅花不惧岭南瘴雾、傲然挺立的神仙风姿,又赞美了朝云不畏岭南瘴雾的顽强精神和自然淡雅的高洁品格。
(本文内容来源于网络 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