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会说脏话?》是埃玛·伯恩(Emma Byrne)的第一本书,之前看到有评论认为这本书不过是关于脏话研究的一堆文献综述——那对于像我们这样的外行来说,还真是本带感的研究综述啊,从话题到文风都相当“读者友好”。至于你正在看的这篇综述之综述,托作者的福,希望也不会太闷。
脏话脱口而出——信手拈来各式关于宗教、生殖、愚蠢、排泄物以及国籍背景的敏感词汇,以求一针见血、振聋发聩。“爆粗口”是发狠,也是取乐;惹人讨厌,也荒谬可笑;是口头禅,也是无事生非。(杰弗里·休斯)
这段引文出现在全书的开头,读完书回过头来看,会发现其对于脏话文化关键点的覆盖着实全面。作者在书中曾多次表示,写这样一本书不是为了鼓励说脏话,而是对骂脏话现象的探询:人为什么骂,怎么骂,以及脏话揭示了人的哪些本质。事实上,神经科学、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等都已为此贡献了大量有趣的研究成果。

《我们为什么会说脏话?》,[英]埃玛·伯恩著,吉永劭译,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7月。
作者在翻阅了数百项相关研究后,得到了两条学术上通用的脏话定义:第一,情绪激奋的情况下使用的词语;第二,指代普遍禁忌的词语。
第一条提示了脏话与情绪的关系,“它是人类情绪的压力阀”,既可以“幻化为一道无形的剑气去挫伤对方的锐气”,也有利于减轻人的焦躁感,排遣负面情绪,书中甚至还有专章介绍疼痛与脏话的关系——实验显示,骂脏话可以减轻痛感,而且“语言上火力要够大,止痛效果才会够强”。研究者猜想,脏话之所以有助于忍耐痛觉,是因为它作了两种情绪的引子,即恐惧和暴力冲动。
而脏话之所以有种种“情感上的震慑效果”则取决于第二条所提示的脏话的本质——禁忌。以英语脏话的“四巨头”而言——宗教类、性交类、排泄物类和污蔑歧视类,情节或有轻重,但无不是语言的“犯忌”。因禁忌是社会文化的产物,因此,一方面,脏话在时间上会随历史发展和语言变迁而发展变迁,比如,在维多利亚女皇治下拘束极盛的时期,《牛津英语词典》中连“裤子”(trousers)一词都被归入“不堪言”之列。而每当社会的价值观发生变化,也总会有新的脏话尾随而至。
另一方面,在地域上,脏话也有极大的在地性,“对比全世界7000余种语言中的咒骂习语,不论在类型、用法还是使用频率上都存在广泛的差异性”,例如,俄语的词形变化繁复,往往能将个别脏字演绎得出神入化,而日本文化总体上缺少“排泄物禁忌”,因此诸如“微笑便便”一类的表情文字还能轻松走红。同为英语世界,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爱尔兰与美国、加拿大等地骂人的习俗也大相径庭。
与此相关,还可引申到脏话与母语之间的关系。虽然,人的确是在用非母语说脏话时面临较小的心理压力,但另一方面,大家又普遍觉得,不管外语说得多流利,还是用母语骂脏话更带劲儿,“脏话的无形气剑要出鞘,既得靠语言上的流利,同时情感上也得通畅”,更不能犹疑于“到底骂得过粗还是不够力度”。
至于,为什么要骂脏话,书中提到了包括排遣负面情绪、贬低他人以及强调正面感触等方面,最后一条涉及的是脏话的修辞功能,即加强语气,好比“非常”“真”这样的修饰词。而与这些显性功能相比,更微妙的是脏话的社交功能。
书中用不小的篇幅讨论了工作场所的脏话问题,“工作场合是否该容忍脏话,向来是争论的焦点”,而以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为首的学界研究却揭示了一条别样的规律:“在很多情况下,一个工作团队能够一同骂人,也就能够并肩协作。”工作场合常见的玩笑话,被认为多用于拉近同事间的关系,或互相打气。
这一点在对女性与脏话的课题研究中,同样得到了印证。研究者发现:如果工作场合以脏话为常,那么女性自然会考虑到跟上男性的步伐,也学着骂脏话。受访的女性们多说,她们讲脏话多半是出于人际关系的考虑,比如幽默,比如交友。作者因此调侃说:“所以与其说脏话是粗鲁的表现,不如说如今的脏话已经成为某种意义上的礼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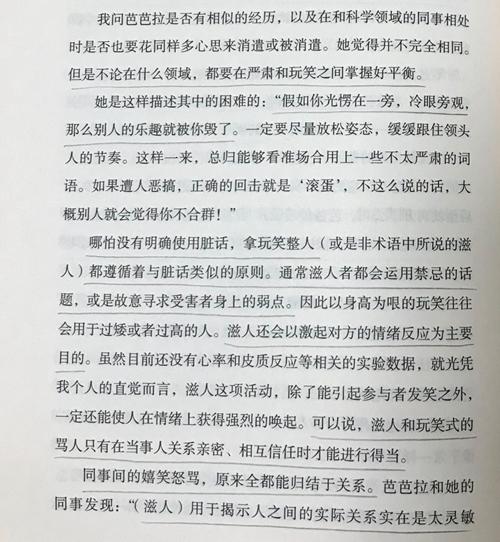
当然,问题的关键依然在于如何掌握好分寸,作者援引芭芭拉·普勒斯特(Barbara Plester)博士的研究成果说:“同事间的嬉笑怒骂,原来全都能归结于关系。(滋人)用于揭示人之间的实际关系实在是太灵敏了——只要两个人是过得去的朋友,那么在相互开玩笑时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有什么红线不能碰,全部能够心照不宣。”玩笑之中是否能留一点“余地”,也是很重要的。芭芭拉还注意到,“开人家的玩笑想要不冒犯到对方,要么不去碰敏感的话题,自我调侃一番再讲别人,要么彻底出格,那样也就没有人当真了”。
这里涉及到讲脏话真正“内涵”的层面了,对此,作者在另一章关于黑猩猩的脏话研究中的一段总结倒是很好的注脚:
不论黑猩猩还是人,要说脏话,必然就要洞悉他人的心理,并对思想存有成体系的理解,如此才能预判到语言的效力;情感上也必须活跃,没有情绪的体验,脏话也就无从出口;头脑须要复杂到能够熟知社会的禁忌,如果不能对区分不同行为有一些哪怕朦胧的概念,羞耻和禁忌也就无从谈起,语言也就“脏”不起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