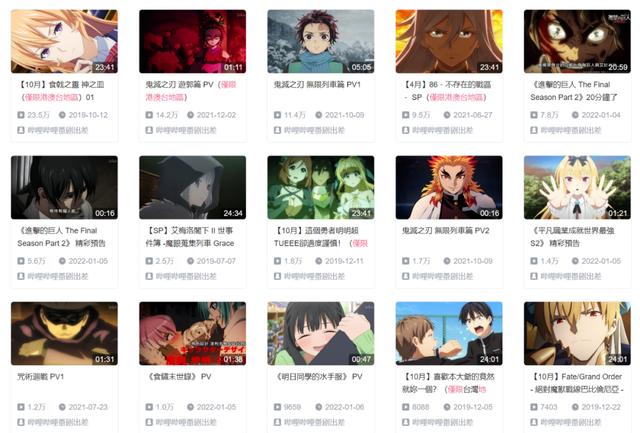Science once communicated in a polyglot of tongues, but now English rules alone. How did this happen – and at what cost?
如果你能读懂这句话,你就可以和科学家交谈了。呃,可能关于他(她)研究的细节你听不太懂,但至少你们有了共同的语言基础。如今,包括物理、化学、生物和地质学在内的自然科学领域,其信息交流绝大部分都以英语作为媒介,像是出版书籍、举办会议、电子邮件、Skype上的研究合作。关于这一点,你随便在吉隆坡(译者注:马来西亚首都)、蒙得维的亚(译者注:乌拉圭首都)或是海法(译者注:以色列港口城市)任意一个科研机构的大厅里走走看看就能证实。当代科学以英语的使用为主。
更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当代科学只使用这一门语言。英语的使用程度如此之高,以至于其他语言全都被弃置一旁。而一个世纪前,西方科学界的研究者们不仅懂一些英语,还能够用法德两种语言进行阅读写作和交流,更有人还掌握一些冷僻的小语种,诸如较晚兴起的俄语和经历了大幅衰落的意大利语。
当代科学曾经的多语特征大概会让人有点不得其解。使用单一语种肯定更高效啊!为了制造出合成苯以及苯的衍生物,过去的科学家得浪费多少时间去读写三种语言啊?如果所有人都使用同一种语言,就不会存在翻译带来的争议,比如在几种语言都记载了相同科研发现的情况下搞清楚谁是最先发现者的问题,教育资源的浪费也会明显减少。从这一点看,正是由于人们的精力由此能够集中于科学本身而非诸如语言一类的表面功夫,现代科学发展的速度才能如此之快。
如果使用英语的人本身就以英语为母语,那这一点倒无可厚非,但当今世界上大多数科学家的母语并非英语。如果把他们花在学习语言上的时间考虑进来,英语独霸天下也不比曾经的多语并行效率更高,无非是两种不一样的低效模式罢了。语言学习和翻译工作仍然如火如荼,只不过是在英国、澳大利亚和美国看不到而已。“毡”上的“针”不是被拔掉了,只是被移了个地方。
如今的科学家们无一例外都被这个单语操控的世界罩得严严实实。科研发展则像个搅拌发酵机,高速运作下,各学科原本的模样都被逐渐忘记。科学不是总这样?的确,科学并非一直如此。然而,只有老一辈的科学家们才勾勒得出科学过去的模样了。科学家和人文学者往往认为,英语取代了德语的在科学界的垄断地位,再往前是法语(被德语取代),拉丁语(被法语取代),拉丁语往前追根溯源就到了西方文明的源泉,在这些人的理解中,那是希腊语的时代。由此可见,科学的发展正是语言的更朝换代,这一点从表面上看的确有些说服力,实则不然,且从古至今都是歪理。
从大处着眼,西方科学界无外乎两种语言政权:多语统治和单语统治。后者历史较短,20世纪20年代才逐渐兴起,且直到70年代才取代了过去数个世纪间一直沿用的多语体制。科学界成了英语的世界,但在这个单语体制下成长起来的最早一辈科学家如今尚在。想要知道这个重大的变革是怎样发生的,我们就得回到故事的开头。
15世纪的西欧,自然哲学和自然历史(19世纪后被统称为“科学”)是多语统治的两大基本领域。当然,这得把中世纪鼎盛时期和文艺复兴时期学术界对拉丁文的青睐排除在外。
拉丁文的异军突起和多语体系并无冲突,相反,前者倒是后者的一个佐证。任何一个文艺复兴时期的优秀人文学者,或是中世纪盛期杰出的经院哲学家都知道,以拉丁文记载自然哲学的发展,其历史可以追溯到罗马的光辉岁月(西塞罗和塞内加都曾在该领域留下不朽的杰作)。但同样的这群人也明白,在罗马最后的岁月里,学术界的统治语言并非拉丁语而是希腊语。他们还知道,从罗马的衰落到他们的世纪到来之前,自然科学的文献更多以阿拉伯语记载,而非这两种古典语言。将自然科学领域的典籍从阿拉伯语译入拉丁文的活动引发了西方世界的学习热潮。博学者深知,学习本身就是一种多语活动。
拉丁文因而成为了人们在对世间万物抒发个人见解时的有力工具,但懂拉丁语的人会的都不止这一种语言。
那时,人们的生活用语也是多元化的。除了少数奇人受父母过于附庸风雅的影响(蒙田自称就是这一类人),没人把拉丁文当成是母语来学,也鲜有人在口头交流中使用拉丁文。拉丁文是为书面学问而服务的,但包括鹿特丹的伊拉斯谟在内,所有使用拉丁语的文人在与仆人、家人及贵族阶级的日常交流中也常常会将拉丁语与其他语言混合使用。拉丁文因而成为了一种媒介,用以拉近不同语言群体的距离。对此,人们大都心中有数,没什么意见。尽管由于拉丁文的掌握对教育有更高的要求,一定阶层以下的人群确实会被排除在外,但它却能够轻易的跨越宗派和政治上的分歧:拉丁文在清教徒中得到了广泛的使用(他们对拉丁文的运用往往比天主教徒更加优雅得体)。晚至18世纪,拉丁文甚至还传入了当时信奉东正教的俄罗斯,成为新建的俄罗斯科学院列宁格勒科学中心的学术用语。
最为重要的一点也许是,正是因为拉丁语不是任何一个国家的母语,欧洲和阿拉伯世界的所有学者都能平等的使用,而不存在这种语言“专属”于某一方的问题。上述的各种原因使得拉丁语成为了人们对世间万象各抒己见的绝佳工具。但使用拉丁语的文人雅士都绝非只会这一门语言,他们会因受众的不同而选择不同的语言进行交流。当有需要与国外的化学家进行书面交流时,瑞典人倾向于用拉丁文书写;当谈话对象是采矿工程师时,他们则会选择瑞典语交谈。
然而,作为“科学界革命”中的一个重要事件,这种体制在17世纪中期逐步没落。1610年,伽利略在发表的《星际信使》一书中提出了木星卫星的发现。尽管伽利略用拉丁语写就了此书,但在此之后,他的大部分作品转而用意大利文写作,以便寻求更多本土的资助和支持。牛顿以拉丁文写就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于1687年问世,但1704年的《光学》却是用英语撰写的。(1706年被译成拉丁文)
与此同时,整个欧洲的学者们逐渐开始使用五花八门的语言,为了方便学术交流,拉丁文和法文的翻译也盛极一时。到18世纪末,化学、物理、生理学和植物学领域,各种不同语言的著作大量涌现,除了英法德以外,也有意大利语、荷兰语、瑞典语、丹麦语和其他语言。但直到19世纪的前叶,许多学术精英们仍旧选用拉丁语(德国数学家约翰·卡尔·弗里德里希·高斯至少在十九世纪初都始终坚持用拉丁文做学术记录,这种语言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凯撒大帝)。现代科学即脱胎于文艺复兴时期多语种的大杂烩。
但人们对效率问题的高度关心,伴随着19世纪欧洲的工业革命,使得历经好几个世纪的多语体制逐渐地位不保。如果并非为了学术研究,而仅仅只是了解自然科学的前沿进展就要投入大把时间去学习一门语言,这看起来像是在浪费时间。因此到了1850年左右,学术语言界慢慢只剩下英语、法语和德语,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各自的著作占有率几乎不相上下(但在特定的学术领域却分工不同:到世纪末,德语在化学界的使用远超其他语言)。
19世纪,现代民族主义在工业化的蓬勃发展中席卷欧洲。为了响应19世纪现代化的需求,诗人和知识分子发展并改造了各地方言。一边是农民阶级的日常用语,一边是曲高和寡的文学及自然科学对语言的精益求精,如何对两者加以调和是摆在这些语言捍卫者们面前的一个巨大挑战。各种语言在文艺界的发展是有目共睹的:19世纪下半叶,现代匈牙利语、捷克语、意大利语、希伯来语、波兰语和其他语言都发展得如火如荼,但科学界对高效率的不懈追求却或多或少的阻碍了多种语言的百花齐放,仅有俄语冲破阻力成为了科学论文的重要语言,即使只有较小的一部分。小语种的拥趸们对自己的语言被排除在外有微辞,而三大语种的使用者也因为要学习其他两种语言而牢骚不断。
毫无疑问,三种语言的并存是一种累赘。科学研究单语化的支持者们提出了世界语的概念,其依据正是几个世纪前盛极一时,兼具普及性和中立性的拉丁语。这些支持者们言之凿凿,据理力争,你在如今英语使用的拥护者身那里也能看到同样的风采。世界语的粉丝中不乏知名人士,例如1909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弗里德里希·威廉·奥斯特瓦尔德和丹麦语言学家奥托·叶斯柏森。但正当他们热情高涨的转向更为极端的人工语言项目时,却很快被看作是乌托邦空想主义者而遭遗弃。在当时,所有人都深信科学如果不拥护多语体系便无法延续。
后来,事情显然发生了变化。我们正生活在世界语的理想国中,只不过自然科学界的这种世界语变成了英语而已。且作为某些超级大国的母语,英语的中立性所剩无几。原来的多语科学体系究竟发生了什么?它坍塌了。确切地说,它被肢解了。1914年爆发在同盟国(德国,奥匈帝国)和协约国(英国,法国,俄国)之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带来伤亡的同时也摧毁了博爱互助的国际主义设想。德国科学家加入了其他知识分子的行列,大肆赞美德国发动战争的动机,英法的科学家都注意到了这一点。
战后,国际研究协会在战胜国的支持下成立。美国也成为了其中一员,但卷入了十月革命巨大漩涡的俄国却被排除在外。协会的成立引发了一战同盟国科学家的联合抵制。于19世纪20年代初成立的新国际科学机构仍将战败德国的科学家排除在外。而接下来的几十年中,德语在主流科研语言中销声匿迹也归咎于这种长期的缺席,在欧洲的部分地区,三分天下的局面演变为了双雄争霸。如此窘境下,德国人重又开始效忠母语。多语体制逐渐出现裂纹,而最终将它打碎的是美国人。
自从1917年4月美国介入战争之后,“德”色变的恐惧使德语在美国国内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德语在爱荷华州、俄亥俄州、内布拉斯加州和其他一些州曾是仅次于英语的第二大交流语言(因为那里曾涌入大量的中欧移民),现在却被勒令退出,而禁令在停战纪念日(译者注:每年的11月11日,为了纪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其他战争中牺牲的军人与平民的纪念节日。)之后才逐渐被放宽。到1923年,超过半数的州限制了德语在公共领域的使用,包括电报、电话、以及儿童教育。
同年,最高法院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内布拉斯加州案件(译者注:1923年,最高法院在Meyer v. Nebraska一案中,宣布内布拉斯加州一项法律违宪无效。因为该项法律禁止在国民小学教授英语以外的外国语言。法院认为这一法律不合理地侵犯了教学自由,也侵犯了父母为子女教育的权利。这两种权利都是宪法第14条修正案所加以保障的)中推翻了上述对德语的禁令。然而已经于事无补,外语教育遭受的这场浩劫甚至也殃及到了法语和西班牙语,导致整整一个时代及后来的科学家都生活在一个几乎与外语绝缘的环境中。19世纪20年代中期,当德国和奥地利的物理学家发表关于量子力学的最新进展时,美国的物理学家之所以还能够读懂德国文献,全都得归功于穿越大西洋前往魏玛共和国求学的美国人迫于生活所需,不得不学到了点德语。
然而,不久之后,美国人留德的风潮就发生了逆转,越来越多的德国人开始前往美国。1933年,阿道夫•希特勒迅速地解雇了“非雅利安人”和左倾的教授,给德国的科学事业发展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后来他们中一些幸运的人移居到了国外。但是这些犹太科学家也遭遇到了很多挑战。例如,曾任爱因斯坦助手的科尼利厄斯·兰佐斯就曾经在用英语出版时遇到了困难。不仅仅是由于其主题敏感,还因为那个在无数人身上用过的理由:英语太烂。尽管他的好友已经帮他从头到尾进行了修订。就连爱因斯坦也要依赖于翻译员和研究合作者的帮助。
与这些犹太科学家同一时期的德国物理学家詹姆斯•弗兰克在移居到芝加哥后花了不少时间才总算慢慢适应了英语的使用。定居在爱丁堡的马克斯•玻恩则由于年轻时英语学得有模有样而将这门语言运用得游刃有余。很多像他们一样的大人物都曾提及自己学习一门新语言的痛苦经历。正如一些日本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自传中所描述的那样,第一次用英语出版自己的研究发现,在日本群岛之外打响名声,对于他们而言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反观19世纪30年代的德国,当时希特勒拒绝了大多数外国学生的签证。切断他们通往德国大学的道路也就意味着进一步阻碍了德语的普及和发展, 这比一战所造成的影响更为深刻。
随着冷战的深入,使用俄语发表文章已经被打上了鲜明了的政治色彩。
二战后,这个问题又逐渐和人口特征以及地缘政治扯上了关系。19世纪版图不断向外延伸的大英帝国开始与多种语言打交道。相比较下,20世纪冉冉升起的美国没对科学家的外语能力提出什么要求。战后苏联涌现的一大批科学家和工程师成为了美国新的科技竞技对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俄语作为世界上25%的自然科学论文的语言,成为紧随英语(占60%)之后的科学界第二大用语。到了七十年代,俄语出版物的比例随着英语一家独大的地位逐渐形成而下降。
为了能够自主掌握科学,美国人与其说是不能,不如说是拒绝为了学术需要去学习俄语,更不用说其他外语了。加之在大西洋彼岸的英语和非英语国家输出美式科研体系的策略,美国人就能更好地掌控这些国家的科学发展,从而进一步推进科学界的英语化。当然,欧洲学者,拉美学者和说其他语言的学者自愿加入这个新的单一语种体系也在科学界英语化进程中起到了作用。为了得到相关领域佼佼者的认同,诸如荷兰人、斯堪的纳维亚人和伊比利亚人一类这些来自非英语国家的科学家都不再使用法语或德语出版学术论文,转而使用英语。更吊诡的是,要是哪个科学家用自己的母语发表研究发现倒是会被认为是民族特殊主义。例如,除了母语为法语的人,没有人用法语发表;德语的情况也大同小异。
随着冷战的深入,使用俄语发表文章已经被打上了鲜明了的政治色彩。而与此同时,全世界科学家学习英语的热情却有增无减。不过我们认为,这一科学史上不寻常的发展其实并没有很强政治性可言,只是他们的自身需要罢了。到了80年代早期,世界上80%以上的自然科学论文都使用英语。现在,这个数字在99%上下浮动。
但是这又如何呢?或许提倡效率至上的人确实有他的道理,现今单一语种体制下科学界的确比以往更好—科技的蓬勃发展就是最好的证据。但我们也不应忘记为此付出的代价。1869年,门捷列夫发现了元素周期表。但因为此项发现是用俄语而非德语出版的,他差点和其应得的赞誉擦肩而过。如今,要是哪个人在一个发展迅猛的领域中,发表一篇非英语文章在一份二三流的期刊上,他的作品可能很快就会被淹没在纸堆里。
法国数学家常常自豪地用法语发表作品,因为他们认为法语严谨的语言结构有助于英语母语者的理解,多语也不错。但如果是在一些重实践而轻理论的科学研究中,多语就显得有些多余了。曾经有多少前途无量的学生在多变量微积分上游韧有余,却因为卡在了英语学习上,而与科学事业无缘。而且当世界上大部分教科书,甚至连高中的教科书都使用英语编写后,这个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市场经济机制下,使用捷克语或者斯瓦希里语编写的微生物学教科书早已所剩无几了吧?科学的单语体制是要付出代价的。
且这种局面一旦形成就会非常稳定。鉴于现状是前所未见的,我们很难预测科学界将来的事。科学领域的学术交流从未曾出现过像今天这样的单语体制,而现在,作为世界上经济和军事霸主的母语,英语已然渗入到了全球每一个角落。
不过有两点是确切的。首先,维持一个如此庞大的单语体系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需要在非英语国家的语言教育和翻译工作上投入巨大的资源。其次,就算那些英语国家明天一下子消失了,仅仅凭借着人们对既有的一切产生的依赖,英语仍然会是科学界的重要语言。科学家基于以往的知识体系提出的沉锚效应(译者注:心理学名词,指的是人们在对某人某事做出判断时,易受第一印象或第一信息支配,就像沉入海底的锚一样把人们的思想固定在某处)既解释了以前的多语种体系,又解释了现在的单一语种体系都是适用的。
问问你身边的科学工作者,她也会认同这个观点的。
翻译:刘源琦/汤茜童/杨玥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