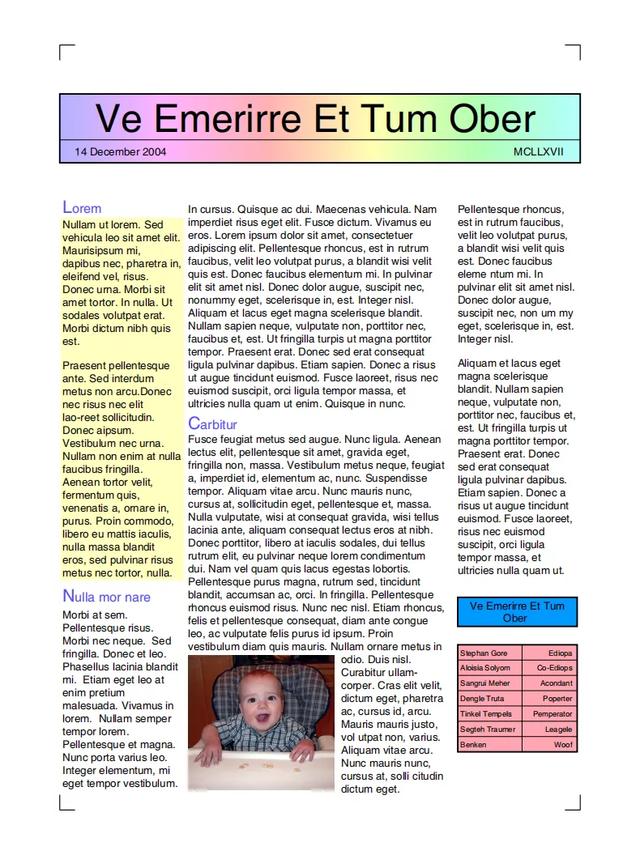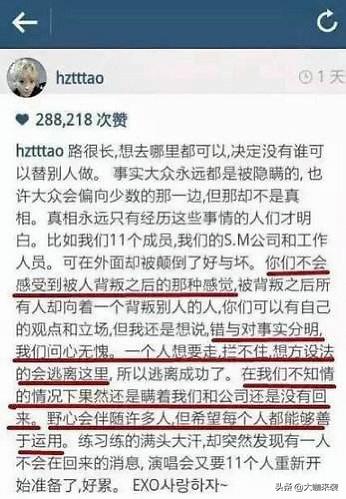1980年代有理想、有路径,青年人可以肆意的选择自己的人生路向,当然结果也由他们自己负责,他们生于50年代末期、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到1990年代,当70末和80初这一批独生子女开始缓慢而坚定的登上历史舞台之时,他们发现从初中起自己的读物,都已经被父祖辈框定,课本之外,几乎全是禁品,考试的压力和邻居家的好孩子和传说中的学习小能手,成为他们精神世界难以承受的重,他们的父母还基本上没有成为农民工的压力,农转非非常难、小城市向大城市的转移之路基本不通,于是他们的学习成绩几乎成为改变自己及家庭命运的唯一途径,同时他们绝大多数人没有兄弟姐妹可以平衡、缓冲家庭内部的压力。公开的叛逆者当然有,然而数量比已经下挫到水位以下。他们,特别是她们。那个年代的故事背景,我是相当了解的,1991到1994年读初中,1994年到1997年就读师范学校(本片中一个女生读卫校一个读高中),1997年毕业后再回到母校教学,整个1990年代都与70末、80初以及85后在一起。
《少女哪吒》描述的是1990年代江边小城两个女生曾经的友谊,以及不知如何就结束并消失的他人。在1990年代的现场,能够拥有的只有以梦为马,在白马过隙般短暂的青春时光里,享受一些彼此依靠(和伤害)的微温,那个年龄段的友谊,炽烈、无目的、神经质,似乎有毒,但却兴奋,恍惚又麻木,他们深深的希望爱着某个东西,亲人、同学、死党或者某个异性,意象往往跳脱。他们的业余生活,也没有太多意思,1980年代的露天电影热潮已经悄然消逝,21世纪的网络和移动互联网生涯还没从地平线上爬起,无非就是汪国真、席慕蓉、三毛、琼瑶等等,还好在偏僻落后的地方也有盗版书的存在,波浪到她们心扉的,已经不是最先进的文化或者思潮,然而这绝对还是她们想象无远弗届的他乡的最好渠道。少年时期是对童年价值重估的时代,往往遇到了什么读物、结识了怎样的人,三观就随之发生重大的变化,这一切都有着巨大的不明确性。小时候觉得漫长的巷子,雨季里也很有感觉,长大之后再看,不过是低矮的、破败的、过时的胡同。
无论学习成绩好坏,都有些迷惘,第一批独生子女(包括但不限于小镇青年)既没能亲身经验过共和国前三十年红的冲击,又没有建立起21世纪以成功学为单向羡慕嫉妒恨的养成模式,1990年代整个社会都在沉默低语中向前看(至于这个前,是金钱还是前途,或者是自我实现的人生,都是相当含糊)。《少女哪吒》的叙事是缓慢的古典风格,但是态度又机器锐利,撕开现实与想象的痛点。少女与哪吒,还是两个少女都是哪吒,不过一个以马为梦,一个以梦为马,远方与诗的成为世俗中人,家乡与戏的继续长不大的决绝,两种成长都可以说是性感的,她们在现实主义泥泞中试图开出浪漫唯美的花,在无限逼近世界末的时空里,内心的炽热与外在的荒凉,最终冰破、路远,各自昂扬。
葡萄牙诗人费尔南多·佩索阿在《惶然录》里说,“有一些毒药是必要的,轻微的毒药组成了灵魂的配方。”《少女哪吒》里,青春期少女可以说得了一种哪吒综合征,美好、残忍与不忿的精神里,有一些内生的毒药,她们的友谊是自我保护的城墙,彼此有信任也有怀疑。是对既成事实的逆反,也是对现实的苦闷,无能为力于此岸的世界,彼岸只在于远眺与想象,更好地生活或可望却永不可及。成年人的世界,似乎充斥着足够的谎言,溢出来的全都是不负责任,凡是能够接触到的,基本上都是粗鄙、荒芜、失真(这些当然是未成年少女对于世界的错误判断,然而自觉是离婚家庭缺乏足够温暖的少女,对于世界的整体判断)。于是,本片片名中哪吒的意象便有了20世纪末的意义,王晓冰以她的形式“割肉还母、剔骨还父”,最终杳然不可寻。而插班生李小路则最终在成年人的世界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青春期哪吒综合征不治而愈。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说“人就是一种领会着存在的在者”。《少女哪吒》里的两个少女,她们本能的以为对方是同类,领会存在的能力有,然而却不能把握,她们自认为“诚实的活着”、“活出自我”,更多是以梦为马的自我期许,确认彼此是异类是对自我的肯定。然而理想的生活往往不是正在过着的生活,也难以是即将迎来、争取到的生活,白马非马才是人生的常态,到卫校上学的王小冰继续迷失,终于在面对人口普查员时选择了如何去逃离现实,也许是失踪,更有可能是自杀,世界上人口那么多,我已经不想去看看,少我一个不少多我一个不多,生无可恋是一种悲恸的生命观,曾经看到过白马的她,过隙了。
与现实格格不入的少女,要好时可以下定决心独身一辈子,也要和对方要好,然而彼此是狐狸的真诚还是刺猬的坚毅,都难以判断,她们在特定时刻内的最大公约数,只能是与世俗的不和解。所谓世俗,往往是家庭的不幸,也容易绑架父母的感情。她们和观众都发现,大人们板着脸、说着永远正确的话,沉重的世界上着过重的油彩。王小冰的不快乐,很大程度上她觉得父母离婚导致、抚养自己的妈妈又似乎有着自己的快乐(喜欢唱戏的妈妈由陈瑾扮演),如此观察人生的视角显然又是一种错位的人生观,态度以自我为中心,世界就非常容易塌缩,最终吞噬自己的梦想和未来,王小冰的现实断裂之后,留给了曾经的挚友一铁盒子烟蒂。抽烟、吸毒、纹身、说脏话、当果儿,等等,曾经被一些人定义为好女孩做的事,只要她自己认为自己是好女孩那么就是,这样的逻辑对于承受能力不同的人来说,后果差异极大。李晓路则去了远方,也许有诗的世界,帝都的漂泊生活,世俗、俗套、套中人的生活,很有可能是治愈外省文艺女青年的绝招。在倔强绝强,他人并不会侧目,反而可以放下身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