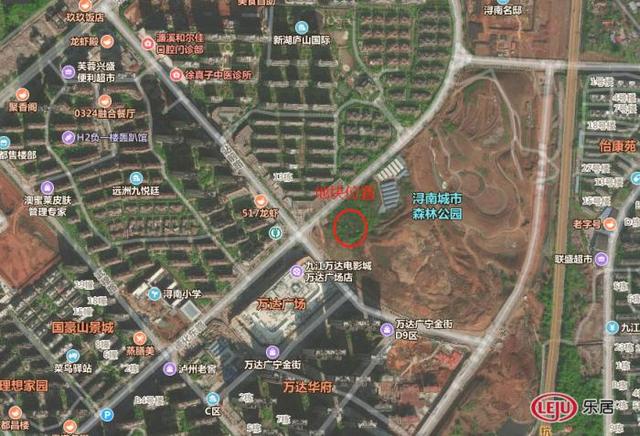大洋网讯 走出广州农讲所地铁站,穿过熙攘车道,拐进德仁里的窄巷,漫步在密布的现代居民楼间,一座红墙琉璃瓦的古老楼阁会有点突兀地出现在眼前。
这座看似不起眼的“红楼”,就是清代两广科举第一考场——广东贡院的明远楼。当年,密密麻麻的号舍分布四周,主考官在此登高监考。如今,红楼一度成为新学堂的图书室、古物陈列馆、广东省博物馆的附属建筑,见证了广东近代教育改革的新历程。

明远楼前,广东实验中学校舍书声琅琅;明远楼后,中山图书馆书海茫茫。

广东贡院布局模型

小朋友们参观明远楼。
贡院小史:
号舍多达11708间 并称清代四大贡院
贡院是中国古代科举考试举行省一级乡试的场所。据《广东通志》和《广州府志》记载,广东贡院始建于南宋淳祐十年(1250年),元朝时被毁坏了。明朝洪武、永乐年间,考生们只能在光孝寺的临时搭起的帐篷号舍里参加乡试,直到宣德元年(1426年),新贡院才建起来,后来在朝代更迭中被战火夷为平地。
清朝早期,广东乡试的考场先借地光孝寺,再借地藩署,后改借旧总兵府。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政府“以崇文重士为急务”,广东却连一个乡试的固定场所都还没有,这让广东巡抚李士祯非常着急。他亲自勘踏,终于在城东南隅承恩里(即今天广州市文明路一带)找到一块郁郁葱葱的空旷之地,决定在此重建广东贡院。建成后的贡院南临城垣,东依濠涌,“中为明远楼,东、西号舍五千间”。
1821年,两广总督阮元为了学子有更好的考试环境,带头捐出俸禄引官员、绅士慷慨解囊,把号舍增至7630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时,英国军舰进逼广州,军队选在广东贡院扎营,士兵就住在号舍里,撤退后,几乎一半号舍都被拆毁,污水横流。见次年乡试在即,十三行富商潘仕成捐资修葺,并增建号舍565间,至8000多间。1857年,贡院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再遭毁灭,只有明远楼幸存。广东总督劳崇光认为乡试不可久停,便同绅士复建贡院,复建后的号舍有8154间。
1862年,两广总督瑞麟、广东巡抚蒋益澧以广东学额、举额增加为由,号召绅士捐资再建号舍3000间。至同治六年1867年,广东贡院号舍多达11708间,规模宏大,和顺天、江南、河南贡院并称清代四大贡院。
贡院布局:规模最大时 北至中山路南达文明路
鼎盛时期的广东贡院占地有多广?按照参与筹建广东省地志博物馆的研究员曹腾騑考证,清代广东贡院规模最大时,北至中山四路,南达文明路,东跨越秀中路至东濠涌,西及德政中路旁的龙虎墙。记者从一张拍摄于1895年的老照片看到,明远楼处在广东贡院的中轴线上,宽阔的甬道两侧分布着一排排整齐的号舍,目之所及,皆为考场。
在明远楼大堂,一个全景模型复原了清代广东贡院的模样。广东贡院的研究者、广州鲁迅纪念馆藏品陈列科副科长刘丹告诉记者,古代贡院的建筑规制非常严谨,不同贡院之间,只有规模大小、间或一两栋办公场所称呼不同的差异,布局基本一致。明远楼现在陈列的模型,以末代探花商衍鎏著作《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中的广东贡院全部略图和建置说明为依据。
广东贡院坐北朝南,呈现左右对称的长方形格局。它壁垒森严,仅大门就有三道:第一道称头门,是考生点名入场的地方,门两侧是鼓楼,用于考试期间击鼓报时,第二道是仪门,第三道是龙门。龙门为木质两层建筑,飞檐斗拱,气势恢宏,能在乡试中“鱼跃龙门”是每个考生的梦想。
进入龙门,沿宽阔的甬道直进,便到明远楼。明远楼是广东贡院的中心建筑,也是最高建筑。站在楼上居高临下,贡院内外形势一览无余。监临、监试、巡察官等官员可以登楼远眺,稽查考生有无私相往来、执役人员有无代为传递作弊,在当时起着号令和指挥全场的作用。因为其用于监考的特殊性,所以清政府规定,贡院内外的建筑在高度上一律不准超过明远楼。
贡院的外墙铺有荆棘,外棘墙高一丈五尺(5米),内棘墙高一丈(约3.3米),所以贡院也有“棘闱”的称呼。考试期间,军队还会在贡院四周分段驻守巡逻,可见当时重视程度之高。
八月乡试:应试、吃喝、睡觉全在1平方米左右的号舍
号舍是广东贡院中占地最广、建筑最多的建筑。每列号舍一个字号,以两代文人周兴嗣编纂的《千字文》为序,依次排列在明远楼所在的中轴线两侧,蔚为壮观。字号除天、地、玄、黄、圣人名讳、数目文字、凶煞诸字不能用外,其他皆可列号。
来贡院考试的都是在每年举行的院试中被录取的秀才(生员),经过贡院乡试考中被录取的士子称为举人(即所谓“中举”)。乡试每三年举行一次,每次考三场,一般都在八月的初九、十三、十五三天。因在秋天举行,故称“秋闱”。“乡试可谓是科举四级考试制度中规模最大的一环。院试由县市举行,多借用临时场所。乡试相当于从每个省选出优等生到北京考试,再往后的会试、殿试规模就小得多了。”刘丹说。
应试秀才在考试的头一天晚上进场,对号入号舍,随身携带文具、餐具、茶具、被褥、衣服及食物,此外不准携带书籍、文卷及其他杂物以防作弊。《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中记载,为防止考生把写有蝇头小字的作弊资料藏在笔管、砚底、鞋底夹层、衣服夹层里,贡院一度规定考生只能穿单层鞋袜、可拆缝的衣服,不允许带过厚砚台、镂空的笔管,连干粮糕饼都要切开检查。
虽然贡院规模宏大,但每间号舍又矮又窄,“高六尺,举手可以及檐,深四尺(约1.33米),宽三尺(1米)”。舍内墙上有两层砖托,各层架设放着一块称作“号板”的木板,可以抽动拼接。白天,考生坐在下层号板上,把上层号板当桌子写字、吃饭。晚上,把两块号板放在下层就可以当床,但也只能缩着腿睡觉。煮茶、加热饭菜也要在号舍里,非常逼仄。
子时正(即零时)发试卷,考生就得马上点燃蜡烛考试,考试的9日间,考生们蜷缩在一个个小小的号舍里,或忍受夏日闷热、蚊虫肆虐,或只能以一油布“门帘”遮风挡雨,号舍靠近巷尾的考生还要忍受厕所的臭气,在种种恶劣条件和有限时间下炮制八股文章。
考生轶事:98岁人瑞与12岁少年同年科考中举
刘丹告诉记者,在整个清代,广东贡院产生举人6000多名。数千上万考生参加乡试,放榜中举者约在七八十之间。乾隆九年规定,广东作为“中省”,录取率为60:1。大学扩招前,高考常被称为“独木桥”,但也有10%左右的录取比例,秀才中举与之相比,只能称为“一苇渡江”了。
中国科举史上最老的考生当属台山人黄章,他从20岁开始考秀才,60岁才考取廪生,83岁考取贡生。1681年到广州参加考举人的乡试时,已经99岁了,由他的曾孙提着写有“百岁观场”四个大字的灯笼,一步一步领入考场。虽然老人还是落榜了,他却乐呵呵地说:“我今年才99岁,还没到科场得意之时呢,等我102岁时再来考,那才是我高中的日子!”
乾隆年间,广东出现了另一位百岁考生——谢启祯。他在98岁参加乡试时,已有三妻二妾,子23人,女12人,孙29人,曾孙38人,玄孙2人。这位老爷子没有在家享受五世同堂,反倒坚持披挂上阵,让人感到佩服又哭笑不得。
有人提醒谢启祯,按照当时朝廷的规定,这个年纪不用参加考试,只要报名就能免试并请求皇帝的恩赐。督抚也多次答应为他造册上报,可倔强的老爷子说什么也不肯。结果这次乡试他真的考中了,据说与他同榜中举的还有一位12岁的少年,从年龄上说可谓是曾孙辈了。
第二年,谢启祯一鼓作气地参加了会试。他的举动感动了乾隆皇帝,特赐他司业官衔。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正赶上皇帝的八十寿辰,102岁的谢启祯被晋升为鸿胪卿。
科考奇闻:修复贡院引发赌博 赌禁放开加剧作弊
1860年,广东贡院被毁,地方财政因为战事早已濒临崩溃,眼看乡试在即,考生却没有场地考试。此时,有绅士请当局放开“闱姓”两年,把赌饷用于修复贡院。清律禁赌甚严,当局只允许放开两年,且“期满禁绝”,却为日后弛禁、把“闱姓”赌饷当作为解决财政问题手段埋下了隐患。
原来,“闱姓”是利用科举考试进行的赌博。其赌博方式是以科考中士子的姓氏作为猜买对象,以猜中多寡为输赢。每当考试之时,赌资之巨大令人瞠目。据《申报》和《革命逸史》记载,“闱姓”总商刘学询,家本赤贫,承办“闱姓”之后却成了广东首屈一指的富商。
此外,为了让所买之人榜上有名,有的赌徒雇佣“枪手”顶替、有的赌徒贿赂官吏通关节换卷。因为考试不止一场,为不让前后成绩相差太大,竟有“枪手”将所有考试包办,成为广东“特色”的“一条葱”作弊方式。
在《科举旧影录》中,记者看到一幅《严惩枪替图》。1885年,惠州科考廖、钟、王三个大姓无人上榜,彭、文、田三个冷僻姓氏却上了榜,被人揭发枪替。学政查处了归善、波罗两县的代考者,将其戴枷示众。
还有赌徒为了让猜买热点的优秀考生落榜,采取买通让其发挥失常的方法,如果买通不成,就会贿赂胥吏或阅卷幕友,在其试卷上做文章,甚至将其试卷藏匿。“闱姓”的存在,使无数考生的命运被其左右,十年寒窗不如一张彩券,祸害不浅。
变迁:见证近代教育变革开端
1905年8月,清廷下达废除科举的谕旨,宣告了长达1300年历史的科举制度的终结。这一诏书也终结了贡院的历史使命,有的贡院建筑被该做新式学堂用房,更多被拆毁。
黄佐在《广东师范教育制度的变迁》中记录:1904年,广东贡院设立两广速成师范传习馆和两广小学管理员练习所,次年设立两广初级简易师范科学馆,1906年,设立两广师范学堂。1908年,设立两广优级师范学堂,培养中学及师范学堂的师资。
民国初年,学制改革,两广优级师范学堂改为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高师附设的中学、小学也陆续建起。其后,高师改建广东大学,又更名为国立中山大学。这期间,贡院唯一的遗存明远楼曾被作为新学堂的图书室、古物陈列馆。1957年,广东省博物馆选址旧贡院作为基建地点,明远楼归属省博物馆。1978年,明远楼被列为广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广州鲁迅纪念馆的管理之下,2016年修缮重新开放。
现在在中山图书馆附近漫步,仍能感受百年文脉流传下来的文化气息。中山图书馆西侧名叫“龙虎墙”的小巷,曾是贡院放榜的地方。龙虎墙与“龙腾里”连通,取希冀考生“龙腾虎跃”的吉祥之意。因放榜时值九月桂花盛开,人们又称其为“桂榜”,龙腾里以北有一“拾桂坊”,这些地名都与贡院相关。往西南行,便到文明路、文德路一带,老广州人都知道,这里是装裱字画或购买笔墨纸砚的地方。再往西行,就到了“龙藏流水井,马站清水桥”的书院群。
刘丹分析,古代人认为,一座城市的文脉在东南方,如今文明路一带仍然浓郁的文化气息,与当年贡院选址于此有很大关系。不光广州,很多城市的贡院旧址如今都是教育、文化场所。
“清代中国建有17座贡院,如今保留下来的明远楼只有江南贡院和广东贡院的两座。在数百年的历史长河中,明远楼见证了科举制度的兴废,也见证了广东近代教育变革的历程。”刘丹感叹道。
参考文献:曹腾騑《谈广东贡院旧址与广东省博物馆筹建》;刘丹《清代广东贡院:考古、文献与历史》;李兵、林介宇《科举旧影录》;蒋坤《“闱姓”赌博与晚晴广东社会》;蔺德生、赵萍《科考轶闻知多少》
文/广报全媒体记者方晴
图/广报全媒体记者陈忧子
策划、统筹/广报全媒体记者嵇沈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