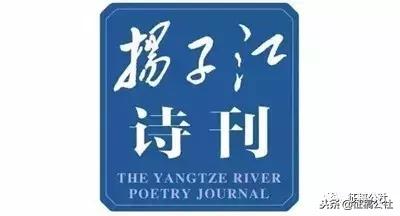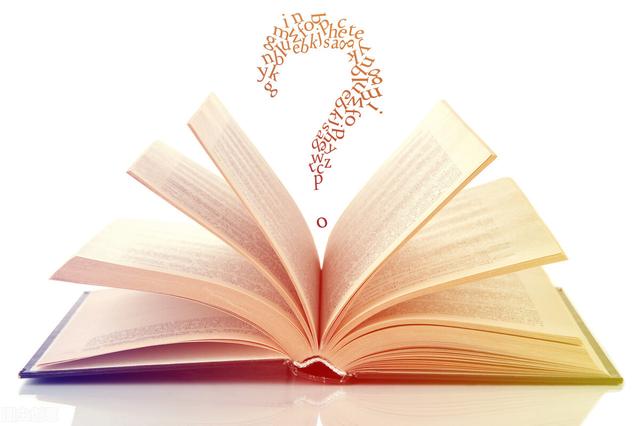
记得从小学五年级开始,我就喜欢上了读书。我喜欢读的这个“书”,不是指学校学生的课本,指的是“闲书”。
当我的一只手端着饭碗,一只手捧着一本厚如砖头的小说时,在母亲近于严苛的呵斥中,我也听到过父亲不责不骂地一声声怪怨:那“都是闲书”,“看外闲书有啥用处呢”。从这时候起,我爱上了“闲书”——文学。也真没想到,这一爱,就真的爱了一辈子。
那时候我的读书,与现在人们的手机上网一样似乎有瘾。读着读着就上瘾了,上瘾了就放不下了。我睡觉时捧着书,吃饭时捧着书,劳动的休息间隙捧着书。从家里到小镇跟集的路上,一个人走着时,手不离书。村庄里有识几个字的人,于是就称我为“书呆子”……读《红岩》时,一天无论干什么,整个思维都沉浸在许云峰,江姐,成岗,小萝卜头这些书中人物的命运中。读《红楼梦》,在冰天雪地里,正在热火朝天的“农业学大寨”着,心里却时时替那个如花似玉的林妹妹打抱不平……于是在人眼里,我就既傻又呆。
读着读着,就想写。写着写着,就想起了投稿。
上世纪的1979年,我在兰州铁路局天水段当“合同工”时,工局有一份《兰州铁道报》,记得报社地址是“兰州市何家庄”。投过几回稿,其中一次是一首“诗”,内容是将我们“合同工”比喻成了钢轨下面“黑不溜秋”的一根根枕木。稿子退回来时,附着编辑一封信,大意是:写东西“调子”要高点,“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怎么黑不溜秋”了?
有关投稿时的小心翼翼,以及无赖,焦虑,尴尬,失落等等太多。有些,已在《在蓝墨水的上游》一书里有文叙述过。曾经听说,我们这些“无名小卒”的稿子投给报刊编辑部后,有些编辑根本不看就扔进废纸篓里了。真的假的,咱不知道。在投了几回稿子石沉大海后,我就直奔主编,副主编。三回五回,我想,总有感动你的一回呢。
首先选择的是我们甘肃的《飞天》,《甘肃日报》。新疆的《绿风》,四川的《星星》,北京的《诗刊》,《人民日报》,《中国作家》等等。暗暗的下定决心:这些刊物上不去,我死不瞑目。说实话,我并不完全认为这是年轻人的茫目狂妄。原因是我读过那些大刊物上的作品,自信那上面有些东西,我也能写得出来。这就给了我,有点“狂妄”的支点。
《緑风》诗刊是新疆石河子文联办的,现在早已闻名全国。《绿风》上稿不容易,但是他们很负责任。稿子一旦留用,至少通知两次或者三次。一次是“拟留用”,第二次是“拟发某期”,第三次是“已发某期”。与此类似的还有四川的《星星》诗刊,稿子留用一般也是二到三次通知。它是省级刊物,创刊于1957年1月,比同年创刊的《诗刊》还早半年。稿费和《诗刊》的一样高。其知名度与“国刊”也差不多。比如顾城的成名作“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北岛最有争议的成名作《生活》,内容只有一个字:“网”。都是上世纪80年代初,于《星星》上发表出来的。我发表作品最多的是《诗刊》,给《诗刊》投稿,基本上都是投给个人的。比如叶延滨,李小雨,周所同等。省内的《飞天》,大多都是老乡老师为我负责看稿。
小镇一、四、七三日逢集。为了投稿,或者是为了得到一封稿子“回来的信息”,活儿再忙,哪怕夏收割麦子,给妻子找个借口镰刀一放,匆匆忙忙跑一趟集市上去。乡下农村与城市不同,邮政所是不会给我们将邮件送上门的。稿件从投出去到见到信息(或不见信息)期间等待的心情,真是一言难尽。提起来,就提起了人一肚子的辛酸。投出去的稿子,百分之九十没有了消息。时间最短的,两个月就见刊了。一般是三个月或者半年。最长的一次是《星星》,因责任编辑退休换了人,我收到留稿通知后,一年半才发了。
那时候投稿都是手写,抄稿子时夹上几张复写纸,一次就至少要三四份。然后,分别投给选好的报刊杂志。曾经形容我的写作和投稿,与我种的庄稼一样是“广种薄收”。杂志社原则上全都是反对一稿多投的。咱们无名小辈,投五家还不一定能靠得住一家,所以常常尽管“不忌”。
几十年只记得“幸运”过一次:“三投三中”。那是1999年的事。稿件投出后,前后收到了《飞天》,《星星》,《诗刊》三家的留用通知。高兴之余担心“违纪犯法”,赶紧给两家编辑部发信退稿,结果只有《星星》一家退了,《诗刊》来信已编辑好无法更改。从此我也知道了,一些大刊物都是提前两个月编辑好定稿的。作品被《飞天》,《诗刊》两家杂志发表后的第二个月,果然有人发话了。当时《飞天》有个“编读往来〔心之桥〕”栏目,记得是延安大学的一位教授,就在这个栏目里对我的“一稿多投”提出了很不友好的批评。批评就批评了,杂志社原谅了我的错误,还是给我按时寄来了稿费。
我开通微信上网大概就是三年时间吧。三年来,觉得微信真是个好东西。使人学到了不少,尤其对于写作的人来说,太方便了。只要你写出来,就不愁发表。全国大大小小的微信平台多得数不清,能使人投稿时左右逢源。你觉得不方便,还可以自己写自己发表。刚开始上微信时,出于好奇,按平台提供的河南一家期刊的邮址,给了他们几首诗。真没有想到,至多两个小时吧,我还在电脑前坐着浏览新闻呢,就已经发表出来了。这给人的感觉是,除了有点惊奇之外,什么都没有。反而有点空荡荡的失落感。细看才发现,连我因不会电脑操作写的两个错别字,都是原样的。
去年有位“微平台”的诗友约稿,我说没写出点好东西。他让我选些以前发表过的也行,我说那怎么可以?一稿多投都不许可。而且以前发表过的,现在又拿出来发表,是否有“炒冷饭”的嫌疑?他说:“别担心,当年我们投稿不容易,再大的刊物发表出来,受众面比起当今互联网来太小了。现在写作上网的大多数都是年轻人,当年你发表了那么多大刊,名刊,如今的人知道的有多少?”
的确也是。但从我心底里来说:以前发表过的东西如今再拿出来发表,脸上总觉得有点不那么自在地“发烧”。
我们这一代人,曾经说过什么都赶不上趟。刚刚知道吃饭时就是“困难时期”。刚刚知道怎样读书时,便是无书可读的“非常”时期。“改革开放”的大好春天来临时,别人早已进入了网络时代,不用笔写东西了,动一下手指头,网上来网上去一片全新的天地。咱白天务农,晚上回家还是爬在枕头上一笔一划地耕耘着纸。人家投稿早就鼠标一点,全国大大小小的编辑部就走遍了。而自己依然将抄好的稿子,装进一只鼓鼓囊囊的信封里〔我投稿用的大信封,都来源于朋友的单位。〕等逢集时一步步翻一座山,来回跑上十几里路投稿。邮寄时,邮政所负责人将鼓鼓囊囊的信封放在手上掂了掂:“超重了加一元邮费,再加一元”……
“形势”逼人,不得不学习电脑。“五笔打字”学了一段时间,头疼记不住。“拼音字母”,咱这一代人根本就没有好好地学过。现在不学是不行了,于是咱就好好地学习拼音吧,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学的时候才发现,几十年来,不知把多少字念错了,念白了。忽然想起近年来,网上常曝出名牌大学校长念错别字的笑话。看后,人心里真有一种五味杂陈的滋味。我们这一代啊!求求大家,原谅他们吧……
生活条件的限制,手机已经相当的普遍了时,我才迟迟用上了手机。大家使用“智能”多少年后,我也总算有 “智能”了。在孩子与朋友的指导下,学习上网。好,好,太好了。也终于享受到了我的祖国改革开放繁荣富强,高速发展带来的高科技的甜果。学着照相,发图片,还能与一二好友聊天……尽管很慢。比如朋友第三条已经发过来了,我才写好第一条的回复。但,这都不要紧。要紧的是我学会了回复,享受了上网,我心里高兴,喜悦。
学习了,享受了,幸福愉快了,就知足得很了。知道世界上有网络,有微信的生活是个什么样儿。尽管知道的非常有限,非常地肤浅。对于我,已经够了。
六十六岁是个吉庆的数字,不容易啊。社会上有人称我“农民诗人”,好得很。幸亏,“诗人”的骨头还是农民。幸亏农民还穿了件“诗人”的虚荣。这样,诗意就不会将眼前的现实,轻而易举地带向虚无缥缈的远方。
于是诗意着,又辛苦着,终于有了“六六”的年寿。与孙子们享些天伦之乐。有空了读点书,或报纸杂志上的小短文,不时地浏览一下网络微信。兴趣来了,或诗或文,也写点。至于投稿与否,早就没了当年的激情和兴致。
微信上网,满打满算就是三年光景。“朋友圈”,有一些是我加的,有一些是被加的,热闹得很。其实无论什么事,包括朋友圈的互动,包括朋友。热得快的东西,一定凉得也快。对于正在热的,别头脑发热。对于突然凉了的,不心生忌恨。朋友吗,哪有常热的?感冒一样发热正常,热到一定程度就会降下来,貌似凉了,实则舒服了。假如高烧不退,有可能会出问题。常热的不一定是好朋友,君子之交淡如水。常热的友情,有,可能是友情外的什么“鬼情”。“朋友圈”里,你说我几句好听的话,我恭维你几句好听的话。全是好话,但绝对不是好朋友的话。
去年冬天,决定退出了“朋友圈”。想来想去,活在“圈子”外面,好。偶尔烦躁了,踮起脚跟瞅一眼圈子里,觉得无聊。偶尔自己无聊了,再瞅一眼圈子里,似乎依然很热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