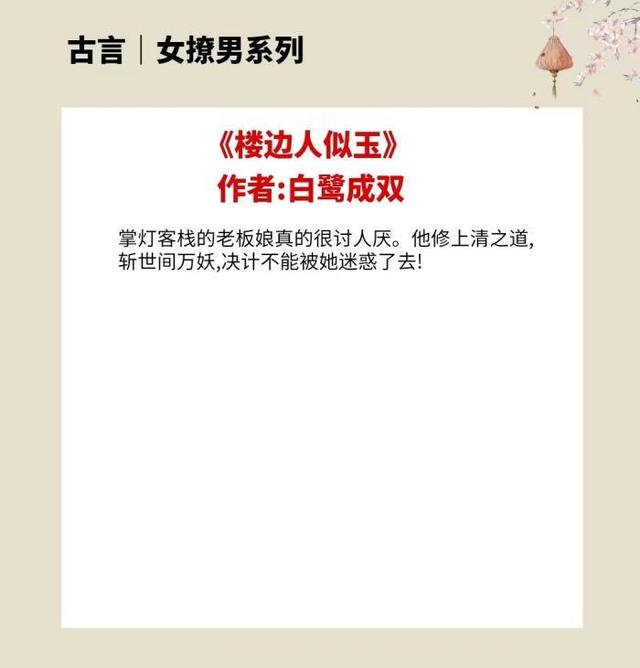当太平天国战争结束时,安庆已经走向历史的拐点,随着战争的远去而渐渐被人遗忘、变得暮气重重。但它注定无法领中国之先而完成近代化转型。内战结束、刀兵远去,本是幸事,可是对于一个军事化模式根深蒂固的内陆城市而言,这同时也意味着失去了在中国版图上被特别关注的意义。
吴头楚尾

安庆振风塔
安庆,是一座境内具有近六千年建城史的古城。在这座军事重镇,有一个老宅,先后成为“太平天国英王府”、“大清两江总督督帅行署”,后来李鸿章的四弟李蕴章以重金购置此宅,其子李经世改建后命名为“太史第”。这座“太史第”,见证了千年古城安庆的兴衰。
公元1577年,安庆城南一处临江山坡上,立起了一座崭新的大宅。宅主任氏,本是安庆郊区的一户殷实乡绅,但当这年一位名叫任可容的族中子弟高中进士后,任家便成了官宦家族,随后便把家搬到了安庆城里这处可极目长江的所在。
33年后,任可容之子任国桢再中进士。父子同朝双进士,风头一时无两。而其宅府大院,也随之向东西两侧延伸渗透。到清康熙年间,任家再出一门三进士,任家宅邸也进一步扩展,最终,连南边半山坡也渐为其所用,竟形成了一整条街的规模。而这片无名山坡,也便毫无争议地成了“任家坡”,如今是安庆长江边一条350米长的老街。
安庆坊间传言,任家的发迹,与任家坡东边1.5公里外高60多米的振风塔不无关联。1568年,时任知府王宗徐“因见安庆境内诸山蔚起于西北,而东南方江流一泻千里”,认为这是“安庆人文不兴之兆,须在东南方起塔,以振人风”。两年后,“振风塔”竣工,有如安庆这座船形城市的桅杆,雄峻而醒目。此后,安庆果然文脉通达、文风大兴。大明万历年间,整个安庆府出了36名进士,而任家则独占其二。
事实上,安庆文脉之兴,乃是得益于明初32.6万移民陆续迁入后带来的盛世繁荣。这些占同期安庆府总人口近八成的移民,几乎都来自“文化水准更高的婺源和鄱阳”。

老安庆城
血火轮回
任氏祖先出身行伍,在明初曾为徐达部下,参与北征。其子孙则世代在安庆乡间耕读,直至第八代任可容。
自明初洪武至晚明万历百余年间,任氏由武转文的努力,也恰恰是安庆这座战乱之城对诗书和盛世的渴望:任氏先祖解甲归田时,安庆也刚从元末明初的血火战乱中完成了一次生死轮回。
安庆是一座军事重镇,前据武汉,后攘金陵,号称“万里长江此封喉,吴楚分疆第一州”,乃是南宋都城临安的西线桥头堡:从建城伊始,它便注定是一座兵刃血溅的战争之城。
1358年,安庆遭遇第一次倾城之祸。时值元末,遍地烟尘,守城主将余阙从1352年起与红巾军血战连场,直到1358年正月援尽粮绝,然后“以身挡之,徒步提戈”,最后“见城中火起,知大势已去,乃引刀自刎”,妻女家人也尽数自裁,同时安庆城中军民 “宁死不从贼”、登上城楼最高处投火死者上千人。
余阙殉死的西门,位于皖河与长江交界处,同时也是安庆通商贸易的门户和商业中心,明清安庆数百年的繁荣气象,便从此处开始渐渐生成:周边六邑到安庆府,多经西门进城,西门外因此遍地盐号、米行、皮油行、棉花行,通江码头货船往来穿梭……
1760年,安庆更升级为安徽省会,海量的人力、物力,都紧随行政中心而来。在西门外,在城南沿江码头,在城中的三牌楼、四牌楼区域,无不徽商云集。又借助得天独厚的水运优势,安庆终于成了一座人气空前的沿江大商埠。

涂抹剔剥
然而,为安庆带来活力的市井商业,终究还只是军事重镇的依附品。当刀兵再起时,任家乃至整个安庆城近三百年的富庶,转眼消散,宛如昙花。
一个世纪后,太平军起于两广雄踞东南,于1853年占领了安庆。战乱中,任氏一条老街,毁之大半,剩余的家族房产,也多为太平军所用,成了太平军统帅陈玉成的英王府。陈玉成之所以选中此地作为王府,是因为这里地势险要,可以居高临下,俯瞰长江。
陈玉成为人简朴低调,不喜奢华,短暂驻留间,几乎未改动府邸格局。曾国藩幕僚赵烈文在日记中称“督帅行署,伪英王府也,在城西门,府屋颇多,不华美,亦不甚大,满墙皆彩画”,至今屋内还有多处可见残痕。
这些光怪陆离的彩画是一个奇特的混合物。来自南方蛮荒地区的起义者,充满了神话般的想象力和原始图腾色彩,并将它们与西方的天主教、黄土地意识杂糅在了一起。
仅仅6年后,已经率领湘军夺取了武昌的曾国藩,又将目光投向了安庆。
“自古平江南之策,必居上游建瓴而下,乃能成功”,他决定自武昌沿江而下、水陆并进,全力夺取安庆,然后围攻南京。“目前关系淮南之全局,将来即为克复金陵之张本”。安庆再临倾城之祸。
此后两年间,湘军与太平军围着安庆反复拉锯、绞杀,直至1861年9月5日,湘军在地道中放置火药炸开安庆城墙,然后蜂拥入城,太平军则以血肉之躯死堵缺口,“或战殁,或投江”,自主将叶芸来以下无一幸存。
而后,曾国荃下令屠城,城中军民被分成10人一小组,分送湘军各营杀戮,半天而尽。“杀贼凡一万余人,男子髻龀以上皆死,……妇女万余俱为掠出。”(赵烈文《能静居日记》)。
五度血战救援安庆而不得,陈玉成再也回不到他的英王府。曾国荃屠城七天后,曾国藩进驻安庆,用白垩土涂抹掉那满壁的彩画、在宅邸四周种上幽竹后,又将英王府改成了曾国藩的两江总督行署。
有趣的是,一百二十年后,专家们为了考证它否就是当年的英王府,曾小心剥掉覆盖其上的六层白垩土,陈玉成们绘下的“飞凤舞狮”“暗八仙”“飞凤奔马”“瓜瓞绵绵”等彩画,又再度重见天日了。

过客
曾国藩在任家老宅驻节的三年里,一边坐镇指挥总攻南京,一边进行着一项大谋划:“以机器局为前提……使中国得致富强”。(容闳《西学东渐记》)
在他手创的安庆军械所里,只有理论知识的徐寿、华蘅芳,居然独立摸索出了小火轮、落地开花炸弹以及中国第一台蒸汽机。尽管小火轮“行驶迟钝,不甚得法”,曾国藩还是大喜过望,随后又派“中国赴美留学第一人”容闳前往美国全权负责机器采购。
只是,当两年后这批机器登陆中国时,曾国藩早已离开安庆。1864年,清军攻克南京,太平天国覆灭,曾国藩随即将两江总督行署迁往南京,同时也带走了安庆军械所,只给老宅的新主人李蕴章留下一块“勋门慈荫”的祝寿匾。
李蕴章是李鸿章的四弟。其少年双目失明,然而精明过人,随长兄李瀚章代办湘军后勤,深受曾国藩、胡林翼赏识。湘军攻克天京后,李蕴章也回到安徽,一心治理家事。任氏老宅,正是他在这时以重金购置的一处主要宅邸。李蕴章之后,其子李经世又改建了老宅,并应自己翰林院庶吉士的身份,将宅子命名为“太史第”。
安徽省立图书馆馆长蒋元卿回忆称,当年的太史第“高大、气派”,“并排三座高大门楼,‘太史第’三个大字的直匾,高挂在正门上,直到建国初都还在。”
然而,李家和此前的陈玉成、曾国藩乃至一样,也都只是安庆和太史第的过客。李经世也很少在安庆居住,他于1891年病逝于天津。
事实上,当太平天国战争结束时,安庆已经走向历史的拐点,随着战争的远去而渐渐被人遗忘、变得暮气重重。但它注定无法领中国之先而完成近代化转型。内战结束、刀兵远去,本是幸事,可是对于一个军事化模式根深蒂固的内陆城市而言,这同时也意味着失去了在中国版图上被特别关注的意义。
更重要的是,此时上海已然崛起,毫无悬念地将安庆乃至整个安徽抛向了近代化大潮的边缘——容闳从美国采购回来的机器,最后就留在了上海的江南制造总局里。不久,一艘长达18丈的木壳轮船在上海诞生。但欢呼雀跃的人们多数不知道,也无需知道,这片在上海燎原的火焰,最初采撷的,其实是安庆的火种。

短暂的归来
李经世去世后,其家眷在太史第中住了八年,也于1899年前后匆匆离开安庆去了上海。此后近30年间,太史第一直闲置,无人居住,直到1927年李家回归。此时的安庆,在民国此起彼伏的城市实验中继续失语,已显出了难以逆转的暮气和颓势。
时年5岁的李经世重孙李家震后来回忆说,他当年印象中的太史第,分左中右三路,分开有三个大门,宅中设施齐全,但与上海大都市的生活相比,还是有诸多不便。
当时安庆“没有自来水,饮用水是从长江挑上来的,放在水缸中,水中有泥沙,很浑浊,必须打上明矾沉淀掉泥沙后才能饮用”。安庆白天还不供电,到晚上才供,所以“夏天白天不能用电风扇,只能用人拉的布风扇扇风”。
李家对当时上海与安庆的差距感触特别深。他们在上海有亲戚,自己又有轮船,每年都要到上海:李家太史第中的一些新式家具,就是专门从上海购置后运过来的。
但李家震说,那时李家跟整个安庆一样,也已经在走下坡路了,“家境跟鼎盛时比,远不足一半的一半”,原因是安庆“逢乱必战”,人们大多有“前途未卜”的忧虑,认为从事工商业没有安全感。
不仅是工商业者,即便是李家这样的大户,也不免被各色军队骚扰。“军队过兵安庆,总要上门来借房子,这些驻兵又不爱惜,宅中设施常常遭到破坏”。无奈之下,李家只好把空房向外出租。
李家在安庆一直住到1937年,而后又在兵荒马乱中去了上海,从此再也没有回到太史第。

老安庆地标大观亭
老宅蒙尘
李家离开安庆后不到一年,安庆沦陷于日军之手,安徽临时省会迁往立煌县。从此,安庆再也不是安徽省会:抗战胜利后,安徽省会迁往合肥;1949年,毛泽东力排众议,指定合肥继续充当省会。对多数安庆人来说,这是心理上的重创,而安庆也确实就此更为低迷、边缘。
尽管当时的安徽省委也不认为合肥宜作省城,但毛泽东认为:形势仍未真正安定,如把省会定为安庆这样一个沿江战略重镇,并且是在南京和武汉之间,一旦战事再起,极有可能被敌军一日连下两个省会城市。而合肥是山区向平原过渡的丘陵地带,能很好缓冲敌军进攻,也便于己方集结物资人员展开反攻。
显然,毛泽东的考量,是主要从军事角度出发。而到1954年,长江洪水横扫安庆后,便再也没有主政者公开提省会迁回安庆一事了。
此后的安庆城史,便如空旷老旧的太史第一样乏善可陈。1981年李家震重回安庆时,发现他的家——当年任家坡最气派的门楼,已经被蜜饯厂加以改造,取而代之的是带有“强烈”文革色彩的大门,其左其右,专门留有可以置放政治标语的凹墙,这让他十分沮丧。
2011年末的太史第,则更显破旧不堪:破损的木门敞开着,门口墙体已多处剥落。门前有两块上马石,右边的一块倒在了左边的脚下,只有门右侧由安庆市政府镶嵌的、上书“太平天国王府”的牌子证实着昔日的辉煌。
这座超过一百五十年历史的老屋,如今仍然有数十户人家居住。砖木结构的穿斗式二楼,左右是厢房,中间开天井,天井的石板地在雾气阴沉的冬天里,透着冷冷的湿气,四处堆着杂物,一些因时间久远而损坏的厢房木门也被草草地靠放在墙边,为方便住户生活而安装的水龙头突兀地耸立着。整个四进房屋进深逼仄。没有华丽的雕花门窗,也没有精美的飞檐装饰。一处处的墙壁斑驳陆离,一扇扇木格门窗掉尽朱颜……
尾声
太史第的没落困顿,或也正是古老安庆时下的困境。有老安庆曾自豪地说,在安庆老街上,哪怕一个破衣褴衫的看门老者你也不能小视,“说不定他可以把一部《春秋》倒背如流”。
然而这终究不能代替安庆现实的困顿。1980年代,安庆曾一度重新活跃,沿江西路上雨后春笋般的露天摊点,虽假劣充斥,却也是那个时代活力的特征,与江浙同兴。但二十多年后,同时代的江浙城市,区域经济早已蓬勃发展,安庆却还是“街头巷尾,麻将声声”。
当时,有六百多万人口的安庆,却没有一辆始发至广州、深圳的列车——交通集散地不仅会带来运力,还会形成巨大的商圈,还有人流带来出租车的旺季、酒店的熙攘、购物高峰,但这一切尽数落空。
不变之外,也有改变,如永远消失掉的城墙、老街、老店铺前的人气……尚未消失的,也如浓缩了安庆数百年历史的太史第老宅一样,在城市的角落里,在高楼包围中渐渐模糊了身影,日复一日静候着永远消失的那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