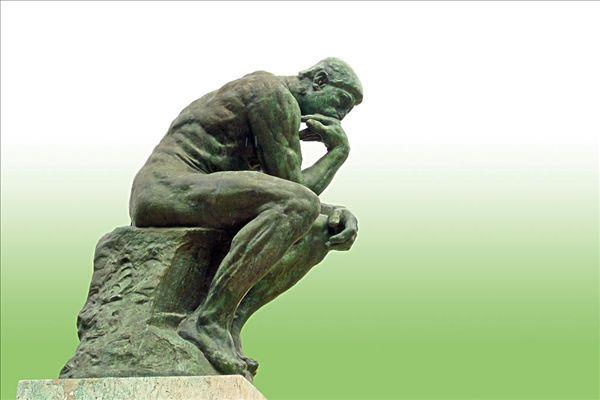现在当小孩太不容易了。
不久前有人录了条视频,测试孩子们的自我保护能力。参与实验的儿童,有两三岁的女童,也有五六岁的男孩。测试者只用两句话,就哄骗这些孩子把身上的衣服脱干净。
无论男孩女孩。
所有的孩子,几乎毫无保护自己的意识。
更可怕的是,这些孩子的语言能力可能尚未发育完全。
这意味着他们很难指认施暴者,而这也让他们更容易成为施暴者的目标。而当家长的,要么不知道,要么很可能知道了也没辙。
2018年,检察官凌十八曾接到报案,一个年轻妈妈说,自己的孩子被检查出妇科病——
女孩只有三岁,还说不出连贯的句子。
而这个妈妈第一个怀疑对象,是她的领导。
如果想为女儿讨回公道,就要把她的顶头上司吿上法庭。

2018年8月,张欣牵着三岁的女儿妞妞,走进医院的妇产科。
等待间隙,妞妞在座椅上爬上爬下。
分诊台的护士大声念到妞妞的名字,张欣把妞妞抱进门诊室。
一进去,张欣就对医生说,自己也是护士,请医生给妞妞做全套检查,阴部超声,还有其他妇科病检查。
医生吓了一跳,三岁的小孩处女膜还在,怎么能做阴超呢?
那是一种是将B超探头放入身体进行超声诊断的方法,适合于观察小骨盆内的盆腔脏器,适用于已有性生活的女性。
医生的话刺痛了张欣。
几天前,她给妞妞洗澡的时候发现妞妞的下体红肿且外翻,妞妞却只会说下面痛。
她不可避免地想到了一种最坏的可能性,她自己也在妇产科实习过,妞妞的下体一看就不对劲,她没法说服自己不当回事。
张欣握住妞妞小小的手掌,声音在颤抖。医生终于妥协了,和检查室的同事解释了半天为什么这个三岁的小女孩需要做阴部超声。
妞妞仅仅比检查床高一个头,张欣把她抱到检查床上,仰卧,退下裤子。
张欣尽量捂住妞妞的眼睛,不让妞妞看到医生手里直径两厘米的探头。
可过了一会,妞妞还是哭了起来。
最终的检查结果是处女膜未破裂,从妞妞身体里提取的分泌物,显示妞妞患上了一种常见的妇科病。
医生跟她说,这种情况可能是不注意卫生被感染,不排除用手摸过。随后给妞妞开了几盒治妇科病的药膏。
张欣很熟悉这种病的症状,妞妞一直喊自己痛,其实也许是痒。
走出医院,妞妞的眼泪早就干了,她像来之前一样,还是不怎么会说话,张欣第一次觉得女儿安静到令她无法忍受。
她身为妈妈,对妞妞的遭遇一无所知。
过了几天,张欣去派出所报警,称女儿妞妞被人猥亵。派出所把警情上报到公安局刑警队。
为了避免对公安和检察机关对妞妞多次询问,造成二次伤害,我作为未成年人检察官提前介入,跟公安一起询问被害人妞妞。
询问妞妞的地方很特殊,叫一站式询问中心。
每一次踏入这个地方,我都希望以后再也不用来了。
在妞妞一声不吭地打量我时,尤其给人一种在戒备的感觉。
她的眼神好像在告诉我,我也是伤害她的世界的一部分。

妞妞是来到一站式询问中心最小的孩子。锅盖头,大眼睛,身子小小的,直接被妈妈抱在怀里。
进来以后,她的头一动不动,眼神四处乱飞,打量了这里一圈之后,就用小手指着门外要出去。
张欣把她按在怀里,让她别害怕。这种催促起了反作用,妞妞显然听不进去,害怕得发抖,一句话不说,用后脑勺对着我们。
张欣对于女儿也又急又无奈。因为妞妞的案子还没立案,她怕妞妞再不配合,警察和我都不把这案子当回事。
她从一开始就怀疑妞妞被人猥亵了,妞妞被确诊之后,张欣问妞妞:“除了妈妈、姥姥、奶奶以外,有没有人摸过你下面?”
妞妞说“有”。
可妞妞说不出来那个人是谁。
三岁多的小女孩能说自己的名字、年龄和性别,但如果说到“我、你、我们、你们”这些词有时也会搞混。
让她去描述出一个除了妈妈之外的陌生人?太难了。
张欣在卫生院当临时工,平常就带着妞妞和一岁的儿子在卫生院宿舍生活。她的妈妈和婆婆平常会来卫生院轮流搭把手照顾孩子,让她白天能正常上班。
卫生院不大,前后两栋白色小楼,分别是门诊楼和员工生活区。
员工二十来人,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
老人精力差点,不会带孩子出去,妞妞生活,玩耍的范围不超过这两栋小楼。
张欣曾放心地以为这是两道保险。可妞妞白天去过什么犄角旮旯,见过什么人,她压根不清楚。
张欣把卫生院的同事在脑海细细过了一遍,突然想起来之前看到的一幕。
员工宿舍都分布在一层走廊里,住另一个宿舍的副院长宋元一把拉住正跑着玩的妞妞,把妞妞的小短裤扯下去,大手在妞妞的光屁股上“啪啪”打了两下。
张欣瞬间血液冲上脑门,对宋元发了火:“太没有分寸了,怎么能把我女儿的裤子脱了?”
宋元无所谓地笑笑,说自己只是和妞妞开开玩笑,暗示张欣反应过度了。
哪有人这么开玩笑的?
在张欣的回忆里,宋元作为副院长,分管后勤,手里有所有房间的钥匙。
大家有事都找他,忘带钥匙也得找他,他是那种出现在哪扇房间门口,张欣都觉得不违和的人。
因为他总能适时地拿出一串钥匙,对准锁孔,转动,打开门,随后消失在门里。
他随便把妞妞带到任何一扇门里都轻而易举。
这意味着,他可以对妞妞做任何他想做的事。
张欣让婆婆带妞妞去卫生院的职工墙去指认。妞妞两次都指了宋元的照片。
回来的路上,妞妞除了认得张欣的宿舍,竟然在两个房间门口停下,指着紧闭的旧木门,“伯伯在这里面摸了我。”
那是两间仓库。没有标志,也没有门牌号。
张欣知道,宋元管卫生院的医疗设备,这两间闲置库房只有他常进常出。
宋元当初能当上副院长,都靠走后门,关系很硬。
张欣只是个普通员工,一旦惊动到此人,可能她们娘俩一块被报复,张欣权衡之下,决定悄悄去报警。
她直接带着被诊断妇科病的妞妞,诊断证明,还有药盒,到了派出所。
接到报警后,公安已经第一时间从卫生院拷走对着那两个库房门口的监控。两个监控探头,都没有拍到宋元和妞妞一起进入库房的画面。
民警问张欣,有没有留其他证据?最好是有痕迹类的证据。
张欣一愣,已经给妞妞洗了澡,衣服也都洗过了,去哪儿找证据?
张欣愤怒地控诉,我看到过他摸我女儿屁股!我女儿认出他来了!这不算证据吗?
她不停地陈述,但是只有言词证据,没有任何证物。这让民警也很为难,这种情况下如果立案,查不到证据,可能都没法结案。
而民警找到宋元以后,此人的反应则像是第一次听到这种事情:“绝对没有。”
如果是他,他知道监控的盲区在哪,也应该早就恐吓过妞妞,知道妞妞什么也不会说,警察没证据。
如果不是他,这种事,警察也怕冤枉人。张欣几次打电话问,都没有得到民警立案的消息。
过了几天,她闯到了警队,当着刑警队副队长的面质问:“你们是不是偏袒嫌疑人?”
副队长气得手里烟一抖,命令民警赶紧查案。

民警给我打来电话求助,十分头疼:“你都不知道,那三岁多的小孩,她会跟你说啥,有的话她根本就不懂。”
民警叫王杰,是一个新手爸爸,之前因为被调到专案组,孩子出生半年了,他也没陪几天。
他说自己不怎么会和小孩沟通,硬着头皮问了妞妞几句,妞妞只会点头摇头,顶多会说“摸啦”。
“然后呢?”王杰进一步问怎么摸的,她就不说话了。
王杰说要不是看到妞妞这个样子可怜,他也不想推进这个案子。
我们都知道,性侵案件最棘手的地方就在于证据难找,而且往往是被害人和嫌疑人各执一词。
三岁的妞妞不怎么能说话,她妈妈张欣的证词再多,顶多算侧面印证。
张欣要是更能豁出去,她可以在报警之前找到宋元当面质问,这样说不定宋元因为慌张而说漏嘴。如果有第三人在场,就能作证。
最可怕的就是没有如果。
张欣来报警的时候,丈夫从外地匆匆赶到刑警队,这是出了事以后,张欣第一次看到丈夫。
他当着民警王杰的面,将张欣狠狠摔到沙发上。他不停数落张欣:“你怎么当妈妈的?”
张欣挣扎着起来,她的孩子被外人秘密侵害,而她被置身事外的丈夫指着鼻子骂。
听到这里,我向王杰确认:“是不是她丈夫怪是姥姥看孩子的时候出的事?”
王杰啧啧嘴:“不然是啥?”
这样的家庭闹剧在派出所经常上演,想必回家后更是没有遮拦。我想象着妞妞孤零零地在旁边站着,把父母的争执尽收眼底。
我曾经自告奋勇,去给儿子的幼儿园小班上过一堂家长课,主题是防性侵教育。
我给小朋友们看了绘本,讲了故事,告诉他们自己的身体哪里是绝对不能被别人碰的。儿子很自豪,小朋友们听故事听得也很开心。
他们都和妞妞一样大,小孩天性就喜欢听故事。
这样的事,直接发生在了妞妞身上,也不再是一个故事。
妞妞不会明白,爸爸妈妈为什么要吵架,妈妈为什么总是问起那个怪伯伯?是不是自己做错了什么?
妞妞似乎被关在了一道门里,明明在风暴中心,却连求助都做不到。
挂完电话我直接去找领导。按照流程,这个案子应该由领导分配,但我以这是疑难案件为理由,主动接下来了。
此刻妞妞已经来到了一站式询问中心。
我坐在她面前,开始准备通过谈话,确认此次性侵的证据。
其实说是确认证据,但首先要确认事实。
从办案角度来讲,现在除了张欣的几句话,依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妞妞被那个副院长性侵过。
但我也是孩子的妈妈,我相信没有哪个妈妈会拿自己孩子的这种事开玩笑。

张欣抱着妞妞,进入了一站式询问中心,全程和我们无交流。
这对妞妞来说完全是一个陌生的环境,王杰已经开始在她对面公式化地说起:“希望你如实陈述,我们会为你保密。”
妞妞完全听不懂,只想出去。
张欣先是低声哄,后来她有点着急,一把将妞妞按在了自己的腿上,呵斥妞妞不能出去。
我走到妞妞面前,蹲下来拉住了妞妞的手,她的手好小,不到我手的一半。
我晃着她的手,轻声安抚:“我是检察官阿姨,和警察叔叔一样,都是抓坏人的,妞妞别怕。”
后来,辅警也走上来,带妞妞在屋子里转圈。可能是因为辅警是女性,又身着警察制服,妞妞开始回应我们的话,也只是点头或者摇头。
妞妞不像有的三岁孩子已经能叽里呱啦一堆话,她说话是往出蹦字的那种,比如“摸啦”。
因为我办的性侵案件太多,了解小孩子的词汇库非常有限,就顺嘴就问了一句:“你有没有见过那个伯伯尿尿的地方?”
“见过。”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那他有没有拿他尿的地方去碰你尿的地方?”
“碰了。”
我直起身子,和王杰对视一眼,法律规定对未满14岁的幼女,只要性器官接触都是按强奸论处。
案件性质由猥亵变成强奸。
女辅警见状,也一直引导妞妞:“太坏了!咱们说清楚,把那个坏人抓起来好不好?”
询问妞妞的过程中,我们要求张欣全程都保持沉默,不要干扰询问。
我问妞妞碰的时候疼不疼?妞妞一边点头,一边说“疼”。
我忍不住直接开口说,以后有人让你不舒服了就告诉妈妈或者警察叔叔好不好?
我看向张欣,她早已经把脸沉默地转向一旁,抱妞妞的手箍得很紧。
只是过了很久,她也不忍心看向怀里的女儿。

可能是因为我们一直在和妞妞重复:“做那种事就是坏人”,妞妞收起了胆怯,点头的频率在变高。
她不像我询问过的十几岁的少女,已经有了羞耻感。她的眼神很无邪。
我恨不得抛出我所有的问题,一连串地对妞妞问到底,但看到妞妞的眼神,我只能慢慢引导。
她也只是配合我们大人说出她知道的事情。
有那么一瞬间,我甚至不敢去和她对视,因为我想如果我们社会的机制完善,她是不是就不会遭遇这些事情。
侵害的方式、时间、地点,还都是未知。
我问妞妞这样的次数有多少?妞妞也记不清。
从什么时候开始,即使我们给出“穿着冬天衣服还是夏天衣服”这样的提示,她也只是摇头。
妞妞的表情很茫然,这个年龄的孩子甚至不知道这种事情是不好的事情。
我遇到过一个二年级的女孩,去邻居家玩,被邻居性侵了三次。我问她,他对你做这个事情,你舒服吗?她说不舒服。我问不舒服为什么还要去?她的理由仅仅是想去找邻居家的小孩一起玩。
后来,我通过问妞妞,“外婆在的时候有没有”“奶奶来的时候有没有”,得到大概侵害的时间是5月份开始。
我们后来了解到,这次是妞妞直接用手伸进去摸下体,说疼。奶奶当时看了一眼,没看出哪儿不正常,就没放在心上。
通过妞妞的点头,摇头,我判断出来有的时候“伯伯”只是用手摸她、有的时候“伯伯”拿尿尿的地方碰她,这是事实。
我像是摸到了一把锁,那把锁把妞妞关进房间里。从五月开始到现在,长达四个月。
询问花了两个多小时,像是拿着铁丝一点点地撬开锁眼。
我没想到能够问出强奸的情节,也没想到除了这一点,也问不出来什么了。
询问结束,我走出询问室,深吸了一口气。
张欣在笔录上签好字,把妞妞留在里面按手印,就立马跟着我出来,问我能不能立案?
我说我觉得没问题,应该能立案。
大厅里一个坐在沙发上的年轻男人看到我们,立马走过来,和张欣打招呼,张欣顿了一秒,跟我说:“这是孩子爹。”
我迅速判断,这对夫妻在闹别扭,如果不是需要给我介绍,张欣会直接忽视她丈夫的存在。
我本来急着走,却突然想到什么,就跟张欣丈夫说了刚刚询问的结果:“孩子在奶奶带着的时候就发生了这个事情。”
张欣的丈夫眼神里流露出震惊。
我继续:“发生这样的事情,孩子妈妈是最不愿意看到的,不要去责怪妈妈了。”
张欣站在我身边不发一言,她的头发一截黑一截黄,发梢还有快剪没了的微卷,看上去她很久没有打扮过自己了。
我把这对夫妇留在了身后。

一站式询问后的第二天,我接到了王杰的电话。他们已经将案件立为刑事案件。
公安局的领导考虑到案件的特殊性,在妞妞辨认嫌疑人时没有采用通常辨认照片的方式,而是采用了真人辨认。
给妞妞做的笔录里,我们已经确认有一个坏伯伯存在。
“你认不认识那个伯伯?点头。
你能不能给你妈妈指出来?点头。
伯伯是不是在你妈妈上班的地方上班?点头。
伯伯有没有给你说过不准给妈妈说?点头。
伯伯有没有说过你给妈妈说的话就打你。点头。”
“那你能不能指一下这个伯伯?”妞妞点头。
民警他们找来了一排7个和宋元年龄差不多一样大的人,包括宋元本人。
宋元站在特殊材质的玻璃窗里面,看不到妞妞从外面走过。无论是编号还是排序,他都非常配合。
我看的是录像回放,屏幕中的七个人看起来都很镇定,让人猜测不出哪个人即将被妞妞指认。
下一秒,女警官问妞妞,谁是脱你裤子的伯伯?
尽管心里已经知道答案,看到妞妞指向宋元的时候,我还是由衷地在心里骂了出来。
再来一次,妞妞还是指他。
面对这样的证据,宋元还是否认自己是妞妞口中的“伯伯”。
他对王杰说,钥匙挂在他办公室,又不是只有他一个人能拿。王杰经领导同意后直接将他拘留。
没想到,人送到看守所,看守所检查出他重度肝硬化,拒收宋元。
公安局对他的强制措施变更为监视居住。宋元被禁足在家,当地公安机关派了两个人监视他。
我还是不肯放弃。我百度了重度肝硬化拒收的理由,问驻所检察室的同事,得了这个病为什么看守所就不能收了?
同事回复我,这病看守所治不了,监狱也许能治。
监狱能治,就代表监狱能收。
我通知王杰无须经审查逮捕程序,尽快将宋元移送审查起诉,我打算通过法院审判直接把他送进监狱。

宋元一天不进去,张欣就一天不得安生。她来到检察院的信访接待大厅,指名要见我。
我看到她一个人来,问她孩子怎么样了?她说把妞妞送回老家了。
一开始面对张欣,我总庆幸自己几年前的心理咨询师证没有白考。
张欣鄙夷地说宋元肯定是装的。我看出她的慌张,跟她解释,“监视居住也不影响案件的进展”,按照司法程序,宋元肯定会被起诉。
为了让她放心,我把个人电话留给了张欣。张欣也没客气,每天给我打电话。
我老公那个时候每天晚上九点多下班,基本都是我接孩子,带孩子。办公时间,晚上哄孩子睡觉时间,我不分昼夜地接到她的电话。
孩子睡眠质量都跟着下降,眼睛刚闭上就被电话吵醒。
张欣也在不断学习法律知识,她也知道性侵案件的证据薄弱造成很多时候犯罪嫌疑人不能被追究刑事责任。
她揪住亲眼看见宋元拍妞妞屁股的事实,问了我几次:“单纯这个事情算不算猥亵儿童犯罪,能不能追究他的责任?”
出于谨慎和工作纪律,我不可能给她肯定的答案,她还是听不明白一样让我再解释一遍。
有一次,她来办公室找我,旁边还有我同事。我同事一直没吭声,过了一会突然让张欣掏出手机。张欣脸色一下子变了,好像做坏事被人发现的尴尬。
手机拿出来,我看到里面存满了录音,我们每一次的通话都被录了音。
通话时长不等,最近的几次通话时长都在二三十分钟。
我一直是个反射弧很长的人,到现在我才终于明白张欣为什么总是反复问我一个问题。
有的家属在电话里扬言要告我,我都不是很在乎。但那一刻,我承认我还是受伤的。
“我不怕你录音,但是希望你能找个律师过来沟通,这样子更方便。”
张欣面色讪讪地离开了我们办公室。半个小时以后,她又折回来跟我道歉:“对不起啊。我做的不对,你别往心里去。”
我嘴上说不在意。但是心里没有原谅她。我劝自己,我不是为了张欣来办案的,而是为了维护妞妞的权益。
但其实我有点理解这个妈妈,张欣录音不完全是出于对我的不信任。
我能感受到张欣的压力在与日俱增。
宋元那边的小动作不断。他给张欣打电话,张欣不接,他就微信轰炸。
表面要说和,语气却在耍狠:“你看看,这事儿闹出来就都不好看。”“你也告不赢我。”
张欣回到卫生院,一个人住回了宿舍,有一次她发现宿舍停电,一看别人宿舍都有电。开大会的通知也唯独漏掉了她,她就知道是宋元在搞鬼。
张欣更加焦虑,回到老家,她发现妞妞不爱笑了。
而且她们家还来了一个不速之客。
那天,张欣给我发过来一张白色轿车的照片,我还没放大,张欣告诉我,驾驶座上坐着的是宋元。

与此同时,她家里坐着一个卫生院的女同事。
宋元悄悄绕过了监视,还叫上一名相熟的卫生院女同事,拉着对方直奔张欣老家说和。
宋元留在车里,女同事独自登门。
女同事进门后,好声好气劝张欣,别把事情闹大了,对孩子声誉也不好,张欣偷偷按了录音,我当时还表扬她做得好。
张欣的家人远远地拍到了宋元的车。
这些证据被张欣一一传给了我,她就问了一句:“为什么他可以随随便便逃脱监视?”
我通知王杰去和当地派出所协调。当地派出所说自己人手不足,答应会加强监视的力度。
女同事后来被公安叫去问话,依然是和事佬的语气:“我想着大家都是同事嘛,然后他让我从中说和,那就跑一趟。”
她撒谎说自己不知道宋元对妞妞做了什么事。警察也只能把人放了。
宋元的老婆比张欣还要委屈。她也是卫生院的医生,在卫生院四处扬言,说张欣诬陷她老公,想讹钱,她老公根本啥也没干。
我同事评价这是一个规律,有老婆的中年男人犯了性侵罪,打死都不会承认的,因为一旦松口,老婆就会和他离婚。
在这种小单位,其他同事在乎的不是事实的真相,而是不会被任何一方牵扯进去。
早些年就有人传宋元有前科,而且是两次。
张欣的一个女同事悄悄告诉她,“有一年下来实习的大学生,他就去骚扰人家。另一个同事的闺女,他也对人家动手动脚。”
张欣想以此向我证明,宋元的作风很有问题。
那两个女孩都是大姑娘了,宋元还会有些忌惮,可妞妞,几乎是任他摆布。
能对这么小的孩子下手,也许真的是因为,他曾经在其他女孩身上没有得逞呢?
无论如何,我并没有只把这两个线索当作一个证据,如果被证实,那两个女孩同样是被害者。

我本想催王杰去卫生院现场取证,问一下这个线索,没想到王杰的动作很快,直接把案件移送起诉了。
因为没有直接证据,罪名还只是猥亵儿童罪。
我只能按照审查程序,先去和宋元打个照面,翻案卷的时候,我才知道他以前因为犯敲诈勒索罪曾经蹲过监狱。
对付这样的人,更要精心准备。检察官接触不到嫌疑人,隔着案卷,我只能把他的照片几乎是刻在脑海里,想象质问策略,列好了讯问提纲。
在讯问室见到宋元第一眼,我都不觉得他陌生了。
我把提前拟好的讯问提纲拿出来,把最确凿的事实放在了第一个位置提问:“你有没有摸这个小女孩屁股?”
他承认得很爽快。但他根本不承认这是猥亵,说他家和张欣一家都是在卫生院的宿舍里住,平常免不了接触,也非常喜欢妞妞。
“因为太喜欢有时就忍不住抱一抱亲一亲,这不能算是猥亵,这是对小孩子的喜爱。”
果然,我还是低估了他的狡猾。
看着宋元厚颜无耻的样子,我音量陡然升高:“难道你不知道男女有别吗?妞妞三岁了,你把她的裤子脱下来去拍她的屁股,这合适吗?”
成年人罪犯往往比少年犯多一层伪装,同样身为成年人,当我知道他们在掩饰什么的时候,我总是想到那些被伤害的孩子,很难保持理性。
和我一起参加讯问的同事眼神示意我不要太激动。
同事说我办性侵类案件总是太不理性,零口供的情况下应该让证据说话。有时候我激动起来,卷宗拍得啪啪响,压根看不到他拼命给我使眼色。
我平复了一下情绪,尽量冷静地警告宋元:犯罪事实已经很清楚,没有口供依然可以定罪。我让他到讯问室外站着,去好好想想应不应该如实交代。
过了一会,宋元主动敲门进来。
他镇定自若,问我是不是脱掉妞妞的裤子、拍下她的屁股,就构成了猥亵,“如果是的话我认罪,但我可没有用手摸她。”
他表现得很是笃定,这种笃定仿佛让你相信他是无辜的。我在心里发誓一定会找出有力的证据,打碎这张笃定的脸。
宋元走了,我很怕这是和他的最后一次交锋。
起诉期只剩下不到二十多天,如果证据还是不足,我可能都没办法亲手起诉他。
讯问结束后,我第一时间联系了王杰,催促他带张欣母女去卫生院,补充妞妞辨认现场的证据,顺便调查一下张欣提供的那两个女孩的线索。
挂了电话,我打开民警随卷移送的硬盘。打开里面的卫生院走廊监控,看到最后,眼睛干涩头晕脑胀。
监控中,妞妞一个人在走廊里跑来跑去,她有时穿个小裙子,有时穿一个红上衣和白短裤,看起来无忧无虑。
宋元也是单独出现,几次进出画面,两人同框的画面一直没有出现。
在办公室关掉监控画面,我静静坐了一会,力气被抽走。张欣又打来电话,屏幕亮起,我第一次没有去接。

卫生院辨认现场的那天,我和王杰约定有情况及时沟通。
很快,我接到了王杰的电话,他不停叹气。
妞妞竟然把卫生院后边的两层小楼的每一个屋子进行了指认,这中间包括了张欣的宿舍、卫生院的餐厅、卫生院的仓库等12个房间。
这意味着妞妞对地点是没有概念的。即使她都点头,这份证据也不能算作有效证据,甚至对嫌疑人是有利的。
证据对我们不利,还是要随入卷宗中。
我让他再想想办法,重点辨认下那两个仓库,看看妞妞是否能够回忆起来。
不到十分钟,王杰告诉我,妞妞还是没有认出来。他有些焦急,天色已经接近傍晚,取证进度太慢了。
他带着张欣和妞妞走出这个小楼,张欣给妞妞买了一个长棍面包当晚餐,妞妞突然用手在面包上比出一个长度:“伯伯尿尿的地方像这样子。”
妞妞这是在就地取材!王杰几乎是立刻拨通我的电话。
我催他:“快再问一遍,录下来啊!”我们都知道这可能是案件的关键证据。
第二天,我等来了王杰送来的视听资料。他笑着说,里面是能够把宋副院长钉死的关键证据。
打开的一瞬间,我的心重重地揪了起来。
镜头摇摇晃晃,妞妞一直往前跑。
王杰边拍边追,并不轻松。我听到他催促张欣,管管孩子,让她别跑了。张欣手里拿着长棍面包,有点无措,一边喊妞妞,一边回头:“我也没办法!”
王杰猛追几步,拉住了妞妞,画面终于停了下来,我能看清妞妞的脸,王杰问妞妞:“你刚才说的他尿尿的地方什么样的,你再比一下。”
妞妞不愿意说,头摇得像拨浪鼓。
张欣蹲在妞妞身边哄着妞妞,让妞妞尽快配合王杰说出事实。这事实又是如此的不堪。
王杰问妞妞,那个伯伯是怎么用他尿尿的地方碰你的?
正好张欣下蹲着抱着妞妞,妞妞的脸面对着张欣,她把腿跨坐在了妈妈的腿上,说:“像这样。”
王杰又问,还有别的吗?妞妞又背对着张欣坐,趴在了张欣的膝盖上,“像这样。”
妞妞定格了几秒,身子好像微微颤抖。我的胸膛里被酸涩胀满。
或许是因为回到了卫生院,身边有妈妈,有警察叔叔,妞妞不再点头或者摇头。
“这个坏伯伯脱我的裤子,还用手摸我尿尿的地方,还用指头插进我尿尿的地方了。”她用手指指自已的裆部。
“还用这里碰我尿尿的地方了。”妞妞用手比划一个圈圈,左手手指指着右手圈圈的边缘。
“坏伯伯用他下边的东西顶我尿尿的地方了。下边的东西是硬的。”
妞妞还说疼,流血。
王杰问说流血怎么办了?妞妞说:“用纸擦了擦。”王杰问擦了纸呢?妞妞指了指自己的口袋。
王杰转头问张欣:“纸呢?”
张欣说不知道,洗衣服可能都扔了。张欣的脸看起来很是伤心。
妞妞说自己当时哭了,“但是坏伯伯说我是个大孩子了,不能哭,还用手堵住我的嘴巴,还说表现好的话带我找妈妈。”

妞妞诉说这段经历,没有再哭,遭遇性侵后,越小的孩子越不会哭。
一个三岁多的小女孩能够清晰描述出嫌疑人对她采取侵害时的体位,这说明侵害对她的影响有多深。
视频中传来院子里喧闹的声音,王杰取证心切,来不及把妞妞带到一个更隐私的空间。
我不知道画面外是不是有人围观,有没有张欣的熟人目睹了一切。
妞妞勇敢地从门内递出了一把钥匙,我小心翼翼地把钥匙伸进去,我多想抱一抱妞妞。

王杰后来找到了向张欣提供线索的女人,亮出警官证,请她借一步说话,女人却说自己从没说过这样的话。
只有卫生院的院长愿意配合作证,宋元手里确实有所有房间的钥匙,院长提心吊胆,宋元的职位毕竟是他任命的。
公安也没再补到更多证据。我向领导汇报案件的时候,科室的同事围绕罪名争论不休。
有同事认为保险点,就定猥亵罪。还有同事认为可以搏一搏,只定强奸罪,就可以把猥亵罪覆盖掉。
我坚持猥亵、强奸数罪并罚。我们已经从妞妞那里证实,宋元的性侵行为分多次,且程度不同,“猥亵就是猥亵,强奸就是强奸。”
到了午饭时间,办公室的白板上画满了交叉的证据链条和拼图,也没争出个结论。
一个罪名,还是两个罪名,就像讨价还价一样,想要一个可观的成交价,要价就要高一点。
我死死地抓住手里的证据,案件的起诉书依然写得很费劲。
时间、地点都是大概范围,因为妞妞记不得了。
开庭前,我和承办此案的法官讲了案件情况,我问他能判吗?他想了想,给了我一个接近于肯定的答复:“应该也差不多。”
开庭那天,因为性侵案件不公开审理,旁听席空无一人,妞妞和张欣没有到场。
法槌落下的声音好像比平常还要响亮。

宋元的律师指出妞妞辨认笔录时指出了餐厅这类公共场所,而这里不可能是性侵的场所。
他从妞妞指认的现场照片里挑出两个房间,问宋元:“这两个房间里住着什么人?”
宋元回答:“实习的大学生。”
大学生的房间,宋元和妞妞怎么可能进得去呢,“由此说明妞妞的陈述是不能采纳的。”对方律师抓住了妞妞证词的漏洞猛攻。
我的心情像是押中考题一样的澎湃。
在开庭前夜,我仔细地过了一遍所有的证据,知道对方肯定会提这个问题。
“妞妞平时就在二层小楼内居住生活,被性侵的场合和她平时生活玩耍的场所一致,她发生记忆上的混淆,从三岁幼儿的记忆规律上来看也是可以理解的。”
“妞妞虽然记不清场所,但肢体的记忆是捏造不出来的。我们还能要求一个三岁的小孩做到什么程度呢?”我完成答辩,看向宋元,他微低着头,没有看我。
他的笃定,在我和妞妞的律师不断提及证据的过程中被击碎了。
很多人不知道,我会穷尽办法从被害人那里知道更多的细节,哪怕这些细节残忍。但它能实实在在帮到那些孩子。
比如当时嫌疑人抱她,是左手先抱还是右手先抱,是什么样的姿势,通过这种更多的细节知道这个事情是真实存在的。这样才能让我在和一个不认罪的嫌疑人对质时有底气。
宋元在退庭前声声呼冤枉,说相信审判长会有一个公正的审判。
我冷冷地看着他。

我接到数罪并罚判决书的那一天,判决书后面附着宋元的上诉书。
没过多久,二审判决下来了,二审判决支持一审判决,宋元被判处有期徒刑九年零六个月。
后来,宋元的家人又提起申诉。案件由上级检察院副检察长包案办理,我一次次联系王杰打包案卷,往上级报材料,证据分析图表,并向王杰保证我会留存材料,不再麻烦他。
上级打来电话,不停向我发问:为什么?
我在脑海里回想这个案子一路至此的全过程,停在了妞妞趴在妈妈身上的样子。
我承认这个案件的证据是薄弱,但是小女孩可以描述出姿势,我还是坚认这个案件应该是一审的结果。
电话那头的检察长还想说什么,最终也陷入了沉默。
后来我又很多次打开那段妞妞现场指认的视频。
每次按下播放键,我的心跳就不受控制,随着摇摇晃晃的镜头起伏,揪起来,落下去。
也许是那栋小楼里,只有妞妞跑了出来,而另外两个被副院长宋元侵犯过的女孩,选择了沉默。
我感觉就像是打开关着妞妞的门之后,发现紧闭的两道门,探不到里面。
我办过这么多性侵案件,一站式询问中心里送走一个被害者,还会来下一个。
我们做了相关的调查报告,去向市里汇报,要求每一个学校都给孩子们开展保护自己的课程,建立防性侵的专门的工作方案。
依然会有孩子因为受伤害,走进一站式询问中心,但他们起码会意识到自己受到了伤害,能更快地求助家长,报案。
有一个幼儿园的女孩,被玩伴的爷爷猥亵,她玩命挣扎,一边大声喊:“不要摸我!不要这样子!”
嫌疑人看到这阵仗,立马松开了她。小女孩马上跑回家告诉了自己的妈妈。
一站式询问时,她告诉我,老师讲过,她知道这是不好的事情。
我心里说不出的高兴,女孩不再沉默,女孩也不该沉默。
我成了给孩子发钥匙的人,有孩子从门里自己走了出来,开门的声音足以回响在一起,让依然被困在门里的孩子听到。
真正该被关进去的,不该是妞妞,也不该是那两个沉默的女孩。

这个案子的检察官凌十八告诉我,儿童是最弱小的。因为大人对他们施暴是如此容易,而让他们说出自己被侵害的过程,却非常难。
但好在,有越来越多的学校,给孩子开展了保护自己的课程。有一些,还建立了防性侵的专门工作方案。
也有越来越多的家长,对孩子进行性教育了,这样起码让孩子能更早意识到自己受到了伤害,能够更早地求助家长,学校,报案。
最后,凌十八也特意为大家准备了一份未成年人防性侵指南。
这些小技巧虽然很微薄,但她相信,只要这些提醒能多被一个成年人了解,就有机会多让一个孩子免于侵害:
1、尽量不要让孩子离开家长的视线。
很多性侵案都发生在熟人之中,不要相信邻居、亲戚等这些你认为的熟人。
2、帮孩子分清安全触碰和非安全触碰。
从孩子两岁起,就要告诉他们哪些部位不能被别人看和摸,比如,摸头和拍肩是安全的,但隐私部位不能给人随意触碰。如果孩子难以理解,可以用绘本帮助他们记忆。
3、告诉孩子尽量不要和异性单独呆在一个空间。
4、跟孩子强调,面对让自己感到不舒服的接触,一开始就要大胆说出来。
告诉孩子想吃什么、想要什么玩具、或者想做什么事情,一定要告诉爸爸妈妈。不要因为别人提供这些,就允许他们做一些让自己感到不舒服的事。
凌十八曾悄悄跟我说,她特别想让这个故事被更多人看到。
或许最终,坏人也不会消失,但是希望越来越多这样让施暴者受到惩罚的案例,能够威慑到潜在的混蛋们。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编辑:猴皮筋 小旋风
插图:徐六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