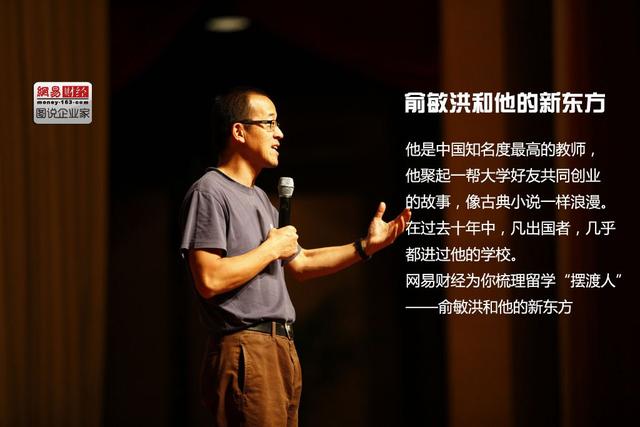#两岸文化寻宝#
作者:陈向阳 发表于青岛故事
这是我生命中的一件大事,发生在35年前,多次想写出来,终究不敢落笔,唯恐写不好,道不出我当时的情感。这是我有生以来,在我四十岁的时候,第一次有机会见到我的骨肉同胞,血浓于水的手足。在渤海边塘沽湾畔,与我的大弟第一次相见了。
我们家在台湾有六个人,我妈妈和我的五个手足,我身下两个妹妹,三个弟弟,都是我爸妈去台湾以后出生的。四十年来,我最先见到的,是我的大弟。自从1983年我与家人互通音信之后,由于两岸关系还是没有三通,第一次与家人相见,竟是以这样的方式,事情竟然来的那么突然。
那是在1987年的12月份,冬至的那一天,我下早班,回到家,姥姥说从日本来了一封信,我打开信,看到落款是大弟,信中说他的船要到天津塘沽港运盐。具体时间让我到青岛外代询问。

当时的信很慢,我收到信的时候已经错过了大弟到塘沽的时间。但是,我还想试一试,不想错过与大弟的历史性的初次会面,我赶紧的拿着信,跑到了馆陶路的青岛外代,当时我家住在博兴路,到了外代,给他们看了大弟信中的内容,他们马上帮我查到了大弟的船,而且给天津外代打了电话,经过确定,对我说,你大弟的船还在天津塘沽的外锚停着,根据大弟说的日子,已经错过了将近一周的时间。我将信将疑,我以为青岛外代也可能查错了,不管怎样,我也要试一试。
晚上,我去了火车站,买了当天晚上九点多的去天津的火车票,一切都是在激动、紧张、忐忑,期盼中进行着,不知道此次会面能否成功。那时的联络方式主要是靠信件。
第二天上午九点多到了天津,那时的火车很慢。出了天津站,在火车站旁边有个长途车站,又坐了四个多小时的长途车,到了塘沽,边走边打听,找到塘沽港,那时的塘沽还很荒凉,一路上枯黄的芦苇在刺骨的寒风中摇曳。

我找到了塘沽港外代办公室,把大弟的信给他们看了。他们说,因为没有泊位,大弟的船确实还在锚地停着。这下,我终于可以放心了,虽然错过了大弟信中的时间已经一个星期,但是大弟的船一直没有进港,还在锚地停着,那是大弟的船第二次来塘沽,往日本运盐。
大弟就职于台湾的远洋公司,担任船长,他们的船挂着巴拿马的旗帜,当时的台湾国民党还限制民众到大陆,大弟第一次到塘沽装盐,没敢跟我们联系,在天津观察了一些风声,感觉很安全,装满盐,很顺利的就到了日本,到了日本,大弟马上给我发了一封信,说他还要第二次来塘沽装盐,让我去天津塘沽港等待姐弟相见。这真是突如其来的令人振奋的大好消息。激动兴奋的心情无以言表。
我当时在纺织单位保健站工作,跟着车间上两班,保健站一共九个人,只有我和顾大夫两个人早、中两班轮流倒换,其他人都上常白班。
接到大弟来信的那天,我上早班,顾大夫上中班。我和顾大夫商议,能否替我几天,她很爽快的答应了。就意味着她要连续上早六到晚十,连续一天工作16个小时,很辛苦。回来后,我再替她。当时估计也就最多三天,没想到顾大夫替了我七天。
到天津的当天下午,我就去了塘沽外代办公室,他们办公室有个靠背长条椅子,我坐在那里等,等他们的消息,大弟的船进港,是他们根据泊位来安排。
连续坐在那里等了五天,大弟的船才有泊位。在第三天的时候,外代的工作人员对我说,给你弟弟打个高频电话吧,他可以下船你们相见,我不懂的高频电话很贵,是大弟拿钱,他们拨通了电话,大弟对我说,他不能提前上岸,因为他是船长,不管什么原因船长都要最后一个离船。
大弟说让我再等等,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有泊位。后来才知道,实际情况是大弟要拉的盐,还没有生产出来,谎说没有泊位。那天早上,我照例在外代办公室等,那几天坐在外代,看着他们工作,听着他们谈话,经常听他们说,这个船长很年轻,工作能力很强,英语很棒。以后才知道他们说的是我的大弟。
12月27号那天,我照例按时到了外代,他们说大弟的船,下午就有泊位了,下午四五点钟就能靠岸了。实际上是那个时间盐就能运到港口了。塘沽盐场是国内最大的海盐场,位于天津市海河口。

我中午早早地吃了饭,焦急地赶到停船的岸边等候,那种心情真是无法形容。
那天的气温是零下11度,天津塘沽比青岛冷多了,青岛最冷也就零下6度,海边的风呼啸刺骨,岸边的石灰地也很空旷,没有可以挡风的地方。
我穿着单位发的戴帽子的过膝盖的红色呢子大衣,还是瑟瑟发抖,不停地在地上跺脚,眺望着远方,也不敢回招待所等候,就怕错过大弟的船进港,相见的每一分钟都是那么的珍贵,深深地体会着血浓于水的亲情。期盼大弟的船能快点出现。
我中午在外面买了三斤羊肉馅的生饺子,心想在大弟船上能吃两天。饺子放在个手提塑料袋里装着,我虽然带了手套,也不济于事,两只手轮换着拿,手冻得针刺样的痛,饺子也都冻成一坨了。
下午四点多的时候,远处的海面上,一艘远洋大货轮缓缓地驶了过来,船靠在岸边,放下了扶梯,传送带立即开始往船舱里装盐。大弟下船把我接上了船,当时,我的脑子一片空白,还是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到了大弟的船长室,里面真暖和。我看过爸爸的照片,大弟长得像爸爸,年轻英俊,穿着船长制服,气度不凡,这就是我曾未见过面的亲弟弟,我心中格外的自豪。
大弟让船上的厨师去下了饺子,那么好的饺子,下熟了就没有饺子样了,姐弟第一次见面,谁也没有心情吃饭,厨师过来对我说:“你要是不吃,就都扔了。”虽然感觉很心疼,但也得入乡随俗,看着大厨把饺子都丢进了垃圾桶。很是不舍,那时候我们两岸的生活水平,差距还是很大的。
我和大弟并肩坐在沙发上,谈了很多,大弟说他拉了这次货,就从日本回台湾了,准备考领港。大弟把他的松下牌的双卡收录机和他用的冰箱都送给了我,还从衣服口袋里翻出360美元,硬塞进我的口袋。
从大弟的谈话中知道大弟对妈妈很孝顺,他说没有妈妈就没有他的今天。大弟还讲了二弟是台湾最年轻的远洋船长,大弟比二弟晚了一年考的船长,是因为大弟当了一年兵。说了我的大妹和二妹也都很优秀。大弟就是没有说自己。
大弟送我的冰箱,我用了10年,睹物思人,以后经济条件好了,也没舍得换。直到1997年搬新家,才恋恋不舍地告别了那个冰箱。在国内用,要加变压器,一天消耗一度电,变压器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还嗡嗡作响,即便是这样,我也不舍得换掉。
我没有办上船证,是不能在船上过夜的,晚上,十点多,大弟送我回招待所,那条路还挺长的,要走十几分钟。,因为船长室里很暖和,我感觉大弟被刺骨的寒风冻得瑟瑟发抖,我摸了摸大弟的腿,他就穿着一条单裤子,我把大弟的手放进我的大衣口袋里,那条路并不平坦,路上也没有开灯,是靠着周边窗户的灯光照亮,否则,真是伸手不见五指。
我住的外代招待所很简陋,房间里有三张木板床,只有我一个人入住,我对前台服务员说,再加一个人的住宿费。大弟很累,躺在床上和我聊了一会儿就睡着了,我怕吵醒大弟,蹑手蹑脚地给大弟把皮鞋脱了,又轻轻地给大弟盖上了被子。
我拿了个凳子,坐在大弟床前,仔细地端详着大弟。这就是我的骨肉同胞,此时,我的心情依然激动,我舍不得睡,尽管我也很困,因为等大弟回到了台湾,就不知何年何月再重逢!我珍惜能和大弟在一起的分分秒秒,就一直在大弟的床边坐到了天亮。
那年我四十岁,大弟34岁,我比大弟大六岁。我们家孩子一个比一个大两岁,只有大弟和二弟之间差了三岁,妈妈先生了三个女儿,又生了三个儿子。
那一夜,我一直没有合眼,就那样看着大弟睡着,唯恐这一别,不知以后能否再相见。这是四十年来我与家人的初次相逢。
第二天上午,大弟找人把冰箱抬到了仓库里,等我回青岛后找车拉回去,我陪着大弟到外代办公室办理了船靠岸需要办理的一切事物,大弟说,船靠岸后,船长是最忙的,大弟不停地用计算器计算着上水,上油,食物补给等等,大弟的业务水平令外代的工作人员很是钦佩 。
中午,我们在离岸边不远的一个小饭馆吃了饭,吃的什么我也记不住了。时间在分分秒秒地流逝,那种离别的忧伤,控制不住的泪水顺流而下。大弟说:“他们的船装满了盐,就要起航了,吃完饭,我们就分手吧!不要等到他开船后我再走,那种离别的情景我们都会很难过。”
下午三点多,我去了塘沽火车站,大弟回到了船上。我们姐弟俩在一起的时间总共不到24小时。
我在车站站台等到一辆从东北过路的车,车上满满的东北兄弟,扁担,麻袋,竹筐,这趟车如果挤不上去,就没有车了,我拼命地往上挤。在列车员的用力推搡下,终于把列车关上了门。

这是一列小站车,逢站必停,有上也有下的,在门口很不安全,我拎着一个背包,肩上扛着大弟送我的收录机,被人挤住了,一动也动不了,挤压的呼吸都感到困难,加上两天没有吃饭,腿哆嗦的很软,却也不用担心站不住。
这种拥挤,比我在青岛坐过的最挤的公交车都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样子,要坐一夜的车,明天早上才能到青岛,我实在坚持不住了,问列车员说:“有没有卧铺啊!”他说:“有啊!不过,在前面四五节车厢,你从车厢里是挤不过去的,你得从车门下去,到一站就往前跑,跑几节车厢算几节,跑到卧铺就好了。”
我在列车员的帮助下,挤到了车门,只要停下车,我就拼命地往前跑,听见火车响鸣,我就赶紧挤上车门,再等下一站,这样我跑了三次,终于到了卧铺车,车里空空的,一个人也没有,我补上了卧铺票,浑身哆嗦着躺在了床上,天已经黑了,也没有准备吃的,车上也没有卖饭的,喝了几杯水。
第二天早上,总算到了青岛,回到了家,对姥姥说了和大弟相逢的点点滴滴,姥姥陪着我一起流眼泪。下午,我就去上班了,顾大夫已经替我一个星期了,心中也是感激不尽。
四十岁这一年,是我命运的一个转折,从天津回来后,大弟回到台湾跟妈妈讲了我们姐弟的会面。妈妈也急于要母女相见,1988年的一月份,我接到妈妈的信,邀我去香港母女会面,一起过春节。
春节的前几天,我的大妹也到了香港,我们母女三人经常畅谈到深夜,那年,我妈妈61岁,我大妹38岁,我们在旅馆里度过了一段刻骨铭心的团聚时光。
仅以此文祭奠逝去一周年的妈妈。安慰她的在天之灵!

后记:
写完此文以后,发给我台湾的大弟,他看了文章以后半夜给我回复了短信。
亲爱的大姊:您好!87年的尘封回忆,历历在目、历历如绘,仿佛昨日塘沽相会是我一生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如果不是货未备妥,相逢将是憾事连连,想来是天意,是奇迹。同时也了却妈妈一生的遗憾与最大心愿!
如今我也将届70不逾矩之年,这35年前的手足相逢,真是往事并不如烟,在此我们互道珍重,珍重再次相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