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三月,新冠病毒肆虐全球之际,美国著名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在《纽约时报》刊文,提出一种新的历史纪元划分:新冠肺炎元年前与后,借此讨论存在不同差异的人类文明付出的改变与牺牲。

但不知道他有没有考虑过当新冠病毒踏上恒河流域这片神奇的土地,会有怎样的不凡之旅。
有别于提及新冠流行便大谈“失去”的消极语气,一项属于印度人独家回忆的风俗异军突起,迎来了勃勃生机、万物竞发的境界,使得去年的新闻也犹在眼前。

从互联网兴起到如今,总有印度人对“祖传秘方”的热爱非比寻常。
这儿的某些医生坚信,圣牛的排泄物是神恩天赐,能包治百病。他们孜孜不倦、以身作则,开导邻里内外不拘一格、趁热即食。

(“不喝不知道,喝了都说好”)
即便邻国的同行们已在数月的抗疫之战中为全世界提供了科学的防治方案,然而在印度信者寥寥。更抵挡不了这帮印度人面对金汁那股105℃的脉脉含情。
种种迹象表明,这类原汤化原食的宣扬者,似乎并不因受教育程度而对信仰有所疏离。

(传说中的八学博士就是您?)
马诺伊·米塔尔,一位来自卡尔纳尔县、在推特上有迹可循的医学博士,站在牛棚里就地取材。
他向“今日印度”(India Today)亲自示范了纯天然的服用方式,竭力证明自己从娘胎开始便与圣物缘分不浅。
这种“行为艺术”显然曲高和寡,令乌鸦只能深吸一口气。

事实上,对于这位医学博士的宣称,连不少坚信科学主义的印度人都看不下去,纷纷在评论区留下了愤怒的文字。

然而,米塔尔博士的面部表情中,分明洋溢着大快朵颐之后的情真意切。
他狂热且虔诚,当块状物融化在舌尖,立刻发出了由衷的赞叹。那一刻,米塔尔的灵魂离湿婆神更近一步,肉体却与希波克拉底渐行渐远。
凡此种种,互联网上尚且有人口诛笔伐。
可若一旦脱离刻意审视,推为民俗,那便信马由缰了。

(“说句痛快话,投翔不投翔?”)
相比于城市,米塔尔博士的受众显然在基层行政单位更受欢迎。
这儿是现代文化的沙漠,宗教占据绝对上风。
大便小便,都因教义的反复诠释而升格,被赋予更多的吉祥含义。

(隆重推荐“八氏消毒液”)
公允地讲,老八若是在印度农村,绝不会有在中文互联网那样一战成名的契机。
上有专家博士,下有乡野村民,印度在牛粪牛尿这一块总有太多的出人意料。

(“咖喱池沼,牛粪大战”)
是什么让印度人如此与众不同?
在印度,以婆罗门教为中心的社会意识形态如同一道帷幕,将诸多现代意识阻挡在外。
这道帷幕的厚重往往又因种姓、民族、阶层而异,时而遮天蔽日,时而薄如蝉翼。

例如高种姓代表精英,盘踞资源中心,接触现代意识自然容易;低种姓人群散落于社会边缘,医学的曙光照不进,于是几千年的宗教文化、统治阶级驭民之术所形成的意识形态,便横行乡里。
狂热印度教徒对牛粪的痴迷,源自“圣牛观”的深入人心。而一说到牛为什么在印度被奉若神明,不予宰杀,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印度人,都会说一句:宗教使然,历来如此。

(印度圣牛,肩上有峰,称瘤牛)
从来如此,便对么?
更应该问一句,真是“从来如此”吗?
其实今日印度所谓圣牛信仰,即对牛不杀不食,又美名“牛五样”(牛奶、凝乳、黄油、牛粪、牛尿),根本不是印度文明一以贯之的。
印度文明史,通常以吠陀时代作为开端。

吠陀时代是公元前十五世纪开始,西方游牧民族雅利安人入侵印度半岛,消灭印度本土哈拉帕文化后创立的。
雅利安人入主印度半岛期间,沿恒河逐渐形成农耕文明,就此定居,形成对当地人的统治。
为有效统治达罗毗荼人(当地土著),婆罗门教(吠陀教)应运而生。其中,种姓制度表面以祭祀等级规定人之贵贱,实则区分敌我、土客以及统治与被统治阶层。

毫无疑问,种姓制度是婆罗门教的灵魂,而婆罗门教则是留给印度人最宝贵的“遗产”。从设计之初,婆罗门教就远超宗教范畴,实则是阶级统治的工具。
同一时期,牛也被划分为三六九等,其中以印度本土特产白瘤牛为至尊,因其是婆罗门神话中湿婆坐骑。相比白瘤牛的圣洁,黑水牛则是雅利安神话中邪祟化身。
所以,印度之所以成为当今世界第一牛肉出口大国,靠的是砧板上的水牛,而不是庙堂里的旱牛(相对于水牛而言的瘤牛)。

现在,绝大多数印度人愿意相信:婆罗门教兴起之初,便首倡不杀生、尊牛为神的教义,以此为自己尊牛的行为寻找绝对合理、不可侵犯性,从而强化对本民族、本宗教的归属感。
走进这种误区,就好似觉得和尚自古以来便戒荤一样。
事实上,从孕育婆罗门教的吠陀时期开始,到公元第一个千年中期,整整1500年的时间,所有的牛既非神圣,亦非不可宰杀。

(《梨俱吠陀》,四吠陀之一)
身为游牧民族,杀牛吃肉对于雅利安人乃寻常事。这个时期诞生的婆罗门教经典《四吠陀》,明确记载着牛的各种用途:祭祀、食用、陪葬、送礼。
如今的婆罗门种姓却严禁宰牛、食牛,殊不知,他们吠陀时期的祖先,正因其宗教职责(祭司)而成为屠牛的主力军。
当然,牛作为宝贵的财产,必然不能浪费,当被用作祭祀品宰杀后,就会进入婆罗门及其随从如刹帝利、吠舍口中。

正所谓“牛肉穿肠过,梵天留心头”。截至目前,婆罗门教教徒们在自身宗教存于世的近一半时间里,是宰牛、吃牛的常客。
《梨俱吠陀》里,确实存在禁止屠牛的要求,但只是禁止正在产奶的牛被杀。原因也很简单:母牛产奶供给雅利安人日常营养,这完全是出于一种利益衡量。
这个时期,《四吠陀》中不断出现诸神对牛群争夺的神话性叙事,常常被视为圣牛崇拜的起源。可是,雅利安人本就是多神信仰民族。
而且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的先民都表现出多神崇拜。面对自然界为其所用的动物,感恩归感恩,也不耽误宰了下饭。

(就比如这样)
本世纪初,德里大学历史学教授吉哈出版《圣牛神话》。该书详尽整理了古印度教中的吃牛肉行记叙,点破食牛肉并非来自伊斯兰世界的“祸害性馈赠”,平地一声惊雷,试图敲碎婆罗门教徒脑海中圣牛神话起源的构想。
然而,现在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并不愿相信这个事实,他们宁可指责是异教徒穆斯林首创屠牛恶习,亵渎了婆罗门的大地。
这位教授也因此收到渎神指控和人身威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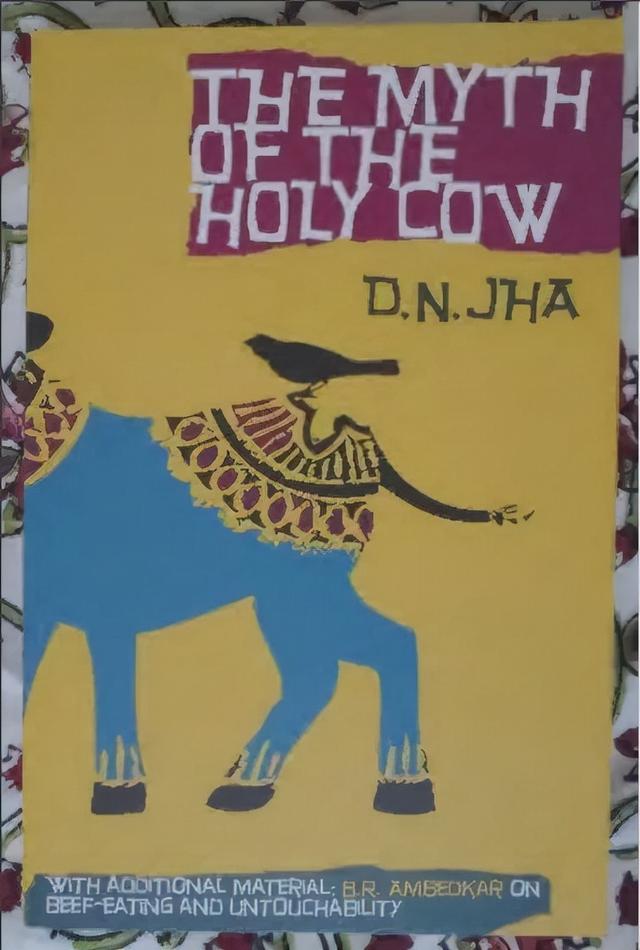
在游牧演变为农耕文明的背景下,牛作为畜力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吠陀早期,雅利安人靠掠夺土著兴许还能维持牛肉消耗,然而一旦从“臭外地的”自命为中原之主,就不得不与所有农耕文明一样,面对牛源紧缺的问题。

然而,牛资源稀缺只构成了珍视与溢价。高种姓者凭借权力,更多地囤积、拥有了土地、耕牛等生产资料。首陀罗、达利特们不是不想吃,而是吃不起。
从此开始,吃牛的权利就开始与下层种姓渐行渐远。
而让高阶种姓放弃吃牛肉,则与婆罗门教地位不保有关。
公元前五世纪左右,吠陀时代结束。与此同时,印度社会生产力提升,大量出家沙门不事生产、思考真理,出现了各种非婆罗门思想,最后诞生了婆罗门的最大对手:佛教与耆那教。

(耆那教庙)
相比于婆罗门教,这两教最鲜明的特点是提倡“不杀生”(非暴力)。
对于典型的农业社会,大肆宰牛献祭、食用这种婆罗门的核心文化是对底层的轻视、规则的违背。
低种姓者对婆罗门的饕餮不满,新兴的佛教与耆那教因此吸引了无数信众。
公元前三世纪,统一北印度的孔雀王朝君主阿育王皈依佛教,更是深深加重婆罗门的不安。

危机之际,婆罗门阶层及时悟道:打败敌人的最好方式是加入他们,并走向更极端。
婆罗门阶层不仅摒弃了活物献祭、食肉习俗,而且直接改吃素。“苦一苦婆罗门”、消除低种姓人群敌视,弥合了“不良特性”的婆罗门教东山再起,大获人心。
于是在今天的印度,高种姓人群又往往叠了个素食主义者的buff。

(自称低种姓的老仙,却维系着素食主义的“高端习俗”)
可在婆罗门地位稳固后的几百年时间里,仅仅是婆罗门这个种姓将牛肉视为禁忌。
要到公元五世纪左右,婆罗门才在教义中将屠牛列为一项小罪,声明“牛肉至少不能进入婆罗门的菜单”。
至于婆罗门以下的种姓吃不吃牛,那是他们自己的事。
然而,婆罗门教占据统治地位的时间越久,沙门辩经就会将真相越辩越分明。

一想到祖先“八百里分麾下炙”的事迹迟早露馅,高种姓便想方设法造了一堆古吠陀经典,再寻章摘句地诠释:咱们正婆罗门是尊牛为天神的,生于平原上,日饮恒河水,你们还敢吃牛肉?蛮夷!
士大夫才能讲经,老百姓有几个会去辨个分明?更何况,讲得多了,连统治阶级自个儿都信了。
种姓制度下等级森严,但仍存在一种潜在的社会流动方式,在印度沿用至今,被称为“梵化”。
梵语,即雅利安人、正婆罗门的母语。梵化即是低种姓群体抬高地位变为高种姓、实现阶级跨越的过程。

(婆罗门)
比如某个村庄里铁匠职业群体自古以来是较低种姓吠舍,在一段时期内发了战争财,群体经济实力大为提升,就往往会进行集体迁移。
迁移后再通过向新居住地的统治阶级打点,或贿赂、或编造祖先故事,将种姓重新认证为刹帝利,彻底改变社会地位。
梵化过程中,新贵们对老财(old money)文化的追逐、模仿,势必也让他们摒弃吃牛肉的爱好。于是在婆罗门教治下,高种姓禁忌食肉、低种姓没条件食肉、梵化人忍痛割爱。

三者构成了伊斯兰势力入侵前,印度社会禁食牛的松散默契。
这还没完,接下来的千年里,从德里苏丹国到莫卧儿帝国,穆斯林统治者与他们的文化在这片大陆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而在苏丹铁蹄驾临前,印度的民族构成就已极为复杂:希腊、波斯、突厥、月氏,有啥来啥。古印度与古中国截然不同,不存在清晰的主体民族。
然而,为与吃牛肉的穆斯林划清界限,一向含混不清的“Hindu”词义变得明了。
它用来指代所有印度教教徒对自己作为次大陆主人的身份认同,尽管他们的祖先多半也是外来者。

(突厥穆斯林入侵)
即便印度教(以婆罗门教为中心的泛称)复杂细分为各派各宗,彼此纷争也不断,但面对食牛肉者兼异教徒穆斯林,坚守阵地成为了各派系掌教者的共识。
一方面,婆罗门从穆斯林身上看到了从前的自己;另一方面,早期的穆斯林统治者对印度教徒的态度极不友善,灭其文化,迫其改宗。
婆罗门们对再次失势深感恐惧。同时,他们发现,护牛议题是最能强调宗教边界、最能广泛动员印度教徒的武器。
于是,对教义的再诠释、极端化在所难免:母瘤牛即母亲神,身体发肤即为圣物,谋杀瘤牛即是谋杀三主神。

(梵天、湿婆、毗湿奴)
底层的印度教徒越反感穆斯林,就越得以彼此对牛的态度划清界限,圣牛不可侵犯的观念正式塑成。而周身涂满牛粪就是识别敌我的一种极端表现。
到了伊斯兰贵族统治后期,疲于军事控制的君主们,终于学会利用印度教顺化万民,与婆罗门实现双赢治理。
莫卧尔帝国的多位皇帝都曾颁布禁屠母瘤牛的法令,第一位莫卧尔皇帝巴布尔就教育其子“这会帮你赢得人心”。
等到莫卧儿帝国湮灭,远道而来的英国人如法炮制,仅以20万左右的基督徒(官僚、军队及配套移民)统治印度3亿人口长达一世纪。
统治者的玩法升级,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异教民族间的相互理解。

英属印度前期,尽管底层印度教徒对穆斯林屠牛、食牛肉的行为不满意,但他们选择了宽容与克制。而大多数穆斯林作为“新来的”,也感恩这种宽宏大量,尽可能地不去伤害印度教徒的圣牛情感。
然而,随着大英殖民统治的推进,印度民族解放、宗教独立意识空前高涨。
英帝国统治后期,一系列婆罗门阶层为主构成的人群,发起“圣社运动”,主张原教旨主义、回归吠陀时代。他们利用维护圣牛不可侵犯为议题,旗帜鲜明,一边反英国殖民,一边驱逐穆斯林(他们都热衷于吃牛肉)。
这些宗教运动很快走向狂热化,于19世纪末造成了北方的大规模暴力冲突。

维多利亚女皇甚至主动承认,这些暴动实际上是针对英国统治的,因为英国人为供应驻军宰杀的牛远多于穆斯林宰杀的。但对于广泛参与运动的低种姓人群,反伊斯兰的宗教观念更浓,因此他们的目标仍然是穆斯林。
接二连三的宗教社群运动虽然狂热,所普及的圣牛崇拜、印度宗教共同体意识却极为成功。印度人如今心目中的圣牛观,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次跨种姓的强化。
现在我们知道,圣社运动倡导者们笃信的原教旨,也不过是他们的婆罗门祖先杜撰的。
但现实就是如此荒诞:圣牛不可侵犯的概念,就这样从无到有,从捏造到坚信,从庙堂入沟渠,走遍了印度教信众的几乎各个阶层。
值得一提的是,如今印度食用圣牛肉的人群,除了远离政治中心的穆斯林,还有婆罗门教贱民达利特(第五种姓)。

(掏粪工,达利特的典型职业)
因地位低下,不少达利特从事着处理动物尸体、剥死牛皮的工作。
圣牛死亡对于他们来说,反倒是一种恩赐。
毕竟压迫太过残酷、生活太过艰苦,而眼前的牛肉是不可多得的营养品。即便被高种姓所鄙视,那帮人只不过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罢了。
不可否认的是,对圣牛虔诚的印度教徒增多了,但现实的印度农民同样不少。
若禁屠牛观念缺乏法律保护,供养不起圣牛的底层教徒,即使表面上不亲自动刀屠宰圣牛,但该卖给穆斯林屠户还是会卖。

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在印度,支配性的高种姓阶层不超过总人口的15%,他们中间的印度教传统主义者构成了共和国建立前后的多数派。
此时的尼赫鲁,虽身为国大党领袖,却显然代表少数派。尼赫鲁对新国家的最初构建是,印度绝不能以印度教国家行于世。他希望印度共和国是“给予所有宗教自由……不偏向任何一种宗教的多民族世俗国家”。
他心里明白,让禁屠牛(母瘤牛)条款进入宪法,就是赋予了印度教特殊地位。
然而,整个制宪会议过程伴随着印巴分治前后的动乱。国大党中的印度教传统主义者声势浩大,尼赫鲁最终选择了妥协。
有趣的是,传统主义者们在这场斗争里,引用已故领袖甘地对母牛的深厚情感游说政府。
但其实,甘地虽是母牛保护的大力倡导者,却反对任何强制性的禁屠措施。

传统主义者的胜利一直维持到今天,甚至愈演愈烈。结果可想而知,他们的意志引领整个国家、整个印度教民族的圣牛观日趋极端。
起初,禁屠牛令尚能允许印度各联邦视本地情况做修改,照顾各民族各宗教的情绪。到如今,诸多联邦不仅将禁屠牛的范围扩大到公牛、阉牛,还加大了惩处力度。
这种背景下,极端社会现象层数不穷:狂热印度教徒动用私刑,杀死村庄内的穆斯林屠户;连政府护送流浪牛前往牛庇护所的车队,也遭到狂热印度教徒的攻击。
2001年,极具威望的印度教上师商羯罗在游历之时,看到母瘤牛被屠宰,公开声明:若政府不解决这一问题,我将绝食至死。
印度政府立刻展开行动,成立全国牛类委员会(简称RKA),最终得出一份《全国旱牛调查团报告》。里面着重论述了“牛粪牛尿革命”的价值。

(RKA官网文章)
学者们认为,牛粪牛尿千年用作燃料、肥料,对有机农业的作用十分重要。此外,他们强调牛粪、牛尿具有多样的使用价值包括重要的医药价值。
因此他们得出结论,即使旱牛失去了农业生产用途,其多功能属性不可取代。
可矛盾在于,如果牛粪牛尿的利用价值真的如他们所言,能大于旱牛的饲养成本,基于利益衡量以及市场呈现,农民绝不会将自家的圣牛转卖、抛弃。
理性的农民们,至少能从这一点感受到圣牛观的摇摇欲坠。
但与此同时,高种姓的宣传机器,却在不遗余力地把牛粪牛尿推广向全印度、乃至全球。
RKA牵头之下,工业化生产牛尿饮料粉墨登场。

宗教诠释与现代思想的融会贯通,碰撞出开发新功能的火花。
作为一个新时代印度人,你应当知道,牛粪退可防辐射,进可造芯片。

女议员的乳腺癌的治疗方法、前总理80岁精神矍铄的秘诀,更无需多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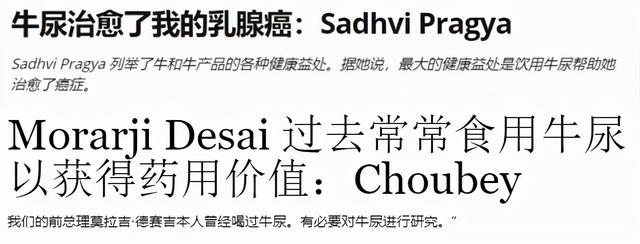
从划分种姓的印度教诞生之初,到吸纳不杀生理念、伪造圣牛信仰,婆罗门的目的始终是统治、压迫他的人民。
后来这片大陆的名义统治者走马灯般变换,他们在幕后却始终身居高位、把持权柄。
一般来说,统治阶级对于祖先创造的驭民之术,应当是拎得门儿清。然而,这种驭民之术越悠久,婆罗门的子孙们就越混淆先民初衷。
尤其是“圣牛不可侵犯”的话语,令它日渐自大与极端。

(向冠状病毒漫画喂牛尿,以作抵抗)
除开被洗脑干净的顺民们,到如今,越是穷困、被压迫的群体,越不把圣牛信仰当成一回事。而高种姓的表现却截然相反。
统治阶级的祖先们苦心经营次大陆几千年,反倒把自己的子孙忽悠瘸了。
参考资料:
王晴锋:印度圣牛观解析——基于宗教、历史、理性选择与文化唯物主义
王晴锋:印度圣牛、种姓政治与教派冲突
吴晓黎:解析印度禁屠牛令争议——有关宗教情感、经济理性与文化政治
杨怡爽:印度“牛粪经济”的文化政治经济根源
钟德志:吠陀时代印度“圣牛”神话初现研究
尚会鹏:种姓的社会流动及其理论
马文·哈里斯:印度圣牛
经济学人:印度政府正在往粪里撒钱
半岛电视台:印度"奶牛科学"考试因"教学大纲争议"而推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