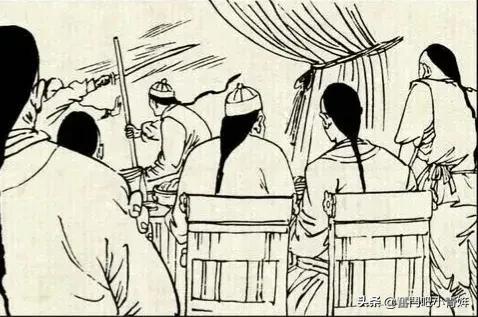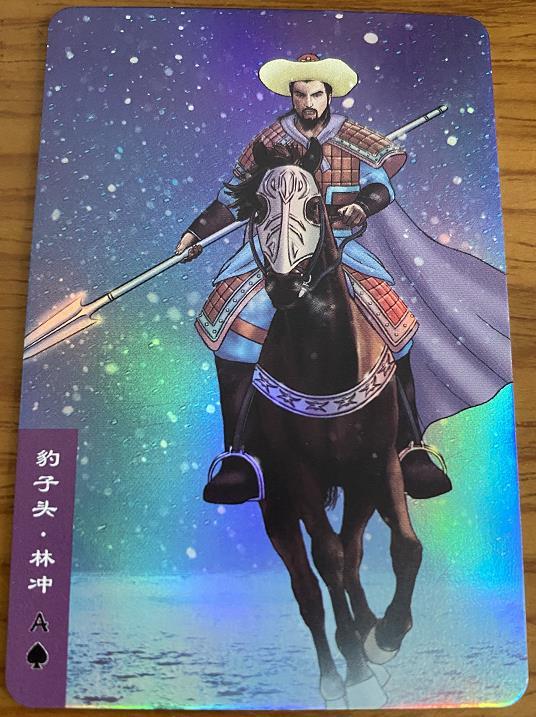詹湛 译
谈到树木,我想说一个难忘的故事。一位名叫中岛健三(Kenzo Nakajima,近代日本文学评论家,1903年出生于东京)的朋友,去世之前几天,在几乎丧失意识的状态下告诉家人,他死后会在那株树下呆两个月时间—— 他说,那株高高的树。他所指的“高高的树”,是栽在他院子西北角上的那一棵。
他生病之前曾经这样对朋友说:哪怕在没有风的时候,这株“家伙”的叶子都会颤抖,并流出歌声。我听说,在他最后的日子里始终抱以巨大的兴趣,从病床上朝他所说的那株树凝望过去。
后来我参加了中岛健三的葬礼仪式。可惜那次我却没能从仪式空间的角度望见那株树,也许它是被什么遮挡住了。中岛健三先生去世不久后,泷口修造(Shuzo Takiguchi,诗人,批评家)先生也过世了。现在这棵树是处在无人管理的状态。
它是一株橄榄树。如今的它投下了更为浓密的枝叶阴影。对,是一株成长得很茁壮的橄榄树,完全可以形容为“有着巨人的体态”。在那个让人悲伤的夏天,石川弘(Takihiko Shibusawa)先生建议我们这些曾经与中岛健三先生很要好的人,都应该在每年的7月1日聚到一起—— 并为之冠名为“卡兰树纪念日”。当这样的机会多少听起来有点类似于某些多愁善感的文学聚会的时候,就私下愿望里论,我其实是蛮希望这样的聚会能够办成并永远持续下去的。
(从石川弘先生的叙述里)可以发现一个错误:将卡兰树和橄榄树混淆在一起的提法早在19世纪中叶就开始了,兴许是随着《圣经》被从西方翻译为中文的时候产生的。今天我们一旦提及卡兰树,不断地让人眼前浮现出的景象,不外乎是阳光透过橄榄树浓密绿色树冠的缝隙投射下来的样子。
我听说橄榄树无法很好地在东京地区生长,如果这是真的,那么那株橄榄树就是一个奇迹喽!更让人吃惊的是,那株树还结出了异常丰盛的橄榄果实,我们中有许多人都尝过。一位诗人有一回将它们装入瓶中,并贴上标签,写着“罗斯·塞拉维 (Rose Selavy)”的字样(译者注: 这个单词来自艺术家杜尚的文字恶作剧,代表自己的一个分身)。
那么这些橄榄树究竟是如何到达日本的呢?怕是没法确切地知道了。但是我想到的一件事是,建筑师丰福(Toyofuku)曾一度居住于罗马,如果说是他将那儿的树种带了过来,也不是没有可能。
我向来着迷于地球上的植被分布,特别是树木。例如树木在澳大利亚是如何分布与扩散的,读这些东西往往得到很多乐趣。
我对树木最早的兴趣,萌发于得知这一事实:一些物种可以在某个相对受限的空间生长,可是一旦它们从那一区域中传播开去(其传播甚至会越过海洋)之后,能够演变出它的下属种类,或者进化成另外一种生存形式。那种新的生长规律,可能与它原来的生长规律迥然有别。
我感觉这段历史似乎与犹太人的疏散、分布有些相似,总而言之,文化“移植”(acculturation,或者翻译为互渗)这样的话题总可以吸引我。我意识到在所有的存在物中有一件东西,被诗人里尔克称作“Weltinnerraum”——内在的宇宙空间,也许,不只有树木这一件事使得我意识到这样的“内在空间”存在着。树木的个体是固定不动的,但是它安稳地用其枝干、树叶与树冠摆出了各种静态的“手势”,好似佛陀一样。

法国诗人蓬热(Francis Ponge)曾经写道:
那些属于树木的时间啊:它们看起来总是静止的,稳固的。你完全可以转过头去,无视他们好几天乃至一个礼拜,但它们不是依旧保持着那样不动的姿势吗? 除了成员成倍地增加之外。关于它们的身份(Identity),你弗需怀疑会发生任何变化,但它们在形式方面已变得愈加明晰(realized)而圆融。
在某些重要的维度上,树木能将时间转化为空间。它们发自于内部的成长年轮以几何上的精确度记录着一切,并一丝不苟地填充着那无尽的空间,所谓“发自于内部的成长”,我想它是朝着两个方向而展开的。一个是沿着根部的、向下的方向,另外一个则是沿着枝干和叶子的、向上的方向。对于大部分人来而言,枝干和叶子看起来是颇为平凡的,而树的根部则代表了某种基础性。其实,这两段生长是完整而不可分割的“行动”,当树木一眼望向那无尽和永恒(infinity and eternity),它上部的叶子创造出叶绿素,而根部吸纳着矿物质,所以说,树木无不可以越过上帝的意志与人的智慧而存活着。然而今天人类的自私或许正在毁了它们,这份喜悦的、树与人之间的密切关系大概只有屈指可数的日子了。不管它们曾经如何遮蔽过它生长着的那片土地,都完全不带着什么宣扬自己想法的意思,也不想创造出独属于它们自己的某种复杂形式。树依旧还是树,一种消极而被动的存在,不留什么余地给诡辩和谎言,但偏偏气量狭小的人类知识里,却往往会将这样的东西漏写。
在一次与罗斯托(Pierre Rosteau,居于巴黎的美术家)的谈话中,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 (Le Clezio)这样说:
树木极具魅力(charm)。它们始终站在同一位置,无有移动,也没有过多的自我中心(self-affirmation)意识。它们的生存经历了许久的岁月。与之相比,人类实在过度地以自我为中心。我们意识到,人类总在想着他们自己怎么样,例如那些琐碎庸常的问题,此时树木却从来不去打搅任何人的任何事,也不偷取其他的什么东西。于是就可以体会,之于我们而言,树木的存在其实是能够让人不断地愧疚与自省的,它们所采取的是一种近于完美的生活形式。

人们与树木之间曾经彼此交换着许多的愉悦。双向的愉悦确实存在过,可现在仅仅变成了单方面的了。今天的人去寻找树木,不过是为了去剥削它们身上的价值。里尔克、奥迪隆·雷东(Odilon Redon,法国象征主义画家)也好,艾默生和梭罗也好, 世阿弥元清(Zeami Motokiyo,日本演员及剧作家)与松尾芭蕉也好,许多这样的名字,就如同那许许多多伫立于大地上的树木一样,都很好地见证着在人与树木之间流动和传递着的愉悦。假如你上溯至某一个特定的时期,那么人与树木之间还可以找出许多亲密关系。例如,一株树是能在一个人的体内生长出来的(within a human),而画家和诗人等等,则又都可以在某些意义上生长于一株树木的体内。
而(里尔克的)诗歌是这样的:
一个空间均匀地覆盖了所有的生灵
那是 “内部世界空间”(inner-world -space)
鸟儿安静地飞翔着
穿过我们飞翔着。
噢,我是否想要栽培
那株我能在外部世界见到,却生长在我体内的树?
在里尔克的观察中,内部与外部的东西形成了一体。关于这种内在需求的饱实(或译为满足),眼下仿佛经常地濒于丢失。那可能缘于人类对自然的感觉往往是居高临下的,所以同时也就摧毁了生长于他们内在的树。
那么,现在的我们应当如何去保护那些树木呢,假如先不论它们是中岛先生的树,还是泷口修造先生的橄榄树……
人和树的存在,所为的,正是人和树的存在。人和树在一起——又是如何的一种转瞬即逝的时刻啊!我想,人与树在一起的时间,真的不能算太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