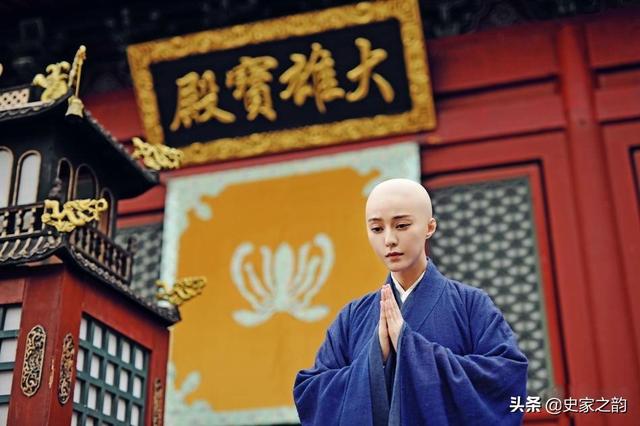《舴艋舟》——吴冠中
博学于文和变其音节
徐建融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力倡先贤所说的“行己有耻”和“博学于文”。“行己有耻”,是从价值观上反拨文人无行的“恬不知耻”,以重塑“天下为公”的士林正气;“博学于文”,则是从学术观上反拨文人游戏的“变其音节”,以重塑“实事求是”的学科规范。

《老重庆》——吴冠中
“博学于文”的意思,是说三百六十行,各行各业都应该恪守各自的规范、标准,“述而不作”,做好本职工作,无非是“术业有专攻”的意思。用闻一多的说法,就是按规范做事,“带着脚镣跳舞,并且要带着别人的脚镣”,“见贤思齐”地跳舞。三百六十行都恪守本法把本职的工作做好了,则天下为公的理想也就得以实现。它的典型,便是《孟子》中提到的孔子尝为委吏(仓库保管员),所关注的是如何做好出入的账目,又尝为乘田(畜牧饲养员),所关心的是如何让牛羊茁壮成长。反映在绘画艺术上,宋代的士人如李成、李公麟、文同、苏轼等也都参与其事。他们无不恪守绘画“存形”的“本法”,以形写神,形神兼备,物我交融,达到“有道(士人之所长)有艺(画工之所长)”。苏轼努力地去做,却做不到,画成了怪怪奇奇、脱离形似的模样,他自认为这是“不学之过”,“有道无艺,物虽形于心而不形于手”,而决不文过饰非,自居创新之功。他还力斥扬雄以赋家的身份转而著经,不过是“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其太玄、法言皆是类也”,“终身雕虫而独变其音节,便谓之经,可乎?”

《拉萨龙王潭》 —— 吴冠中
文人“变其音节”的学术观,便是不按规范做事,颠覆了规范做事,用甲事的规范来做乙事,无法而法,我用我法。最典型的反映便是文人画,后世奉为鼻祖的便是苏轼,而把苏轼自责的“过”当作了创新之功来加以发扬光大。苏轼“论画以形似,见于儿童邻”的鉴赏论,被篡改为“作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的创作论。于是,形神兼备作为再现的匠事,不过是与照相机争功;真功实能的“画之本法”被斥为低俗,不过是没有文化的技术。什么才是高雅的好画呢?“论形象之优美,画不如生活,论笔墨之精妙,生活决不如画”,根本在诗文、书法等“画外功夫”,尤其是书法,更被奉作绘画的基础和标准,“书法即是画法”、“画法即是书法”。术业在他攻,这就好比奥运会的长跑跑得快不过是与摩托车争功,而要想踢好足球的基础训练和评判标准应该以跳高为规范。

《宽容》 —— 吴冠中
文人画概念的提出,包括把唐宋的读书人如苏轼等全部称作文人,是董其昌之后的事。在宋元,绝无文人画一说,而是称作“士夫画”、“士人画”。宋代的士人,更明确表示:“一为文人,便不足观。”因为文人之才,有识者虽然怜爱,但其德行,则为世人欲杀。诚然,基于万物理相通的道理,“变其音节”的文人画,于教化大众的以“存形”为本法 的绘画之外,创新出了一种以文人所擅长的书法为功夫的自娱的绘画形式。诚如闻一多所说:“中国画与书法发生因缘,是较晚的一种畸形的发展”,“画拉拢字,使画脱离了画的常轨,而产生了我们这有独特作风的文人画”,“但是以绘画论,未免离题太远了!”进而以此否定原来的绘画形式,则虽然与书法相通,但毕竟与书法不同的绘画学科,其自身的规范便被颠覆;而既然书法可以颠覆“存形”而作为绘画的规范,则行为、装置、观念等等又何尝不可以颠覆书法而作为绘画的规范呢?就像扬雄创新出了一种新的“经”,怎么可以以此为标准来否定原来的经呢?文人做事,行为总是出格,离经叛道,标新立异,放纵不羁,又岂独画和经?其好处是创新,坏处则是败事。

《苦瓜家园》 —— 吴冠中
一旦当术业无专攻,什么都可以作为这个学科的规范、标准,唯独本学科的规范、标准不再被作为这个学科的规范、标准,这个学科本身也就被颠覆了。固然,近亲之殖,其蕃不衍,所以需要他山之石来攻玉,所谓“置身山所以识真面”。但逾越了基本规矩的跨学科创新,既未必能给交跨的两个学科带来福音,也未必能创造出一个新的学科。如科学界的狮虎兽或虎狮兽,便是典型的例证,所谓“深入虎穴方得虎子”。仍用闻一多的说法,“谁知道中国画的成功(包括一切变其音节的成功)不也便是它的失败呢?”它造就了“许多新花枪,同时也便是艺术型类的大混乱。”作为造型艺术的中国画,从此便成为综合艺术(诗、书、画、印)的中国画。毫无疑问,王楠的打乒乓,与刘翔的百米跨栏,道理是相通的,但如果用跨栏的规范来打乒乓,则既无助于乒乓成绩的提高,也无助于跨栏成绩的提高。至于它可能创新出一个综合竞技(乒乓、跨栏)的项目,又另当别论,但无论如何,用这个综合竞技项目取代乒乓,说只有它才是真正的乒乓,原来的乒乓不过是“工匠之技”,显然是说不通的。

《酱园》——吴冠中
术业专攻的画家画,吴道子、莫高窟等工匠不工诗文,不精书法,有些还是文盲,他们固然不可能把诗、书搬到“存形”的画面上。就是李成、李公麟等士人,工诗文,精书法,事实上他们也没有把诗、书搬到“存形”的画面上。所以,诗文和书法,是真正的“画外功夫”。而术业他攻的文人画,那些以诗文、书法为擅长的文人,则纷纷把诗、书搬到了“不求形似”的画面上,所谓的“画外功夫”,实际上成了“画上功夫”。喻之以高考,前者好比普招,以高考成绩的优劣为评判标准;后者好比特招,并不以高考成绩的优劣为评判标准,而是以高考成绩之外的特长、偏才为评判标准——但它很容易演变为以高考成绩的低劣为评判标准,反以高考成绩优异为“工匠之事”,于是而沦于“荒谬绝伦”(傅抱石语)。

《嘉陵江边》——吴冠中
我们今天强调创新,古人亦然。什么是创新呢?文人“我用我法”、“标新立异”、“变其音节”的术业他攻固然是创新,士人“见贤思齐”、“述而不作”、“博学于文”的术业专攻同样也是创新。一者好比奥运会的竞技,遵守某一项目的规范参与这一项目,努力创造更快、更高、更强的新成绩,打破了前人的纪录是创新,打不破前人的纪录也是创新。一者好比吉尼斯的竞技,别人走过的路我不走,想出一个自己的项目参与没有对手的竞技,努力创造新、奇、特、绝的项目,长头发、肥皂泡等等。从想法上,创新一个新的项目难;从功力上,创新一个新的成绩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