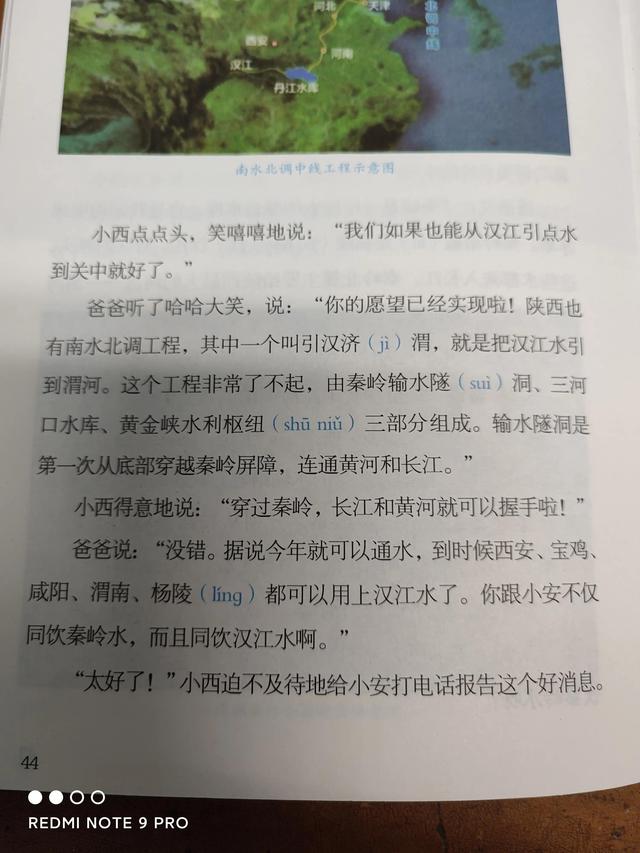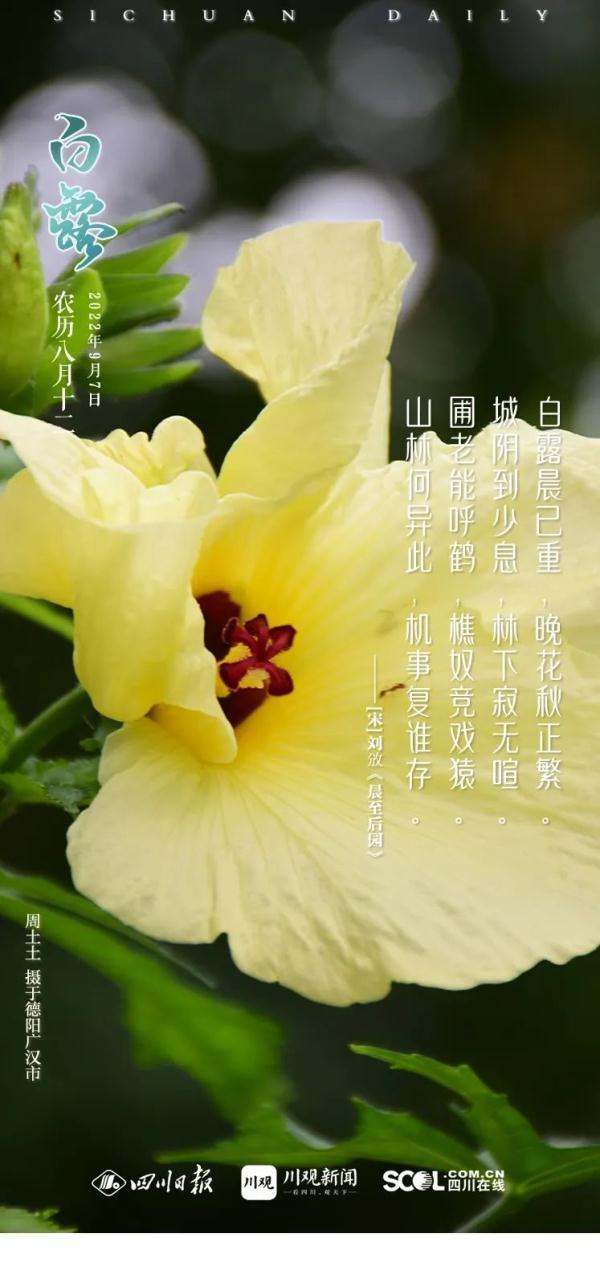四五十年前的成都,市区范围大致在锦江、府河以内。作为四川的省会和经济中心、以及西南的文化中心,成都不仅文化底蕴浓郁,而且商业也非常繁荣,除了人头攒动的各大商场外,每天还有各类商贩游走在大街小巷。

各种叫卖声、吆喝声此起彼伏,加上百姓居家过日子的声音,构成了一曲颇具地方色彩的都市市井交响曲。现在回忆起来还很有意思。
每天清晨,当雄鸡的啼叫划破了川西平原的浓雾,宣告新的一天到来的时候,大街上小巷里就会响起一声男性十足的吼声:“倒桶子!”——那时的成都平房居多且无厕所,有厕所的院子也非常少。马桶,成都人叫“桶子”,就成了大多数人家的必备之物。
收集粪便的人拉起装着大粪桶的架子车,天刚麻麻亮就会来到每一条街上,随着这一声吼,各家各户就要完成这每天第一件必做的事情。倒马桶、涮马桶的声音就成了这部交响曲中的序曲。收集起来的粪便不仅没有成为令现在人头疼的污染物,还成了农村里上好的绿色肥料。
稍后,就该是吃早饭的时候了。
“买豆浆,甜豆浆,豆浆热的!”一两分钱可以买一大碗,卖豆浆的一般还兼卖油条油糕,“买糖油果子!买油条!买发糕!”、 “蒸蒸糕!”,豆浆油条、馒头稀饭成为早餐的最常见组合。其间还夹杂着卖牛奶的声音——但那是奢侈品,一般人是吃不起的。冬天还有热气腾腾的牛羊肉汤,两毛钱可以买一大碗,你要多少汤都行,回家后用昨天的剩饭煮成汤饭,加上每家都有的泡菜简直不摆了。
各种早点的叫卖声构成了交响曲的第一乐章。
八点以后,上学上班的人都走了,街上、院子里逐渐安静下来。少顷,又逐渐响起市井交响曲的第二乐章。
“买小白菜!”“买白菜秧儿!”“买青头儿萝卜!”这带了儿化音的成都话叫卖声非常好听,那是挑着担子、拉着小架子车的农民们把自己自产自销的农副产品送进城里来卖。留守在家的大爷太婆们就开始和卖菜的人讨价还价。上午叫卖菜的内容由于季节的不同而经常变化。
除了叫卖蔬菜的声音外,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声音夹杂其中。

“倒渣滓!”、“倒炭灰!”成都话把垃圾叫做“渣滓”,每家每户烧的蜂窝煤会产生许多碳渣。每天上午专门有人拉着架子车摇着铃铛来收集垃圾和碳渣,这两样东西还要分别收集,不能混在一起。人们也很自觉,渣滓和碳渣都分开装在烂得不能再补了的烂脸盆、撮箕里,听到铃声就端出去倒掉。
“买晒衣杆!”川西平原上农家小院四周都种有竹子,笔直细长的竹竿是每家每户必不可少的晾晒衣物之物。尤其是星期天,在院子里,凉衣杆朝两边房子上一搭,各种衣物被单就成了大院里的一道风景线。平时,上班一族趁天气好把衣物被子拿出来晾晒,只要临走时交代一声:“赵婆婆,我的东西晾起的,如果下雨请帮我收一下哈!”“要得,你放心上班嘛,保证不会出问题!”邻里之间特别和谐温馨。
“买青果!退热解渴的青果!”“买荷叶,一分钱一张!”盛夏酷暑的时候,这是最受欢迎的东西。
“捡亮瓦捡漏瓦!”老成都街道两旁多瓦房,屋瓦中还夹杂着几块玻璃,为的是增加屋子的采光。因为风吹雨打,或是猫儿在房上踩踏造成损坏,屋瓦是需要经常检修的,于是就有了这样一个专门检修屋瓦的行当。捡瓦人肩扛长梯,除此之外不需要其他任何工具,在小街小巷里穿行。如遇到哪家瓦坏屋漏,一声招呼,就支起梯子麻利地爬上房顶检修烂瓦。有时候也有顽皮的小孩跟在匠人后面捣乱:“捡亮瓦捡漏瓦,不捡不漏捡了包漏!”然后一溜烟地跑了。
“补锑锅补铁锅!”“补洋磁盆盆!”“补碗!”补锅匠人担一挑子,手拿一串铁片,一边走一边甩动铁片发出清脆的声音,一边还要吆喝。瓷碗摔破了居然还要补好再用,现在的人恐怕怎么也想不到吧。
“买蜂窝煤楱楱!”、“买桐油石灰!”、“买灯草!”——那时居家多用木桶木盆,不像现在几乎都是塑料用具甚至不锈钢,木盆木桶用久了会漏水,而桐油石灰就是专门补木盆木桶的。灯草,据说煮牛奶时放一些可以为婴儿起到清热的作用。
“补凉席!”夏天使用的凉席坏了也有专门修补的篾匠上门服务。
“弹棉睡!”成都话管棉絮叫“棉睡”。棉絮用久了就会板结,保暖作用降低,需要重新疏弹使之松软。于是就有用最原始的办法来疏弹棉絮的手工业者,背一张巨弓,手拿一木锤。如遇雇主,则就地摆开家什作业。于是,或院子里,或街头、或巷尾就会响起有节奏的弹棉花“嘭嘭嘭”的声音。
“磨剪刀起菜刀!”一串铁片在磨刀人手中有节奏地敲打,肩扛一条绑了厚厚磨刀石的凳子,这吆喝声也具有成都味道。北方干这行的吆喝是这样的:“磨剪子来镪菜刀……”像《红灯记》里磨刀师傅吆喝的那样。

“收废品!收烂布巾巾,有烂棉花烂罩子(成都话管蚊帐为罩子)拿来卖!”“有废铜烂铁拿来卖,有烂铁锅烂锑锅拿来卖!”现在谁还收烂布巾巾烂棉花呢?收废品的已经进化到收彩电收冰箱收电脑了,而且还用电喇叭招揽生意,都懒得吆喝了。
下午,响起了老成都市井交响曲的第三乐章。
“买冰糕,买果汁冰糕四分儿,牛奶冰糕五分儿!”小贩把一个方形的保温木箱挎在身上,一边走一边叫卖,他们把凉爽带给市民,而自己却累得满头大汗。后来发展到用自行车搭着冰糕箱沿街叫卖,再后来这种行当就消失了,因为电冰箱几乎成为家家户户都有的电器,冰糕也几乎被各种美味的雪糕取代。
“叫咕咕、南瓜花!”翠绿色的昆虫蝈蝈也能成为孩子们的玩物。卖者扛一根长长的竹竿,上面挂满了用麦秆编成的装蝈蝈的小笼,这些小笼各式各样,方形圆形六角形宝塔形飞机形……简直就是一个精巧的手工艺品。
成都的市井交响曲中居然还有打击乐。
“叮朵叮朵叮叮朵……”这是买麻糖的小贩用一个薄铁片和一把小锤敲出的极富音乐感的声音。小孩子一听到这清脆的敲击声就会缠着妈妈:我要吃白麻汤——麻糖被成都人叫做“麻汤”。卖麻糖的小贩用手中的铁片做刀,用小锤轻轻一敲,一块麻糖就被敲下来了。
那东西怪得很,单用手是无论如何也弄不下一块来的。成都人有一句俗话:“冰糖服烧,麻糖服敲”——大块的冰糖放在火上烧一烧就很容易弄碎,大块的麻糖轻轻一敲就会乖乖地变成小块。
老成都交响曲中还有一个极富地方特色的音响:打锅盔。锅盔,一种小小的面饼,成都人把它做绝了:锅盔做成两层,中间夹凉拌菜或卤肉。面饼在北方是烤或烧的,制作过程是没有声音的。
而成都制作锅盔却有音响,恰似交响曲中的打击乐。
小铺临街支一个炉子,上面放一个圆形带木把的平锅,叫做鏊子。锅盔师傅分好八个小面团,每分一个面团时,右手大拇指按在中间使空气进去,面团做好后,右手握擀面杖在案板上敲出有节奏的哒哒声,左手同时揉面团,很快面团就成了圆形,左手腕一翻,“叭”的一声,面团扣在案板上,擀面杖同时在案板上击打出一个重音,然后在面团上擀三两下,左手飞快地转动面团。很快,一个几何学上都无法挑剔的圆锅盔就成了。
锅盔店擀面杖清脆的“哒哒”声以及面团扣在案板上的“叭叭”声,不知勾起了人们的多少食欲。
异曲同工的还有糖油果子三大炮。

居然还有骟鸡的。虽然从乡下住进了城里,但是,一些婆婆大娘养鸡的习惯却没有改变,那时的人们碗中缺少油水,为了使公鸡长得肥一些,就将其骟掉。于是,就产生了专门骟鸡的行当。
骟鸡者一般不吆喝——大概觉得太难听了,只是手拿一面巴掌大的小锣,不时地敲一下,声音短促沉闷,只要听到“咚”的一声锣响,就知道骟鸡的来了,于是,婆婆大娘们养的公鸡就失去了做公鸡的权利。
四五点钟左右,《成都晚报》出版了。街头又增加了叫卖报纸的声音:“买晚报成都晚报!”有的报贩还将当天报纸上的重要内容吆喝出来:“看我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看美国昨天开始轰炸越南北方,我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看今天晚上周企何在锦江剧场演出拿手川剧!”“看四川电影院单机连放,上映惊险反特故事片《羊城暗哨》!”“看人民电影院放映彩色宽银幕电影《魔术师的奇遇》!”

成都的老茶馆还有各种曲艺以及川剧表演,这时也开始登场。比较著名的有“悦来茶馆”、“三怡宫”和鼓楼北一街的“芙蓉亭茶铺”。伴随着“买纸烟!”“买瓜子花生!”及掺茶倒水混响的,就是竹琴、金钱板、四川清音、四川评书和川剧折子戏的悦耳声声。说书人的惊堂木、阵阵丝竹管弦、川剧的帮腔不时透过茶馆的窗户门面传到街上。
傍晚,另一个很有韵味的声音又响起了:“蚊烟儿哟蚊烟儿,买二仙牌香料哟蚊烟儿……”,成都方言中,“药”被说成“哟”,薰蚊子的药蚊烟——盘蚊香的祖先,在方言里成了“哟蚊烟”。卖蚊烟的手挎一长篮,篮内整齐地放着长条形的“蚊烟”,一边走一边唱。那是有音乐的,记成简谱是这样的:“13261—32316—216516——”,你说好不好听?
药蚊烟儿用锯末和六六六粉拌成,燃烧后的烟非常呛人。当家家户户都点起“蚊烟儿”关好门窗熏蚊子的时候,街面巷口就成了非常热闹的地方。大人们三三两两围坐在一起,手摇大蒲扇,天南海北地摆龙门阵......
女孩子们则静静地坐在旁边听着,听外婆奶奶唱一些莫名其妙的儿歌,如“月亮月亮光光,芝麻芝麻烧香,烧死麻大姐气死幺姑娘……”,“月亮走我也走,我给月亮打烧酒……”或者和姐妹们咬着耳朵说悄悄话。
这时,院子里,大街上,小巷深处就成了男孩子们的天下,捉迷藏是他们的拿手好戏,不时响起冲啊杀啊的喊声。

大约九、十点钟,“蚊烟儿”熏完了,父母亲呼唤孩子们的声音又此起彼伏地响起:“三娃子,快回来洗澡睡觉了!明天还要上学得嘛!”、“钱大毛,还不回来嗦?想吃笋子熬肉了哇?!”接着就是小鸟们归巢的声音:“明天再来哈!”“要得!”
“还有莫得人没有回来?关大门了哈!” 各家各院落随即响起关大门、上门栓的声音。
老成都的市井交响曲在奏完了最后一个音符后结束,喧闹了一天的街巷终于渐渐安静了。月光如水银般洒满大地,星星眨着眼睛,像卫兵似的守护着这座充满了诗情画意韵味无穷的城市。
作者简介:杨全,1954年生,1971年赴云南支边,1978年考入云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学习,1982年分配回成都,在中学任教至退休家住双眼井附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