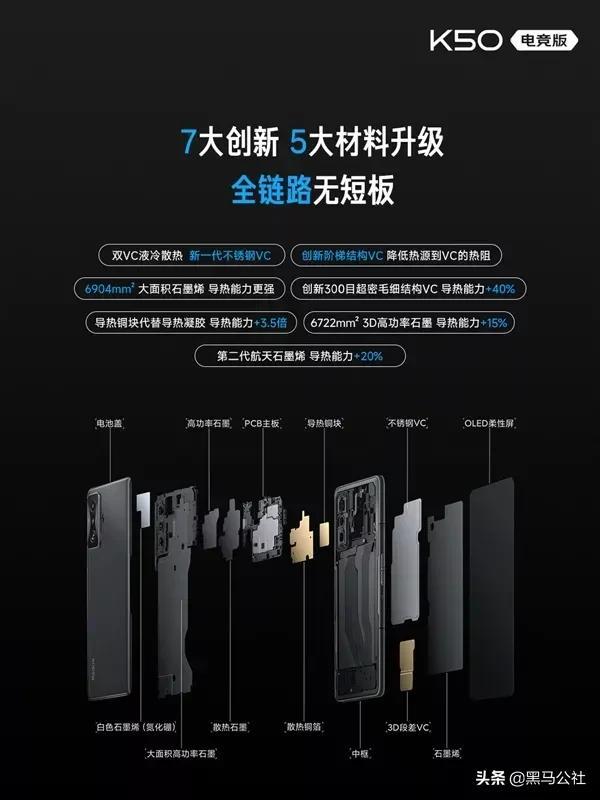“继往圣将微之绪,启前贤未发之机,辨诸儒之得失,辟异端之论谬,明天理、正人心,事业之大,又孰有加于此者。”——《行状》
“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孔子

我们前面讲到,佛家进入以后,倒逼着儒家又有新动向了,因为佛家实在是太精彩了,于是儒家就要思考一系列的问题,必须要进行自我改造了,所以,产生了新儒家。
新儒学的天理与良知观新儒家看到了佛教有一系列很严密的体系,儒家就需要提供一些自己所有思维的宏观精神依据了。他们就要挖掘天理,挖掘心性,后来由这个又挖掘到良知。本来呢,正宗的儒家,像孔子、孟子,他们也讲了很多我们必须遵守的美德,我们必须遵守的那些规矩。但是请问,为什么要遵守这些美德?为什么要遵守这些规矩?根本理由是什么?儒家学者好像历来不太在意,就是对于根本理由他们不太在意的。
你如果问孔子、孟子,为什么要遵守那么多美德?为什么要遵守这么多规矩?他们的回答往往是,先王就是这么做的,尧舜禹是这么做的,或者说得更彻底一点,就是人们需要,国计民生需要。为什么这样?他们不太说,他们只能说应该怎么样,他们不太问为什么要这么样。
这种学术态度本来是可以的,但是到佛教出来以后,这样学术态度就显得浅了,就显得单薄了。你只说应该怎么样,却不说为什么要这样,大家有没有感到儒家确实有这个毛病?老在说什么规矩,老在说什么是美德,老在说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很少说为什么要这样。

而反观佛教,我前面讲过,它把宇宙解释成世界,解释成是各种各样偶然关系的偶然组合,所以一切是空的,当空的时候呢,它慢慢地就来看到我们的苦难,其实也是我们营造出来的, 也是空的,它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了。
儒家从来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儒家学者慢慢慢慢地,终于从佛教学习种找到了根本原因,找到宏大的哲学理念的这么一条路子上来了,他们走到这条路子来了。他们找来找去,找到了两个非常棒的概念,一个叫“天理”,一个叫“良知”。他们想从“天理”和“良知”上来寻找社会上的一切规范和一切美德的理由。
大家想想看,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只要是中国人,我们面对实在看不下去的最极端性的事件,我们是不是会疾呼“天理何在?良知何在?”可见,天理、良知是人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在口语上也是最后界限。
我们新儒家,就在这两条最终的界限里边去寻找儒家规范的基点。这样的话,就出现了新儒家的两条路,一个是理学,一个是心学。天理,由理学来研究;良知,由心学来研究。
我们现在先讲理学,就是新儒家的理学,他们是研究天理的。我先讲了理学,再慢慢地讲心学。心学上次已经讲过了,但是我们这次呢,在儒家学术接受了佛家的冲击和启发以后所产生的新形态,要比较完整地把这个新形态讲述一下。
朱熹:理学的集大成者理学在哲学史上往往被称为“程朱理学”,“程”是程氏两兄弟,而“朱”指的是朱熹,他是主要集大成者,也是我们非常优秀的哲学家。

就像佛教一样,朱熹要从天地宇宙的根本上去讲我们行为的基点了,他说“宇宙之间,一理而已”,用理来决定天下万物的由来和规范。天下万物的由来,按照他的说法,叫“所以然”;天下万物的规范,按照他的说法,是“所当然”。
世界就是由一个理,宇宙之间一个理,所组成的。理,有一部分是必然出来了,有一部分是我们要设计出来的,这两个是我们要在世界上、在社会上,实现我们天理的基本途径。
我认为,程朱理学是中国思想家从理性主义的高度,来探究天地万物的终极原理,表现出了宏观的抽象的思维能力。这在中国,平心而论,出现的比较少,时间也比较晚,但是出现了还是让我们很钦佩。
在六百多年以后,德国古典主义哲学家康德,提出过理性法则,黑格尔提出过绝对理念,其实他们和中国程朱理学哲学家的哲学企图是很靠近的。尽管康德、黑格尔对中国哲学相当陌生,他们完全不知道六百年前,有一批东方哲学家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精神高度,而他们在六百年以后还在攀越。
朱熹认为,“理”是宇宙的本体,是唯一的太极,天地万物就由此分出来的。正是在这个关口上,他触及到了所有思想家都很难回避,但又不得不讨论的善恶问题。孟子说“性本善”,荀子说“性本恶”,但是却一直没有深入的论证。朱熹认为,孟子说“性本善”,是“不备”,也就是说不完备的;荀子说“性本恶”,不明,也就是说不明确。在不完备、不明确的时候,执着于一端,朱熹觉得,根源的问题上还要理清脉络。

朱熹认为“理”是善的,是至善的。但是,当“理”要在世界上实现的时候,它必须要化作“气”,这个“气”就有清、浊、阴、阳之分了。清生善,浊生恶,所以,人类也就有了善恶。大家听明白没有,朱熹说,理是至善的,理要在世界上体现的时候,它就要碰到气,和气组合在一起。但气呢,有清气、浊气,有阴气、阳气,这里边就有善恶之分了。
朱熹说,由于天理是至善的,所以人的先天的本性也是至善的。朱熹把这种先天的本性说成是“天命”,把后天养成的特性,叫做“气质”。他认为天命和气质常常矛盾,所以,一个人应该好好地认识自己的天命,慢慢地改善自己的气质,要改善气质,其中有一个就是要放弃人的很多欲望,放弃人欲,来服从天理,而且要知而后行,你知道了就要慢慢地做。
朱熹认为,你只有领悟了天理,才能领受自己的天命。但是,要领悟天理很难,所以就要经过格物。什么叫格物?就是集中心性,对各个具体的事物的纯粹状态进行省察。你把你的心智集中起来,对各种事物的存在状态进行思考,进行观察,这样就可以由个别到达普遍,由事物到达天理。
这个过程非常难,因为人心并不能够集中起来面对客观的事物;所以,他提出人心要进入一种主敬、涵养的修行过程。什么叫主敬、涵养呢?要敬畏,要收敛,要谨慎,要深思,要专一,要严肃。在这些词汇当中,敬,这一个普普通通的汉字,在朱熹那儿,就成了人们皈依天理、服从天命的主要途径。在朱熹看来,有了敬,天下人心就能够深入天理、天命,和谐安定。
大家大体上能够明白朱熹的思维吗?他认为,整个天地宇宙就是一个“理”来统治的;但是到人间呢,就要变成天命,每个人都应该服从。人要认识天理和天命很难,所以只能格物致知,只能就具体的事务,集中精力去想它、想它、再想它,想到后来,慢慢地就由个别到一般,认识天理了。

这个过程很难完全能够实现,原因是人心太浮。所以,他要求大家的人心,首先要保持敬畏的态度,对天理敬畏,对天命敬畏,敬,就是让天理和天命慢慢地渗入到我们心中。所以,在朱熹那儿,敬字,非常重要。
朱熹形象的变化:成为官方哲学的儒家通病朱熹所说的这么一个宏大的思维结构,如果进入到我们社会里边,这个天理和天命,就变成了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譬如父子关系,譬如兄弟关系,譬如族亲的关系,延伸下去呢,又扩大到了君臣关系。平心而论,你讲父子关系、兄弟关系、族亲关系的时候,你讲天理、天命那还说得通。但是,如果一直推理到用父子关系、兄弟关系、族亲关系,推理到君臣关系,而且把君臣关系推到天理和天命的高度,这就问题就大了,这就让朱熹的形象变了。
本来,朱熹想用天理来表述一种稳定的秩序,相反相成、百脉呼应的一种社会理想,但是,却把封建社会的君权专制合理化了。这种强取豪夺的制度变成了一种天然现象,变成了天理、天命了,这就不对了。
他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这个“四书”做了大量的诠释,诠释以后,他以天理、天命来维持社会秩序的这么一个构想,后来慢慢地被他后世的统治集团所重视,就渐渐地成了一种国家哲学,他对“四书”的注释甚至成了全国科举考试的一种标准。

朱熹他本人,当时去世的时候,日子还非常的不好,当时被说成是“伪学”。他的地位是在他死后慢慢地被统治者重视的,因为他把当时的社会的这种专制集权的构建,变成了一种天理和天命,这样的话,统治者一定是很高兴了,老百姓如果学的话也会跟着服从。有很多的后来的思想家为了求得自由,就一定要把朱熹的理学推翻,有这样一个背景。
如果撇开这一部分,我个人认为,朱熹试图用天理的理念来探究宇宙和人世的终极道理,这一点还非常值得我敬仰。而且,他知识实在是渊博,他的气魄非常宏大,他在讨论社会结构的时候,那宏大的理论,陷落在一个为专制制度辩护的泥坑里边,这是历代儒家的通病。
这样的话,我们对理学的功和过都做了简单的解释;而且理学为什么在当时会产生,由于佛教的冲击,产生的充分的合理性,我也做了说明。他后来产生了某一种理论陷落,那是儒家的通病,我们也应该历史的看问题,予以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