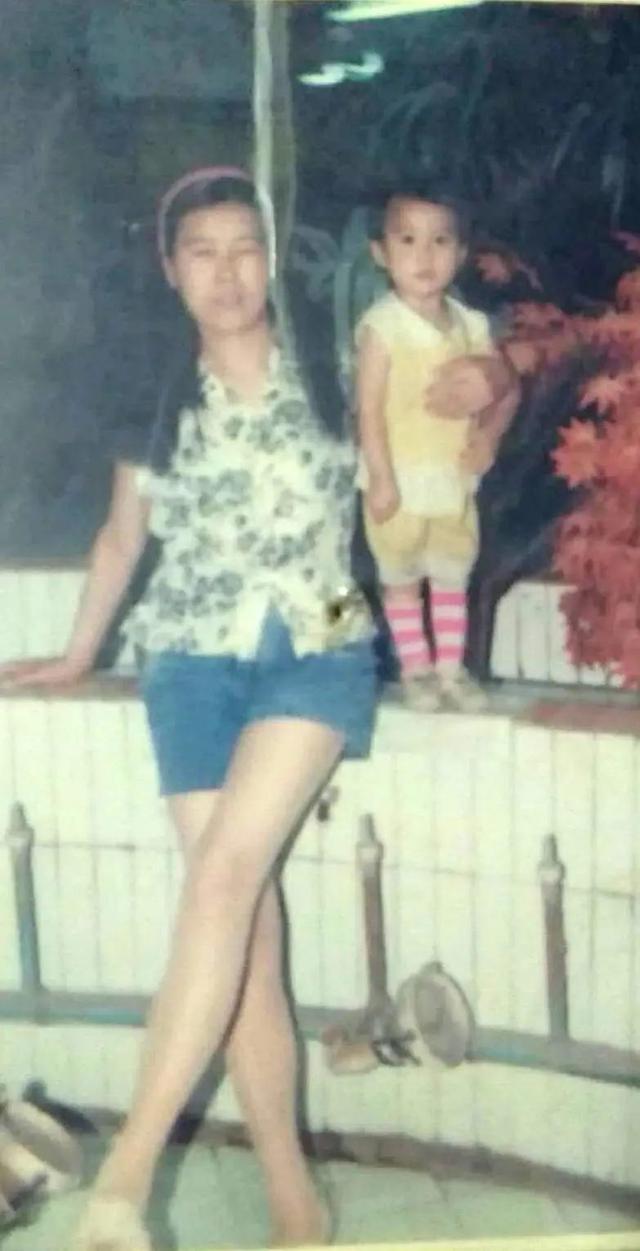摘 要
公、侯、伯、子、男历来被认为是周代实行的五等爵制中的五种爵称,但实际上在西周金文材料中,公侯伯子男的用法十分复杂,并不单指称谓。公主要用于尊称,侯在西周金文中最常用于封国君主的称谓,伯的基本含义是代表宗族长子的地位,子的用法多与儿子、后代的意思相关,此外还表示贵族称谓。除了这些常见用法,还有用作地名、人名和泛称等其他含义,总体上看,公侯伯子男作称谓讲时,不属于同一个体系。
目 录
摘 要 I
绪 论 1
一、西周金文中“公”的具体用法辨析 3
(一)用作王官中位高年长者的尊号 3
(二)部分诸侯的死称 3
(三)贵族对去世祖考的尊称 3
(四)大保(太保)、大史(太史)的尊称 4
(五)封国之君、蛮夷之地君长称公 4
(六)泛指公卿侯伯一类的贵族 4
(七)用于表尊敬之意的辅助词 4
(八)表示女性的身份地位 5
这段话不但言明周代五等爵级包括公侯伯子男,并说明了不同等级封国的疆域大小。《礼记·王制》则载:“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也认为公侯伯子男是周代的五等爵称。
《左传》襄公十五年云:“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卫、大夫各居其列。”此记载认为公侯伯子男是周代列位等级的组成部分。《国语·周语中》记载周襄王言论时谈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规方千里以为甸服……其余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宁宇。”《逸周书·职方氏》说:“凡国,公、侯、伯、子、男,以周知天下。凡邦国大小相维,王设其牧,制其职各以其所能,制其贡各以其所有。”这两则记载基本都认为公侯伯子男是周代五等封国。
因年代久远,相关传世文献稀少,对五等爵存在的真实性及其具体内涵,学者难以言明。随着西周青铜器的不断出土,大量带有公侯伯子男等记载的铭文材料逐渐为世人所知。这对于学者厘清公侯伯子男的具体含义,探究西周是否实行过五等爵制,意义十分重大。
根据金文材料,对周代实行五等爵制持否定意见的早期有傅斯年、郭沫若等人。傅斯年在《论所谓五等爵》中率先指出,五等爵说与《尚书》、《诗经》等传世文献不合,与金文亦有出入,“以常理推之亦不可通”。他提出公与君同,侯近于汉代持节、伯为长等观点,初步对公侯伯子男的历史含义进行了辨析。郭沫若作《周代彝名中无五服五等之制》和《金文所无考》,论述了五等爵制不可信,周代爵名不固定,“公”、“侯”、“伯”、“子”无定称的观点。杨树达的《古爵名无定称说》赞成郭沫若的观点,并搜集金文资料中“爵名兼称”现象作补充说明。以上学者对五等爵制的真实性持否定看法,利用金文材料,质疑传世文献、挑战传统观念。但同时也导致他们在搜集材料时带有一定倾向性,不利于看清此问题的全貌。20世纪80年代后,出土铭文材料日渐丰富,大型青铜器铭文著录书的出版也为研究提供了便利。学者们对五等爵制的研究也再次活跃起来。在这一时期,赵伯雄在其专著《周代国家形态研究》中论述五等爵制时,提出公侯伯不是一个等级序列的称号,公伯最多只是诸侯的“类称”,侯是天子所封邦君的称号,本身没有等级的意义。盛冬铃在《西周铜器铭文中的人名及其对断代的意义》一文中探讨五等爵的相关内容时提出,“邦国之君的爵称不是固定不变的”,其中侯和部分称伯、称子的情况属于爵称,公、君是尊称,证明男、田为爵称的材料不足。二人也否认周代实行五等爵制。

根据金文材料或者依据传世文献,认为西周时期确实实行过五等爵制的主要有王世民和陈恩林。王世民在《西周春秋金文中的诸侯爵称》中区分“生称”和“死称”,指出“公”为天子重臣或死后追赠谥号,“侯”为诸侯爵名,“伯”为畿内封君生称,“子”为贵族男子美称,“男”为爵名。陈恩林在《先秦两汉文献中所见周代诸侯五等爵》一文中肯定了王世民的意见,并引大量文献论述了周代诸侯存在公侯伯子男这一序列,并且“公”地位最贵。近年来,,王世民利用新发现的金文资料,作《西周春秋金文所见诸侯爵称的再检讨》,在维持原说的基础上,补充论述了原来观点,认为公、侯、伯为具有一定使用规律的爵称。
具体探究金文中公侯伯子男的用法,总结其使用规律的有李峰、魏芃、刘源等人。李峰在《论“五等爵”称的起源》中,根据青铜器出土地点,认为侯是政治秩序中的一环,是东方各国根据自己在西周国家中的政治地位,对自己身份的表述;伯是社会秩序的一种,是王畿地区的贵族根据宗族血缘关系和排行,对自己身份的称呼。而公的身份从属于西周中央政府的官僚秩序,是最高执政官的称呼;子则为周人对异邦国君的称谓。李峰根据铭文出土地区来归纳侯伯含义的视角非常独到,十分具有启发意义。魏芃在其博士论文《西周春秋时期“五等爵称”研究》中,利用金文材料,结合传世文献,归纳了公侯伯子男的用法及其内涵发展演变的轨迹,总结为:公是尊称和职务之称;侯既是诸侯泛称,又是其中一种;伯本义为长,即兄弟之长,引申后包括宗氏之长和国君;子包含儿子、宗子和国君等义;男为诸侯体系中最低的一级。刘源在《“五等爵”制与殷周贵族政治体系》中,分析了从殷商到春秋时期公侯伯子男的具体内涵及其演变,提出西周时期外服诸侯的真实体系为:侯、甸、男、卫、邦伯。

上述学者在论证相关问题时,大多都较好地结合了金文材料与传世文献,论据较为充分。但学者们对此问题的探讨多从宏观入手,对金文中公侯伯子男用法的划分也多为大类,一些细节问题的讨论还不充分或有所忽略。笔者将《殷周金文集成》、《近出殷周金文集录》和《近出殷周金文集录二编》中收录的一万多件青铜器铭文拓片中,摘录出西周时期有关公侯伯子男记录的所有材料,并进行分类。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搜集更多证据或反证,对前人成果,进行补充论述或提出异议。除了历来学者们关注的称谓问题,笔者还注意到公侯伯子用作地名、人名和泛称、活用等其他用法,进行了总结并加以例证。
一、西周金文中“公”的具体用法辨析
西周青铜器铭文中提到公的材料十分多,用法也很复杂。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用作王官中位高年长者的尊号
西周金文中出现有周公、召公、毕公、益公、明公、毛公、武公、濂公、穆公、井公、同公等。刘源认为:“西周的公,总体上看是一种对长者和位高者的尊号,而非爵称。公多用作王室最高执政大臣的称号。”称“某公”者是否都为最高执政大臣,难以定论。但据魏芃统计,载有某公的青铜器资料,公与器主的关系以上下级居多,公常以赏赐者或上司的身份出现,属于地位较高的一方;而器主多是被赏赐者或者下级,地位较公为低。“部分不能确定‘公’与器主之等级差异的铭文,也基本可以确定二者的身份都相当高。” 这些公在周王室中央主理朝政、总领王室众臣和四方诸侯,位高权重。这些可从西周金文记载中找到例证。明公簋(《集成》4029,成王)铭载:“唯王令明公遣三族伐东国。”毛公鼎(《集成》2841,西周晚期)铭载有:“王曰:‘父,今余唯肇经先王命。命女(汝)乂我邦我家内外,憃于小大政……’”由此可见,公不仅可以统兵征伐,甚至有处理大小政务的权力,职权之盛可见一斑。

(二)部分诸侯的死称
鲁侯熙鬲(《集成》648,西周早期)铭文载:“鲁侯熙作彝,用享䵼厥文考鲁公。”铭文中,“鲁侯熙”是时任鲁侯,为生称;“鲁公”指上代鲁侯,为死称。类似的记载还有滕侯簋(《集成》3670,成王)铭文:“滕侯作滕公宝尊彝。”滕公是指上代滕侯。吾作为滕公鬲(《集成》565,西周早期)铭文“吾作滕公宝尊彝”中的滕公也应为前代滕侯的死称。但笔者发现,诸侯死称公并非通例,应侯见工簋(《近出二编》430、431,西周中期)铭中,应侯见工在称前代应侯时,便称“皇考武侯”,而不是称“皇考应公”。另有应公簋(《集成》3477,西周早期)、应公尊(《集成》5841,西周中期)铭文中的应公也为生称。据此,笔者认为,诸侯死称若称公,形式为“国号加公”;若不称公,形式则为“谥号加侯”。
(三)贵族对去世祖考的尊称
刘源对此有总结,“一类是日名加公”,“一类是氏名加公”。西周铭文中,这两类用法甚多。日名加公如
方鼎(《集成》2824,西周中期)铭文中提到的甲公,此鼎(《集成》2821,西周晚期)铭文中的癸公,
钟(《集成》246,西周中期)铭文“追孝于高祖辛公、文祖乙公、皇考丁公”中的辛公、乙公、丁公等。但日名加公也不全是死称,西周中期的乙公鼎(《集成》2376)铭载“乙公作尊贞(鼎),子子孙孙永宝”,此铭中的乙公应为生称,不属此类。氏名加公,典型的有南公,如南宫乎钟(《集成》181,宣王)铭“先祖南公”、大盂鼎(《集成》2837,西周早期)铭“用作祖南公宝鼎”。根据西周铭文记载,属于此种用法的还有两类情况。一类属于“美称加公”,即在公前加上美好的、赞誉性的形容词。如师趛鬲(《集成》745,西周中期)和师趛鼎(《集成》2713,西周中期)铭文载“师趛作文考圣公、文母圣姬尊䢅”,师趛称其先父为圣公。还有一类用法为“公加日名”或“公加行辈”,如壶(《集成》9690,西周中期)铭文提到的公乙、公己,乙、己为日名;恒簋盖(《集成》4199,西周中期)铭文“用作文考公叔宝簋”中的文考公叔,叔即表示行辈。在何尊(《集成》6014,成王)铭文中,提到了“尔考公氏”,公氏也表示对去世父亲的尊称。
(四)大保(太保)、大史(太史)的尊称
“公加官职”,表示该职地位尊贵。西周早期的旅鼎(《集成》2728)铭文载:“隹公大保来伐叛夷年,才(在)十又一月庚申。”御正良爵(《集成》9103,西周早期)铭文载有“隹四月既望丁亥,公大保赏御正良贝”。两铭皆提到了“公大保”。作册䰧卣铭文:“隹公大史见服于宗周年,才二月既望乙亥,公大史咸见服于辟王,辨于多正。越四月既生霸庚午,王遣公大史。公大史在丰,赏作册䰧马。扬公休,用作日己旅尊彝。”铭文中不仅多次提到“公大史”,更用“公”代指大史本人。由番生簋(《集成》4326,西周晚期)和毛公鼎(《集成》2841,西周晚期)铭文可知,西周王官存在卿事寮和太史寮两个官僚系统,协助西周天子处理政务。大史为太史寮的官长,杨宽认为大保在周初为卿事寮的官长。总之,大保和大史,地位尊崇、身份显赫。尤其是大保,更是辅弼周王、统理政务的最高执政官。“西周初期的中央政权,十分明显,是以太保和太师作为首脑的。太保和太师掌握着朝廷的军政大权,并成为年少国君的监护者。”除了公大保、公大史外,西周金文中未见其他官职前加公的记录。职官前加公,是大保、大史两个官职特有的用法,足见二者地位显赫。

(五)封国之君、蛮夷之地君长称公
封国之君如应公,蛮夷之地君长如楚公、邓公。应公(应公簋《集成》3477,西周早期、应公尊(《集成》5841,西周中期)为西周姬姓封国应国的国君,即为金文中常见的应侯。楚公(楚公家钟《集成》44,西周中晚期;楚公逆钟,《集成》106,西周晚期)是楚地的君长。徐少华在《邓国铜器综考》中指出,时代为西周中晚期的邓公鼎,铭文中的“邓公”为南土即南阳盆地地区嫚姓邓国的国君。
(六)泛指公卿侯伯一类的贵族
如公室、公族等。逆钟(《集成》60—63,西周晚期)铭文:“叔氏若曰:逆,乃祖考许政于公室”。公室指“诸侯或公卿的家室”,铭文中指的是叔氏的宗族家室,可知逆为叔氏家臣。卯簋盖(《集成》4327,懿王)铭:“荣伯乎令(命)卯曰:载乃先祖考死(尸)司榮公室”,荣公室即为荣伯的宗室。在这类词组中,公并非专指某人,也不表示某一具体身份,而是泛指公卿侯伯这一类的贵族。与之类似,中觯铭文(《集成6514,西周早期》)和番生簋盖(《集成》4326,西周晚期)铭文中提到的“公族”,意指与周王同宗同族的王室贵族,这里的“公”,也非专指某人或某一身份,而是一种泛称。
(七)用于表尊敬之意的辅助词
具体有公伯、公侯、公君等。魏芃在分析豦簋(《集成》4167,西周中期)铭文中的公伯时,指出“若此匋君公伯确有‘公’的身份,应该没有不直呼其为‘公’的道理”,“此人身份的核心是‘伯’,而不是‘公’”。亳鼎(《集成》2654,成王)铭文则出现了“公侯易(赐)亳杞土”的记载,陈梦家先生指出公侯之“侯”是爵名,然则公侯连称,侧重的人物身份应为侯,而不是公。此外,笔者认为圉方鼎(《集成》2505,西周早期)铭中提到的“公君”之“公”也不是人物身份的核心。燕侯的臣属圉称燕侯为“公君”,在燕国境内,燕侯对于臣下而言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身份是君上,所以“公君”一词,侧重的是境内封君的身份。由上述三例可知,在此类用法中,“公”没有具体的实际意义,不用来专指某人,也不是人物身份的主体,仅仅充当表示尊敬之意的辅助用词,从而彰显在成对的人物关系中,地位较卑者对地位较尊者的崇敬之意。
(八)表示女性的身份地位
公姞鬲(《集成》753,西周中期)器铭中提到了一位女性人物公姞,此称谓乃是“身份地位称号与姓的结合”,因其为姞姓、丈夫为穆公,故此称为公姞。

(九)僚属对其君长的尊称
簋(《集成》4099,西周中期)铭文中,
受到伯氏赏赐的,便称其君长伯氏为公。
(十)用作人名
“公”用作人名的用法,多被学者忽视。伯公父簠(《集成》4628,西周晚期)铭文载:“伯大师小子伯公父作簠。”伯公父之“伯”应是尊称或表示他的行辈为长,“父”为美称,“公”当为他的名。公臣簋(《集成》4184,西周晚期)铭中提到的公臣,既非官职,又非爵位,应是人名。
综上所述,“公”在西周周金文中主要是用作尊称或者表示尊敬之意的泛称,并没有明显的材料可以证明公是爵称。
二、西周金文中“侯”的具体用法辨析
西周金文中,“侯”的用法较为明确,分类也不算复杂,归纳如下。
(一)外服侯甸男的统称
簋(《集成》4215,西周晚期)、驹父盨盖(《集成》4464,西周晚期)和兮甲盘(《集成》10174,西周晚期)等器的铭文中提到了“诸侯”一词。
令方尊(《集成》6016,西周早期)和令方彝(《集成》9901,西周早期)铭文解释了诸侯的具体含义为:“诸侯:侯、甸、男。”也就是西周时期外服内三个不同等级的封君。侯,单独来看是三种封君的一种;“诸侯”一词中的“侯”,则是统称,代指属于同一体系不同等级的三种封君。至于为何选取“侯”作为代表,特称“诸侯”,是由于封国中“侯”的地位最高、数量最多,在三种身份中最具代表性。

(二)外服封国国君的称谓
这是“侯”在西周金文中最常见、最主要的用法。侯的数量众多,常见的同姓侯有燕侯、鲁侯、蔡侯、晋侯等,异姓侯则有纪侯、陈侯、鄂侯等。众侯担负着拱卫周室、助王征伐的职责。明公簋(《集成》4029,成王)铭文记录表明成王命明公以三族伐东国,鲁侯助师有功;晋侯苏编钟铭文(《近出》35—50)记载厉王命晋侯苏率师伐夙夷,晋侯有功受赏。鼬侯鼎(《集成》2457,西周早期)铭载:“鼬侯获巢,俘厥金胄,用作旅鼎。”铭文表现了鼬侯征伐有获、铭功记胜的行为。综上可知,侯的主要职能即为军事职能。周王室在各地分封诸侯,目的在于加强对王国各地的统治,并获得广泛的军事支持。
(三)表示宗族身份
侯氏簋(《集成》3781,西周晚期)中提到了侯氏,徐少华认为,“侯氏”应为邓侯之宗族。陈昭容先生则认为“侯氏”是应侯,侯氏作孟姬簋乃应侯为孟姬嫁到邓国而作的媵器。倘若侯氏即为应侯本人,何不直接称“应侯作孟姬簋”,而以侯氏代称呢?侯氏一词,应指与侯有宗法关系的宗室贵族,而非侯本人。
(四)通假作“维”或“惟”
遲父钟(《集成》103,西周晚期)铭有“侯父眔齐”,陈梦家指出父为遲父的自称,“案《尚书·酒诰》的‘惟亚惟服’相当于《周颂·载芟》的‘侯亚侯旅’”,故此“侯父”之“侯”,当读惟。杨树达在《积微居金石说》中则提出:“侯者,《诗·小雅·六月》云:‘侯谁在矣。’《大雅·文王》云:‘侯文王孙子。’《毛传》并云:‘侯,维也。’”认为侯作语辞,释侯为维。侯假作“维”或“惟”的这种用法在西周金文中仅此一例。
(五)用作地名
典型者如上侯。师俞鼎(《集成》2723,西周中期)铭文提到:“王女(如)上侯,师俞从。”不栺方鼎(《集成》2735,西周中期)铭中也有“王在上侯㕇”的记载。而启卣(《集成》5410,西周早期)铭文更加详细地记载说“王出兽(狩)南山”、“至于上侯境川上”,由此可知上侯是周王狩猎的区域。
(六)用作人名
据郑大师小子甗(《集成》937,西周晚期)铭可知,做器者名为侯父,身份是郑国大师的小子,即僚属。另有叔侯父簋(《集成》3802、3803,西周晚期)铭中的叔侯父、伯侯父盘(《集成》10129,西周晚期)铭中的伯侯父,叔、伯当指其排行,父为美称,侯是其名。
三、西周金文中“伯”的具体用法辨析
“伯,长也。”表示“长”的意思,是“伯”在金文中最普遍的用法,而其他的含义也基本上是从“长”的本义引申出来的。
(一)贵族长幼顺序的排行之长
西周青铜器中,常见伯作宝鼎(《集成》1914,西周早期)、伯作旅鼎(《集成》1915,西周中期)、伯作宝彝鼎(《集成》1917,西周中期)等,同时还有大量的仲作旅鼎(《集成》1922,西周中期)、仲作宝鼎(《集成》2047,西周中期)、叔作旅鼎(《集成》1928,西周中期)、叔作宝彝鼎(《集成》1923,西周)、季做宝彝鼎(《集成》1931,西周早期)等器物。由此可见,“伯”的一项基本用法,就是表示排行的伯仲叔季之“伯”,也就是同辈之长。同于此类的用法还有“伯某”,如伯申(伯申鼎《集成》2039,西周早期)、伯矩(伯矩鼎《集成》2170,西周早期)。伯某之伯,旨在强调在宗族血缘关系中的嫡长地位。李锋所谓的“社会秩序”应当包含这一层意思。另外,金文中常见“伯某父”的用法,伯某父的身份为嫡长子,此处的伯亦是强调排行之长的意思。

(二)表示大宗和宗子身份
常见的用法有“伯氏”或“某伯”。不簋(《集成》4328—4329,西周晚期)铭中提到了“伯氏”。在不簋铭中,受赏者不称赏赐者为伯氏,伯氏则称不为小子,在这组关系中,伯氏为大宗,他和不
为大宗宗子与小宗的关系。西周金文中除了有伯氏,还有仲氏、叔氏和季氏,伯氏与其他三者的区别,就在于大宗与小宗之别。而“某伯则是由嫡长子发展而成的宗子的称号”。例如朱凤瀚先生在《商周家族形态研究》中提出,同属西周王室贵族的荣伯、荣仲、荣季,以荣伯为大宗,荣仲、荣季等为小宗。有学者认为,“‘某伯’究竟是指爵等还是行辈,现在还难以推断。不过,至少有些‘某仲’‘某叔’‘某季’乃是氏称……” 既然有些“某仲”、“某叔”、“某季”是氏称,那么也存在相应的“某伯”为氏称的情况。在同是氏称的情况下,某伯相对于某仲、某叔、某季而言,就是大宗。此时,某伯即是该氏族的首领,也就是宗子。“伯氏”和“某伯”的区别在于,“伯氏”指宗子时,也可作小宗宗子的称谓,如五年召伯虎簋(《集成》4292,西周晚期)和六年召伯虎簋(《集成》4293,西周晚期)铭中,“伯氏”就被大宗宗子用来称呼小宗宗子。而“某伯”,既指大宗身份,又彰显宗子地位。
(三)用作国君之称
“伯”作国君之称时,包括畿内封国之君、商代遗留方国之君、为大国附庸的小国之君、地处偏远封国之君。畿内封国如杜国,君长称杜伯(杜伯鬲《集成》698,西周晚期),《铭文选》注曰:“杜,周畿内国。”商代遗留方国之君如戲伯(戲伯鬲《集成》666,西周中期)、㚅伯(㚅伯鬲《集成》696,西周中期)。戲、㚅为国族名,戲是商代戲方遗存,㚅伯是商代逢公之后。大国附庸的小国之君如邾伯(杜伯御戎鼎《集成》2525,西周晚期),邾伯是邾国之君,而邾国地近鲁国,为鲁国的附庸。偏远封国如曾国,曾国位于长江汉水之间,地近南国,其君有称曾伯(曾伯文簋《集成》4051,西周晚期)之例。

(四)王室贵族、卿士之称
此类用法十分多见,如铭文中的荣伯、定伯、单伯等,他们的地位显赫,无疑是周王室的重臣。然而他们的具体官职、所司何事,并不明朗。“王室的执政贵族亦多称伯,特别是地位仅次于公的重臣”,他们“一般多以伯称见之于当时的贵族社会”。推测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周代实行嫡长子继承制,继承祖辈官爵者必为嫡出长子,即同辈中的“伯”。久而久之,人们便习惯以“伯”来代称由嫡长身份而获得的职位了。
(五)司马司工类执政大臣的尊称
师
簋(《集成》4312,西周晚期)铭中有司工液伯,师簋(《集成》4283,西周中期)盖铭提到了司马井伯。陈梦家在《西周铜器断代》中分析师雍父和伯雍父的关系时指出,两个称谓指同一人,雍父可以独称,称“师”是其官职,称“伯”是其尊称。由此可知,“伯”可作为师类职官的尊称。小臣簋(《集成》4238,西周早期)铭文记载了伯懋父以殷八师伐东夷的事件,说明伯懋父有军事职能,这与师类官职的职责相近,很可能他的官职就是师官。这也就从另一个侧面表明,师类官职以“伯”为尊称。
(六)官职之正职
《西周金文官制研究》一书在解释“大师”时,提到:“大师前冠以伯仲之称,似乎暗示我们,西周之大师可能设有二人。伯大师、仲大师即大师有正副之别的明证。”金文提到“大师”的有大师小子师望盨(《集成》4354,西周晚期),提到“伯大师”的有伯大师盨(《集成》4394,西周晚期)、伯公父簠(《集成》4628,西周晚期,铭文为“伯大师小子伯公父作簠”),提到“仲大师”的有仲大师小子休盨(《集成》4397,西周晚期)。从器物名称或铭文内容可以看出,无论“大师”、“伯大师”还是“仲大师”,都有“小子”也就是属官。若三者之间没有分别,何不统称“大师”,而非要冠以伯仲之名呢?大师是西周王室的官职,而非爵位,担任此类官职并无明显的证据表明要区分嫡庶长幼,此外,金文中常见“伯大师”、“仲大师”而无“叔大师”或“季大师”,可见此处伯仲并非区别长幼嫡庶、大宗小宗之意,而是引申为官职正副的意思。“伯大师”乃“正大师”之意,是师类官职的官长,有时也省称为“大师”。
金文中“伯”的用法与“公”类似,主要用于尊称。而且,“公”与“伯”的称谓多见于中央执政贵族。可见,称公与称伯的两类群体同属于中央王朝官僚体系中。
四、西周金文中“子”的具体用法辨析
“子”的本义即为儿子,表示某人之子也是金文中常见的用法。后来“子”的含义有所扩大。林澐先生指出:“因为必须是确切的‘子’,才有继父嗣君的资格,所以‘子’也就逐渐转化成一种对世袭贵族的尊称了”。这揭示了“子”由本义儿子引申为贵族称号的原因。金文中见到的“子”的用法有以下几种。
(一)表示儿子
具体有大(太)子、仲子、沈子、涉子、毓子等不同的形式。堇鼎(《集成》9705,西周中期)铭文载:“燕侯令堇飴大保于宗周。庚申,大保赏堇贝,用作大子癸宝尊彝。”其中的“大子癸”,魏芃认为应是器主堇的家族内部的某位早逝的长子,而“大子”或“太子”并非国君之子的专称,也可普遍的称呼长子。“仲子”多表示排行第二的儿子,仲子作日乙尊(《集成》5909,西周早期)中的“仲子”即为此意。至于“沈子”,陈梦家先生在分析其含义的时候指出,“沈”在文法上是“子”的形容词,而非国邑封地的名称。“沈子”是表示儿子的特化称谓。“涉子”的用法应与“沈子”近似。“毓子”在金文中见于吕仲仆爵(《集成》9095,西周早期),大概意为“后子”。
(二)表示女儿
用“子”来表示女儿的用法并不多见。番匊生壶(《集成》9705,西周中期)铭文载:“番匊生铸媵壶,用媵厥元子孟妃□。 ”铭文内容为番匊生为女儿孟妃□出嫁作媵器,铭文中用“元子”指代孟妃□,意为长女。
(三)名词固定搭配
具体有公子、小子、天子、太子等。公子,指同族宗室成员。腹公子簋(《集成》4011,西周晚期)铭文中的“公子”,指腹国的宗族成员。“小子”一词在铭文中十分常见,含义也很丰富,大致可分为四类:一类意思为臣属、属官,前文所举的大师小子师望盨铭文中的“小子”,是做器者的自称,表示其为上司大师的属官;一类表示未成年人,王辉先生在注解何尊(《集成》6014,成王)铭文中的“小子”时,即作此说;还有一类用作宗室子弟,马承源先生把逆钟(《集成》60—63,西周晚期)铭文中的“小子”释为宗室子弟;最后一类表示自谦,如㝬簋铭文中,时王对前王自称小子,以表敬意。在㝬钟(《集成》260,西周晚期)铭文中有“惟皇上帝、百神,保余小子”的记载,此处的“小子”,也是铭文中时王的自称,表明自己谦逊的态度,用以祈求得到上天神灵的庇佑,获得征伐的胜利。“天子”在西周金文中更为多见,用来指周王,常见句式有“畯臣天子”(追簋《集成》4219,西周中期)、“对扬天子休”(伊簋《集成》4287,西周晚期)、“对扬天子丕显休”(静簋《集成》4273,西周早期)等,这些语句通常用来表示感激周天子之恩德。“太(大)子”一词,一者意为长子,前文已述。另有“芮大(太)子”,见于内(芮)大子白簠盖(《集成》4537,西周晚期)铭,指继位芮国国君之人。
(四)泛指子孙后代
此类用法在金文中多见,且句式多变。常见的有“子子孙孙永宝用享”(兮仲钟《集成》65,西周晚期)、“子孙永宝用”(芮公钟《集成》31,西周晚期)、“其孙子永宝”(榮子旅鼎《集成》2503,西周早期)等,通常用来表达对后世子孙的祝愿。
(五)封国君长称子
荣子旅鼎铭提到了“荣子”,荣为西周封国,荣子乃荣国之君。貯子己父匜(《集成》10252,西周晚期)铭中提到了“貯子”,《铭文选》解释为:“貯,国名。史籍假贾为貯,贾、貯声可通。贾,周之同姓国。”貯子即为貯国封君。

(六)蛮夷之君称子
如北子、
子。《礼记·曲礼下》云:“其在东夷、北狄、西戎、南蛮,虽大曰子。”说明了蛮夷君长多称“子”。而金文中的材料也印证了这一观点。㝬钟(《集成》260,西周晚期)铭文载:“王肇遹眚(省)文物勤疆土。南或(国)报子敢臽(陷)虐我土。”该铭文记录了
子犯边之事。
子是报国的君长,报国属于南国即周王国南部疆域。此外,西周金文中同时出现了“北伯”、“北子”,学者指出北伯诸器出土于北方的燕地,北子诸器出土于江陵地区。北子之北与北伯之北应是不同国家,北子所属的江陵之北,位于南方,也即㝬钟铭文提到的“南国”,是传统意义上的蛮夷之地。此外,地近南国的曾国,其国君也有称“曾子”(曾子仲诲甗《集成》943,西周晚期)的记载。

(七)用作干支记时之子
如甲子、戊子。记载武王征商的利簋(《集成》4131,西周早期)铭文有“珷征商,唯甲子朝”的记录,就点明了武王伐纣之日在甲子这天,与传世文献《尚书·牧誓》中“时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的记载相互印证。小臣傅簋(《集成》4206,西周早期)铭文“唯五月既望甲子”和六年召伯虎簋(《集成》4293,西周晚期)铭文“唯六年四月甲子”都提到了日干支“甲子”。除了甲子,作册折觥(《集成》9303,西周早期)铭“王在斥,戊子”中提到了“戊子”。可见,“子”用于干支记日,在西周金文中是较为普遍的。
(八)用作人名
虢文公子段(虢文公子段鼎《集成》2634,西周晚期)、虢季子白(虢季子白盘《集成》10173,西周晚期)、己候貉子(己候貉子簋盖《集成》3977,西周中期)中的“子”都是用作人名的组成部分。
“子”最基本的含义是表示子孙后代,在表示身份地位时,“子”的用法出现了一种看起来“矛盾”的现象,即同为称子,贵族称子是表示地位尊贵的美称,蛮夷军长称子则变成了蔑称。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实际上都是“子”的基本含义延伸的结果。用作贵族美称是基于血缘宗法的纯正性,可以彰显贵族嫡子身份。用作蔑称,则是因为“子”多是未成年的孩子,力量弱小,将蛮夷之地的人贬称子,就是出于这样一种考量。
五、西周金文中“男”的具体用法辨析
西周金文中的“男”,是“侯甸男”这一诸侯序列中等级最低的一级。从西周金文材料中,“男”的出现频次非常低,可以间接说明这一点。男,原作任,意为“任王事”。从为王任事之“任”,转化为诸侯等级中的“男”,裘锡圭先生认为:“也许任本是侯、伯等所委派的,率领人专门为王朝服役的一种职官”,“后来他们之中大概也有一部分人演变为诸侯,所以任(男)也变成了一种诸侯的称号。”西周金文中,仅见無皿(鄦,即许)男(無皿男鼎,《集成》2549,西周晚期)、㲋酉男(遣小子䪘帀簋《集成》3848,西周晚期)等极少数记载,透露的信息有限,故其用法也相当单一。
从金文中可以看出,“侯”、“男”是属于外服诸侯体系“侯甸男”的序列中。两者在用作称谓时,指代的是诸侯国君,因此传世文献所载的“五等爵”制中,只有侯和男是爵称。

结 论
西周金文中除了男的用法较为单一,公侯伯子的含义都相当复杂。但是很明显,在用作称谓时,它们并不属于一个体系,因此西周时期并不存在所谓的五等爵制。如要按照系统划分,可把公伯归为一类,他们都是服务于西周王室的执政贵族。公的级别明显高于伯,据班簋(《集成》4341,西周早期)铭文所载,毛伯在接替虢公职务后称公不再称伯,可为一条证据;再据前文的分析中,称公者往往是师保类的高级官僚,称伯者多是司马、司工等卿士类的官僚,也是明证。侯男属于同一系统,即“侯甸男”这一诸侯体系。侯的地位要高于男,封侯的数量也远比男多,从相关材料的多寡可以得出此结论。公伯属于中央王官系统,侯男属于外服诸侯体系,二者各有职守,共同拱卫周王室。而个别公侯兼称的情况,如应侯又称应公,可能因应侯地位尊隆,既是诸侯君长,又入周王室担任要职,所以能以侯而称公。殷商遗民,不守周礼者,在国君称谓上也不受周室秩序节制,故殷商遗留方国君长称伯,应另当别论。
而子在作为称谓时,最主要的作用是强调嫡子身份,并由此身份而获得的宗族首领或者一国君长的地位。这种意义的子,是基于宗法血缘关系的一种美称。而蛮夷之君称子,首先是周人以中央的角度对蛮夷国家君长的蔑称(周厉王“南国子敢虐处我土”的用辞和语气明显有对于南国蛮夷的蔑视之意),而蛮夷地区的君长畏于周王朝的强大,默认了此种称呼,并以此自称,以示驯服(子向周王请罪)。但是蛮夷之国毕竟地处偏远,周室天威无法有效传至;加之教化未遍,蛮夷君长难免生出桀骜之心,行僭越之事,自称公、伯,甚至称王。公、伯、子,称谓混乱,多由蛮夷君长自行其是导致。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西周金文中“公”、“伯”、“子”在用作称谓时,是一种类称,多表示尊称;而“侯”、“男”才是传统认为的爵称。除了用作称谓,“公”、“侯”、“伯”、“子”还用作地名或人名,或者用作词组固定搭配,关于“公”、“侯”、“伯”、“子”、“男”的其他用法,及它们之间的联系,有待更多资料佐证。但西周时期不存在所谓的“五等爵”制,从金文资料来看是无疑义的。
参考文献
资料汇编:
[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
[2]刘雨,卢岩.近出殷周金文集录[M].北京:中华书局,2002.
[3]刘雨,严志斌.近出殷周金文集录二编[M].北京:中华书局,2010.
专著:
[1]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M].北京:中华书局,2004.
[2]马承源.商周青铜器铭文选[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
[3]张亚初,刘雨.西周金文官制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4.
[4]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5]中华书局编辑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论文类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9.
[6]丁山.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M].北京:中华书局,1988.
[7]郭沫若.郭沫若全集[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2.
[8]杨树达.积微居小学述林[M].北京:中华书局,1983.
[9]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10]赵伯雄.周代国家形态研究[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
[11]徐少华.周代南土历史地理与文化[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
[12]陈絜.商周姓氏制度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13]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
[14]王辉.商周金文[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15]王世民.西周春秋金文所见诸侯爵称的再检讨[C].李宗焜.古文字与古代史第3辑.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2.
[16]李锋.论“五等爵”称的起源[C].李宗焜.古文字与古代史第3辑.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2.
[17]林澐.从武丁时代的几种“子卜辞”试论商代的家族形态[C].吉林大学古文字研究室.古文字研究第一辑.北京:中华书局,1979.
[18]裘锡圭.甲骨卜辞中所见的“田”“牧”“卫”等职官的研究[C].文史编辑部.文史第十九辑.北京:中华书局,1982.
期刊论文:
[1]王世民.西周春秋金文中的诸侯爵称[J].历史研究,1983(3).
[2]陈恩林.先秦两汉文献中所见周代诸侯五等爵[J].历史研究,1994(6).
[3]刘源.“五等爵”制与殷周贵族政治体系[J].历史研究,2014(1).
[4]杨宽.西周中央政权机构剖析[J].历史研究,1984(2).
[5]徐少华.邓国铜器综考[J].考古,2013(5).
[6]俞伟超,高明.周代用鼎制度研究[J].北京大学学报,1978(2).
学位论文:
[1]盛冬铃.西周铜器铭文中的人名及其对断代的意义[D].北京:北京大学历史系,1981.
[2]魏芃.西周春秋时期“五等爵称”研究[D].天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