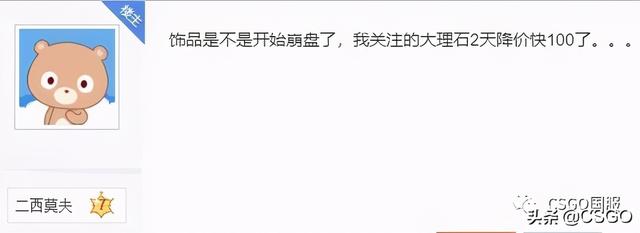摘要:“存天理,去人欲”是理学思想的核心价值观念,是对儒学道统论中“从道不从君”、仁义之道高于君主之位思想的继承发展它主要针对统治者违背儒家纲常伦理,失德乱政,恣情纵欲而发这一思想要求统治者以道制欲,遏止私欲,以德治国,以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适应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而非禁止普通民众饮食男女的基本物质需求它的产生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及合理性,但亦存在自身的流弊和消极影响自近现代以来,这一思想遭到了人们的激烈批判,这虽有其道理,但亦需要我们对“存天理,去人欲”思想提出的针对性、原因等作客观的分析,以便更好地认识其实质和意义,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四君子招纳了哪些人才?以下内容希望对你有帮助!

四君子招纳了哪些人才
摘要:“存天理,去人欲”是理学思想的核心价值观念,是对儒学道统论中“从道不从君”、仁义之道高于君主之位思想的继承发展。它主要针对统治者违背儒家纲常伦理,失德乱政,恣情纵欲而发。这一思想要求统治者以道制欲,遏止私欲,以德治国,以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适应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而非禁止普通民众饮食男女的基本物质需求。它的产生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及合理性,但亦存在自身的流弊和消极影响。自近现代以来,这一思想遭到了人们的激烈批判,这虽有其道理,但亦需要我们对“存天理,去人欲”思想提出的针对性、原因等作客观的分析,以便更好地认识其实质和意义。
关键词:天理;人欲;道统;针对性;必然性;流弊
“存天理,去人欲”是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兴起的理学思潮的核心价值观念,它的产生有其历史的根源与合理性,是对当时社会存在的客观反映,当然亦有其自身的流弊。自清及近代以来,这一思想遭到了人们的激烈批判。以往学术界在批判“存天理,去人欲”思想的流弊时,往往采取一棍子打死的态度,而忽视对其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的探讨。如李泽厚说:“以程朱为中心的‘理学’在其数百年统治期中对广大人民的惨重毒害,……怵目惊心地可以看到这些理学家们是那样地愚昧、迂腐、残忍……,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要求用等级森严、禁欲主义……等等封建规范对人进行全面压制和扼禁。”(李泽厚)侯外庐等主编的《宋明理学史》说:“二程提出‘去人欲,存天理’,是针对人民求生存而发,它并不是要求统治者去遏什么人欲。这种说教对后世有严重危害。劳动人民背着‘天理不胜人欲’的黑名就死,屠伯们却抹去脸上的血污,逍遥复逍遥。‘以理杀人,其谁怜之!’戴震的名言揭露了二程‘存天理,去人欲’的本质。”(侯外庐等主编,第170-171页)王育济说:“‘明天理灭私欲’成为一种以无条件地牺牲个人利益,无条件地牺牲人的感性自然欲求为旨归的极端道德主义的说教,成为一种带有鲜明宗教禁欲主义倾向的教条。”(王育济)此乃对理学理欲观的彻底否定。王泽应说:“我们既不能走‘存天理,灭人欲’的禁欲主义路径,也不能走它的反面即纵欲主义或享乐主义路径。”(王泽应)这仍是把“存天理,灭人欲”视为禁欲主义。除以上所引,类似的观点在学术界还有很多,其影响较为广泛,以至于人们一提到理学存理去欲的价值观,基本上都持否定的态度。这虽对清理理学的流弊有一定的作用,但同时也有相当的片面性,缺乏对存理去欲观念的客观全面的理解,看不到作为一代学术思潮的理学之所以兴起并蔚为大观的历史必然性,以及理学思想中所蕴含的积极因素,不利于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
近些年来,也有学者提出要对理学的理欲观重新评价,认为存理去欲的思想有其一定的道理,不能全盘否定,它对于今天提倡反腐倡廉,遏止现实社会生活中因过分强调满足私欲而助长的贪腐现象,也是具有积极的现实借鉴意义和价值的。然他们对存理去欲观念之所以产生的原因仍缺乏深入客观的探讨。本文拟结合“存天理,去人欲”思想提出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历史根源,对此问题再作探讨,以就正于方家。
一、“存天理,去人欲”针对的对象通过考察提出“存天理,去人欲”思想之人物的原话,结合理学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原因,可以看出,其提出“存天理,去人欲”思想的目的主要是通过“以理制欲”来约束统治者的贪婪欲望,以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针对封建君主和皇室宗亲于儒家纲常伦理多有违背,恣情纵欲、失德乱政的行为,理学家提出了激烈的批判。程颐指出:“太宗佐父平天下,论其功不过做得一功臣,岂可夺元良之位?太子之与功臣,自不相干,唐之纪纲,自太宗乱之。终唐之世无三纲者,自太宗始也。”(《二程集》,第236页)批判唐太宗违背三纲,夺太子之位。朱熹亦斥责“唐太宗分明是杀兄劫父代位”(《朱子语类》,第3259页),认为这是导致天下大乱、国家衰亡的原因。由此他们把“存天理,去人欲”的目标首先指向封建统治者。理欲之辩是当时人们讨论的核心话题,二程划时代地提出天理论哲学,把儒家纲常伦理原则与哲学本体论相结合,这也是宋代理学发展的主要趋势。理学家将天理论哲学运用于政治,得出用天理治国的主张,即把内在于人心的天理,贯彻到外在的政治事务中去,由内圣开出外王。张栻指出:“王者之政,其心本乎天理,建立人纪,施于万事。”(《张栻全集》,第785页)认为天理是治国的根本,要求统治者顺应天理,按天理的原则治理国家而不得违背。朱熹亦强调:“修德之实在乎去人欲,存天理。”(《朱熹集》,第1633页)主张修德施政,把“去人欲,存天理”落到实处。因此,思想家们提出“存天理,去人欲”的目的是为了纠正唐统治者“闺门无法不足以正天下”(范祖禹,1986年a,第636页)的乱象,以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和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转。这基本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
范祖禹认同理学及其道统论。程颢卒,范祖禹云:“先生于经,不务解析为枝词,要其用在己而明于知天。其教人曰:‘非孔子之道,不可学也。’盖自孟子没而中庸之学不传,后世之士不循其本而用心于末,故不可与入尧舜之道。先生以独智自得,去圣人千有余岁,发其关键,直睹堂奥,一天地之理,尽事物之变。”(见《二程集》,第333-334页)这里所说的“一天地之理,尽事物之变”,就是对程颢天理论的认同。为此,范祖禹著《唐鉴》,明确把唐太宗视为“存天理,去人欲”所要纠正的对象,指出,李世民“为子不孝,为弟不弟,悖天理灭人伦而有天下,不若亡之愈也。故为《唐史》者书曰:秦王世民杀皇太子建成、齐王元吉,立世民为皇太子,然则太宗之罪著矣”(范祖禹,1986年a,第481-482页),认为唐太宗李世民当年作为秦王虽有功,但不过是一藩王,而建成却是太子,太子乃君之贰、父之统,杀太子是为无君父,乃违背天理、灭绝人伦的无道行为,因而坚持道义重于生死的原则,认为宁愿守死,而不能为不义,批评唐太宗悖天理而篡位,其罪甚著。从这里可以明确看出,宋代天理论的提出,其“存天理,灭人欲”所针对的正是唐太宗一类统治者违背天理的行为,而非普通民众饮食男女的基本物质需求。范祖禹并批评唐王朝:“三纲不立,无父子君臣之义,见利而动,不顾其亲。是以上无教化,下无廉耻。古之王者必正身齐家,以率天下。其身不正,未有能正人者也。唐之父子不正,而欲以正万事,难矣。”(同上,第543页)认为唐统治者违背君臣父子的原则,为了满足个人的私利和权色欲求,而导致“上无教化,下无廉耻”。在上的统治者“其身不正”“父子不正”,何以正人,怎能治理好国家?由此可见,作为天理重要内涵的三纲和作为道统论重要内涵的修齐治平之道,首先指向的均是封建统治者。程颐深知封建统治者过分的人欲所带来的危害,力主以天理来加以遏制。他说:“天下之害,皆以远本而末胜也。峻宇雕墙,本于宫室;酒池肉林,本于饮食;淫酷残忍,本于刑罚;穷兵黩武,本于征伐。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后王流于末者,人欲也。损人欲以复天理,圣人之教也。”(《二程集》,第1170-1171页)把峻宇雕墙、酒池肉林、淫酷残忍、穷兵黩武等视为人欲之末,其为害天下甚大,主张以“天理”来“制其本”,以损“后王”的人欲之末。这就明确把损人欲的对象指向后世封建帝王。从这里也可看出,理学家“损人欲以复天理”的“圣人之教”主要是针对封建统治者的,而非一般的民众;理学家反对的只是人欲之末,而非正常的人欲。
从程朱批判佛教的禁欲主义也可看出,理学家并不排斥正常的人欲。程颐说:“佛之所谓世网者,圣人所谓秉彝也。尽去其秉彝,然后为道,佛之所谓至教也,而秉彝终不可得而去也。耳闻目见,饮食男女之欲,喜怒哀乐之变,皆其性之自然。今其言曰: ‘必尽绝是,然后得天真。’吾多见其丧天真矣。学者戒之谨之,至于自信,然后彼不能乱矣”。(同上,第1180页)这里程颐明确将“饮食男女之欲”视为“性之自然”,而对佛教将饮食男女之欲“必尽绝是”的禁欲主义则持反对态度,这怎么能说理学的“存天理,去人欲”是“鲜明宗教禁欲主义”“坚决主张禁欲复理”呢?朱熹亦说:“夫外物之诱人,莫甚于饮食男女之欲,然推其本,则固亦莫非人之所当有而不能无者也。但于其间自有天理人欲之辨,而不可以毫厘差耳,惟其徒有是物而不能察于吾之所以行乎其间者,孰为天理?孰为人欲?是以无以致其克复之功,而物之诱于外者,得以夺乎天理之本然也。今不即物以穷其原,而徒恶物之诱乎己,乃欲一切扞而去之,则是必闭口枵腹,然后可以得饮食之正,绝灭种类,然后可以全夫妇之别也。是虽二氏无君无父之教,有不能充其说者,况乎圣人大中至正之道,而得以此乱之哉?”(朱熹,1986年,第234-235页)在这里,朱熹明确肯定饮食男女之欲是“人之所当有而不能无者”,而批评将饮食男女之欲一切“扞而去之”“闭口枵腹”的做法,认为这是“绝灭种类”,流于佛老二教,而非圣人大中至正之道。可见理学家的天理人欲之辩是明确肯定人的饮食男女之欲,而反对灭绝人欲的。这出自二程、朱熹等理学家的原话,是最有说服力的。由此可以看出,他们肯定饮食男女之欲是不能灭绝的,其天理也正是建立在对人的饮食男女之欲“即物以穷其原”的基础上,而非建立在灭绝人欲的基础上。理学家反对的只是脱离义理指导的人欲,这是十分明确的。
针对宋哲宗13岁就开始贪恋女色,致使宫女“已有怀娠,将诞育者”(范祖禹,1986年b,第237页),范祖禹上太皇太后疏云:“皇帝已近女色,后宫将有就馆者。有识闻之,无不寒心。”(同上,第239页)并上书哲宗直接劝谏云:“今陛下未建中宫,而先近幸左右,好色伐性,伤于太早,有损圣德,不益龙体。……今陛下圣学,天下未有所闻,而先以嗜欲闻于天下,此臣之所甚忧也。”(同上,第237-238页)要求哲宗皇帝“惟陛下抑情制欲”(同上,第239页),好于进德,远于声色,坚决去除和戒止“有损圣德”的私欲好色之举,以避免出现“纪纲坏乱,政事荒僻,使天下以陛下为逸欲之主”(同上)的不良局面。说明其“抑情制欲”、去“逸欲”的对象也主要是封建帝王。
宋以来的学者大多将天理人欲对举,重视理而轻视欲。一方面,二程、朱熹等理学家提出“存天理,去人欲”的理欲观,是为了重整儒家纲常,对以皇帝为代表的统治阶级进行必要的道德约束,当然对普通民众也有道德自律的要求,以实现社会治理。另一方面,“存天理,去人欲”并非禁欲主义,这从程朱理学家等的原话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他们是明确反对禁欲主义的。但由于偏重于道德理性的价值,而相对忽视人的自然属性和物质欲望,以致产生弊端。朱熹说:“熹窃以谓人欲云者,正天理之反耳。谓因天理而有人欲则可,谓人欲亦是天理则不可。盖天理中本无人欲,惟其流之有差,遂生出人欲来。”(《朱熹集》,第1890页)认为人欲与天理相反,天理中本无人欲。并强调“天理人欲,不容并立”(朱熹,1983年,第254页),去人欲才能存天理。虽然朱熹也说过“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朱子语类》,第224页),但他没有、也不大可能在饮食和要求美味之间划一条明确的界限,所以重理轻欲的思想成为一时之定论。而当程朱理学被定为官学后,统治者进一步强化了理欲的对立,以约束下层百姓,而日益淡化对自身的制约,存理去欲价值观的流弊也日渐显现,影响到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二、“存天理,去人欲”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原因“存天理,去人欲”是宋代理学的核心价值观,亦是理学最重要的理论———天理论哲学的基本内涵之一,它的产生有其相应的历史背景。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关系和政治制度上的变化,使得社会意识形态亦发生相应的变化。鉴于前代失德乱政的恶劣后果,宋朝统治者需要用新的统治思想来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以适应社会变迁和发展的客观需要,于是新的伦理道德规范———“存天理,去人欲”思想便应运而生。
理学兴起于唐宋社会转型时期,当时面临维护社会治理与稳定、儒家伦理价值观念的重建等重大社会问题,总起来看,“存天理,去人欲”思想提出的历史背景和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唐宋时期社会变化的客观要求。宋代理学“存天理,去人欲”的思想是对儒学道统论中“从道不从君”、仁义之道高于君主之位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二程指出,儒家的伦理纲常之所以在唐代未能起到重要作用,对皇室的约束几乎谈不上,就是因为皇帝凌驾于“天理”之上,不守伦理,纪纲不立,所以导致动乱以至亡国。由此,理学家总结唐王朝的历史教训,提出以“天理”来规范皇帝的行为,限制重臣的权势。二程明确指出:“‘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天下之治乱系乎人君仁不仁耳。离是而非,则生于其心,必害于其政”。(《二程集》,第390页)如果君心出了问题,背离仁义,不辨是非,必害于政,所以必须把格君心之非当作头等大事:“格其非心,使无不正”。(同上)为了格君心之非,程颐十分重视帝王讲师的作用。他在任崇政殿说书给哲宗皇帝讲课时,便是通过开导君心,来纠正君主不合于“理”的念头,并坚持坐讲于殿上,以示师道尊严。
宋代理学是宋学的主流,宋代理学思潮的兴起是继先秦百家争鸣之后出现的中国文化发展的又一次高潮。理学思潮的出现,具有客观的必然性,它既是社会经济、自然科学发展的结果,又是社会政治、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同时亦是中国经学发展到宋代的产物。理学之能够成为思潮,绝不是偶然的现象,也不是一两个或少数思想家的意志所能左右,它植根于深厚的时代土壤之中。我们既不能以理学在今日不合时宜而否定它的历史价值,也不能否定它在定于一尊之后的消极性和局限性。对于理学思想本身的消极因素以及其中包含的合理因素,需要通过认真研究来加以深入总结和批判继承。
宋王朝建立后,加强中央集权制,复兴儒学,重整纲常,解决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和社会治理问题;发展社会经济,提高生产力水平,促进自然科学的发展,成为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包括理学家在内的宋学学者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端正君心,认为唐、五代以来社会动乱的根本原因在于统治者私欲泛滥,败坏人伦,皇室宗亲乱伦失德,故而强调维护天理纪纲以端正统治者的本心,自上而下推行仁义纲常,以实现社会治理。
宋学学者大多继承了唐代韩愈提倡道统、重整儒学的思想。宋初孙复强调君为臣纲、父为子纲,他说:“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禽兽之道也,人理灭矣。”(孙复,第178页)认为违背了伦理纲常,则为“禽兽之道”而丧失了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他还把“去君臣之礼,绝父子之戚,灭夫妇之义”(同上,第176页)称为“异端”邪说,认为它只会祸害天下民众,“以之为国则乱矣,以之使人贼作矣,儒者不以仁义礼乐为心则已,若以为心,则得不鸣鼓而攻之乎?”(同上)要求以儒家仁义礼乐为心,对违背三纲的行为“鸣鼓而攻之”。石介继承了韩愈的道统论,提倡以道事君,他说:“夫不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事其君者,皆左道也。”(石介,第71页)又说:“人道非它,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夫妇、父子、君臣灭,则人道灭矣。”(同上,第96页)强调三纲是人道的准则而不可灭。这是对唐、五代伦常扫地的批判,体现了宋学人物的伦理观,其思想与理学相类。
欧阳修认为社会动乱的主要原因就在于背离了三纲五常之道。他说:“五代,干戈贼乱之世也,礼乐崩坏,三纲五常之道绝,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扫地而尽于是矣。”(欧阳修,第108页)又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乖,而宗庙、朝廷、人鬼皆失其序,斯可谓乱世者欤,自古未之有也。”(同上,第101页)欧阳修对以冯道为代表的五代鲜廉寡耻的士风进行了批判,指出:“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乱败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读冯道《长乐老叙》,见其自述以为荣,其可谓无廉耻者矣,则天下国家可从而知也。”(同上,第350页)冯道(公元882—954年),自号长乐老。后唐、后晋时历任宰相;契丹灭后晋,又附契丹任太傅;后汉时,任太师;后周时,又任太师、中书令。曾作《长乐老自叙》,历述自己事四朝、相六帝,多朝为官的经历。欧阳修认为,冯道改换门庭,历事多朝,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真“可谓无廉耻者”。指出身为大臣而无廉耻,天下国家岂有不乱不亡之理。后世因冯道历事四朝,多有非议。可见以冯道为代表的鲜廉寡耻的士风遭到了宋人的唾弃。
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也对唐、五代时的世风提出批评,他说:“宋兴,则由深深反省自觉,涌出理性,开出中国历史上第二次之文化运动。这是华族自身之文化生命文化理想之复位。民族生命与文化生命又归于一。原宋儒之讲学,一在对唐末五代无廉耻,人不成人而发;一在对佛教而发。”(牟宗三,第237页)这与欧阳修的观点相近。
范祖禹批评唐玄宗纳儿媳寿王妃杨玉环作为自己的贵妃:“明皇杀三子,又纳子妇于宫中,……父子夫妇君臣,人之所以立也,三纲绝矣,其何以为天下乎!”吕祖谦注云:“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范祖禹,1986年a,第534页)可见宋学人物和其中的理学家均以三纲来批判和约束封建帝王的乱伦行为和私欲,认为违背了三纲,就会导致天下大乱,并造成赤地千里,民不聊生,封建王朝日渐衰落,走向灭亡的恶果。
从这里可以看出,宋学学者和其中的理学家提出重塑社会伦理、抑制私欲的主张,其出发点主要是针对封建帝王和上层统治者,而不是下层百姓,是为了正君心。理学家将其概括提炼为“存天理,去人欲”的命题,这适应了唐宋之际社会变化、治国理政的客观需要,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至于后世封建统治者将其用来针对下层民众,成为套在人民头上的礼教枷锁,无疑是歪曲了思想家提出这一思想的本旨。
理学家对封建统治者有违儒家伦理纲常的失道行为提出严厉的批评,提出系统的“存天理,去人欲”的思想,反映了时代的要求和历史的必然。理学家和宋学学者重视统治阶级内部的儒家纲常伦理法度,这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和历史必然性,从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历程看,儒家伦理纲常最大程度适应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以血缘宗亲为纽带、注重上下尊卑社会等级的宗法制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客观需要,这是维护和保持社会稳定,发展经济文化的必要前提。
由此,理学家批评道不行于天下以及与中原儒家文化不同的价值观,并以义理为标准,总结历史教训,明于天理、人欲之分,以规范社会治理秩序,维持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转。朱熹批评说:“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朱熹集》,第1592页)针砭统治者未遵行圣人之道,而陷于利欲之中。并强调:“《书》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朱子语类》,第207页)此处把道统十六字心传与明天理、灭人欲联系了起来。同时也说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道之不行、三纲失序将导致天下动乱而不得治理,它不仅动摇了封建统治的政治基础,而且也使社会的稳定难以维系,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的生命财产也得不到保障。有人褒扬唐朝政治文化的所谓宽容性,认为唐朝在君臣、父子、夫妇之间是相当宽容的,但这种对子杀父、臣弑君、男女无别、人无廉耻、纲纪败坏、荒淫奢侈乱象的所谓“宽容”,并没有带来社会的长治久安和稳定发展,反使得唐王朝日渐衰落,走向灭亡。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期之一,战乱频仍,人口数量大减,权力之争超乎寻常,不少帝王就是被自己的儿子、家人所杀,这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破坏了社会经济,给百姓生活带来极大的痛苦和灾难。因此,违背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价值而谈论政治文化的宽容与否,很难得出正确的结论,也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和价值。
质言之,理学“存天理,去人欲”价值观的产生有其多方面的背景和原因,它基本适应了唐宋之际社会变化的客观要求,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存在,因而具有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正因为如此,“存天理,去人欲”的价值观不只是理学家们提倡,而且在宋学学者如“宋初三先生”、欧阳修、范祖禹等人的思想中也多有体现或共识,只不过理学家将其作为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念而深入阐发罢了。
第二,回应佛老挑战的需要。佛教视人间为苦海,其人生理想是解脱,即通过修持佛法,以超越世俗世界,进入涅槃境界。“佛教对人生和对社会的主张,佛教伦理观念的泛滥,势必对儒家的伦理观念起一种腐蚀、瓦解作用,从而危及儒家的社会理想结构。”(方立天,第264页)隋唐时期,佛老的势力和影响甚大,由于得到统治者的提倡和支持,曾一度冲击儒学,动摇了儒家文化的主导地位。这一时期佛老盛行,宗教冲击人文,统治者思想失向。佛老提倡超脱人伦,入于寂灭虚空,追求个体超越修炼,不讲社会治理,带来了严重后果。对此,理学家提倡“存天理,去人欲”,强调重建儒家人伦社会秩序。
理学思潮的兴起,经学的理学化,成为中国宋代学术发展的趋势。新儒学者在研治经学阐发义理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面临三教关系这样一个时代背景,并对隋唐至宋初佛老盛行、冲击儒学的状况,作出自己的回应。
需要指出的是,理学家对佛老的批判,虽然也涉及批判佛教的因果报应说和道教的长生成仙说,但主要还是批判佛老违背儒家伦理纲常,不讲社会治理,动摇了社会稳定的基础。这是对唐、五代佛老盛行,统治思想涣散,导致社会大动乱的深刻反思。
理学家提出的存理去欲思想是对佛老挑战的有效回应。佛教禁欲主义是对合理人欲的否定,它提倡出世出家,注重个人修炼,不讲入世主义的社会基础———儒家世俗人伦社会关系,所以被理学家批判是为私而不是为公,违背了三纲五常之天理原则。批判佛教去天理禁人欲的“异端”思想和行为对社会造成的危害,这也是理学家所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这个问题如不能妥善解决,也会带来严重后果,动摇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根基。
由此,程颢、程颐对佛教作了严厉批判,他们抨击佛学:“大概且是绝伦类,世上不容有此理。又其言待要出世,出那里去?又其迹须要出家,然则家者,不过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处此等事,皆以为寄寓,故其为忠孝仁义者,皆以为不得已尔。又要得脱世网,至愚迷者也。”(《二程集》,第24页)认为佛教不讲纲常伦理,主张出世出家,对社会造成危害。指出如果佛教思想泛滥,人人都成佛徒,那么,不仅天下国家将无法治理,而且社会生活及人伦关系也难以维持。又批评佛教逃避家庭和世俗社会,不受儒家伦理的约束,不承担家庭、社会责任,以至于无父无君,如此等等,佛教的出世主义遭到了二程的坚决抨击。二程还以天理论批评了佛教以现实世界为幻化的观点,指出:“其说始以世界为幻妄,而谓有天宫;后亦以天为幻,卒归之无。佛有发,而僧复毁形;佛有妻子舍之,而僧绝其类。若使人尽为此,则老者何养?幼者何长?以至剪帛为衲,夜食欲省,举事皆反常,不近人情。”(同上,第409页)从二程的批判中可知,佛教以现实世界为幻妄,提出变幻无常的理论,是为其出世主义的行为作论证的。这也是二程批判佛教世界观的基本原因。
二程等理学家对隋唐以来佛老盛行、冲击儒学的积极回应,体现了儒家学说的基本精神和价值取向。他们以复兴儒学为己任,在回应佛老挑战的论争中,批判了佛、道有悖于儒家纲常伦理的教旨教义,以解决唐至五代宗教冲击人文、胡化冲击汉化、道德沦丧和社会动乱等严重社会问题。这是对隋唐以来宗教盛行、儒学地位每况愈下的深刻反思。为了解决社会危机和理论危机,宋代理学家在回应佛老的挑战中,对佛老思想既批判又吸取,逐步发展了儒学的思辨哲学,创造性地提出天理论哲学。而以天理论为基础的“存天理,去人欲”思想即是把宇宙本体论与儒家伦理学紧密结合的伦理政治哲学,是对佛老挑战的回应,基本适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而有别于汉唐儒学。由唐及宋初的佛老盛行,到宋末理学居于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数百年间,经过一代又一代新儒学者的不懈努力,理学蔚然成为一代学术文化思潮,广泛影响社会,彻底改变了佛老盛行、冲击儒学的局面,形成了以儒学为本位,吸取佛、道思辨哲学的三教融合的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基本格局。
三、“存天理,去人欲”的流弊和消极影响在宋明理学风行数百年的历史背景下,来考察“存天理,去人欲”的流弊,可以发现,其中既有统治者的歪曲利用而造成的社会风气,亦有理学家自身理论的偏差,同时也有人们一定的误解误读。其流弊长期存在,因而戴震、胡适等对此进行批判也是必然的。
反思和总结存理去欲观念的影响和流弊,应是把天理与人欲结合起来,而不应过分强调一方而忽视另一方。在这个意义上,理学“存天理,去人欲”的观念存在着压抑人性的弊端,而正确的原则应是把道义与人文主义、人性关怀相结合。
由于理学重视人的道德理性,强调道德自律,而具有相对忽视人的自然属性的特征。理学虽批判佛教的禁欲主义,对人的自然属性并不抹杀,但理学强调和重视的主要是人的道德理性,并将其作为先验的、天赋的人的本质。与此相关,在价值取向上,宋明理学注重价值目标和道德理想的实现,相对轻视物质利益和欲望的满足,这也使之受到了来自不同学派的批评。
客观上讲,理学在历史上有其产生的必然性,曾起过积极的作用与影响,但到了宋末及明清时期理学上升为官方意识形态后,“存天理,去人欲”思想被统治阶级歪曲利用和发挥,加之其理论本身的局限性也逐渐显露,造成了一系列流弊,其中包括:重视道义原则,相对忽视人的情感和物质欲望,产生抑制人性的弊端;以内圣修养为重,相对忽视物质利益和社会实践;强调天理至上,相对忽视事功修为,致使“虚意多,实力少”;等等。由于理学“存天理,去人欲”观念本身便具有这些流弊,加上历代封建统治者的片面歪曲利用,使得理学在一定程度上逐渐成为束缚人们思想的枷锁。这使它遭到了后世学者的激烈批判,其中最为激烈的莫过于清代的戴震,他批判“后儒以理杀人”,控诉当时统治者以“名教”“天理”为借口来残害百姓。他说:“宋以来儒者,以己之意见,硬坐为古贤圣立言之意,而语言文字实未之知。其于天下之事也,以己所谓理强断行之,而事情原委隐曲实未能得,是以大道失而行事乖。……后儒不知情之至于纤微无憾,是谓理,而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之所谓法。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浸浸乎舍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戴震集》,第187-188页)戴震用“理者存乎欲”的命题批判了“存天理,去人欲”的理欲观,对封建统治者和“后儒”的弊害提出抗议,表达了同情人民的愿望,这值得肯定。但对戴震的批判也要加以分析,戴震抓住了二程理欲观灭私欲的一面,而未看到二程肯定客观物质欲求的一面,并把后儒的流弊及统治者压制民众的人欲归之于宋儒的理欲观,这说明他对二程及宋儒理欲之辩的完整含义未能全面理解。张岱年先生在《中国哲学大纲》中指出:“道学家之排斥人欲,其实并不是否认一切欲望,而是将最基本的欲提出不名为欲;将欲之一词,专限于非基本的有私意的欲。”(张岱年,第458页)认为理学家的去人欲是指排斥私欲,而非否认一切欲望,这是需要人们注意把握的。
理学家继承儒学道统论“从道不从君”的传统,以“天理”为至上,隐含着与封建君主君权至上观念的冲突,朱熹本人就明确批评宋宁宗“独断”。宋以后的封建统治者一步步削弱“存天理,去人欲”原则对自己的约束,而一步步加深对老百姓的约束,使之成为束缚下层民众和妇女的礼教枷锁,造成了不少人间灾难,这已经违背了思想家的初心和本意。
四、结 语通过对“存天理,去人欲”理论本身的针对性和主要内容的分析,将其放在唐宋社会转型时期的历史背景下来考察和评价,则可以看出其所具有的时代价值和一定的社会积极作用。面对唐、五代时期朝纲紊乱与“人欲横流”的社会环境,理学家提倡以理节欲,是为了遏止和反对统治者的特权,是以理抗势,从道不从君。它有利于纠正统治阶级失德乱政、恣情纵欲的时弊,并重塑儒家伦理,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朱熹上书宋孝宗云:“一念之萌,则必谨而察之:此为天理耶?为人欲耶?果天理也,则敬以扩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阏;果人欲也,则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滞。”(《朱熹集》,第542页)因此,宋儒“存天理,去人欲”的理论从时代性上看,具有纠正唐宋统治者人欲横流导致社会失序的价值;从思想家的理论主张和社会实践上来看,亦具有克服统治阶级私欲膨胀的价值。因此,它对于治国理政、维护社会长治久安和稳定发展均具有重要意义。
撇开封建统治阶级的歪曲利用等因素,便会发现理学家所讲的“去人欲”实指“去私欲”,即去除人心中不合“理”的过分的私欲,并非如传统观点认为的“去人欲”就是灭绝人的一切欲望。从理学家对佛教禁欲主义的批评,对合理客观物质欲望的肯定来看,理学家的本意不会是“以理杀人”。但“存天理,去人欲”思想流传到明清时期,由于自身理论的局限以及为统治阶级所曲解利用,产生了对民众客观物质欲望的抑制、对女性的过分约束、对社会经济和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阻碍以及对封建专制主义的固化等流弊,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因此,对宋代理学“存天理,去人欲”思想及其影响应当一分为二地看待,这一思想的提出,既存在着应该克服和批判的流弊与消极影响,又有其产生的必然性和积极的社会作用,对于保存和发扬在“天理”内涵中蕴藏着的中华民族精神具有重要意义,而存理去欲与重义轻利、尊公轻私在逻辑上是一致的,所以不应全然否定。
以史为鉴,古为今用,需要我们更好地挖掘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联系当今现实,在某些领域出现了道德失范、私欲膨胀的现象,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也正影响着一些人的价值观。宋代理学“存天理,去人欲”的理欲观倡导以理节欲、尊公轻私、重义轻利,其合理内核转化到现代社会中,可发挥其独特的现代价值,正如陈来先生所说:“在任何社会,被社会肯定为正面原则的伦理价值体系中,‘理’总是对于‘欲’有优先性,而鼓吹感性法则的主张永远不会成为一个伟大民族的精神传统。”(陈来,第8页)
来源:《哲学研究》2019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