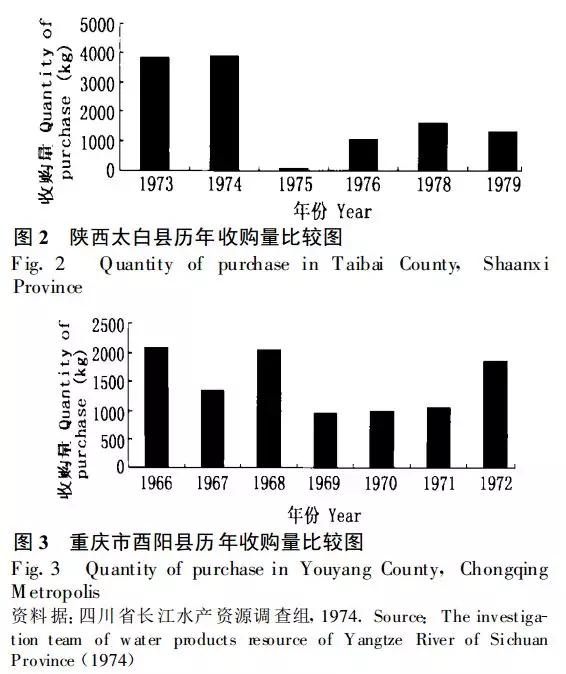“德国的欧洲”与“欧洲的德国”是1953年德国著名作家托马斯·曼(Thomas Mann)向汉堡大学生发表演讲时提出的概念,至今历久弥新、长盛不衰。不要一个“德国的欧洲”,就是不做欧洲的主宰者和教师爷;而要一个“欧洲的德国”,就是要立足欧洲、携手欧洲和自觉服务于统一的欧洲。[1]2012年,在中德建交40周年之际,笔者以此为题发表纪念文章,系统阐述了德国在欧洲乃至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德国的欧洲”是一种客观存在,从历史到现今的国际关系发展来看都是如此。无论德国处于怎样状态,是分裂割据还是实现统一,是主观上大打出手的“权力强暴”还是客观上受制于人的“权力忘却”,德国一直或隐或现地构成对欧洲乃至世界格局的冲击势力。

二、“欧洲困境”及其化解尝试
(一)“欧洲困境”的意涵与解析
什么是“欧洲困境”?这既是一个现实问题,也是一个理论问题。从现实层面来看,“欧洲困境”同欧洲整合的哲学与德国处境的悖论相通。简言之,就是欧洲既需要、同时又不愿接受甚至拒绝德国的主导作用。这在欧债危机中表现尤为突出:一方面欧盟或欧元区成员国急需德国出手相助,另一方面又不能容忍德国的领袖地位。前述欧洲国家对默克尔政策的批评充分说明这一点。总之,问题主要不在德国,而更是一种欧洲的困境。鉴于德国与欧洲紧密交织,难以剥离,因此,“欧洲困境”投射到德国身上,形成“德国问题”好似仍未解决的表象。
如何化解“欧洲困境”?德国的资深政治家施密特曾以90多岁高龄、坐着轮椅发表讲话,谆谆教导德国人民“要立足、携手和服务于欧洲”。[26]不少学者也呼吁德国人要更多显示“指尖上敏觉”(Fingerspitzengefühl),多从别国人民的角度出发去思考解决问题。德国高姿态固然能弱化矛盾,但却不能彻底化解欧洲对于德国强势地位的承受问题,必须独辟蹊径,寻觅化解之道。笔者以为,“欧洲困境”更是一种欧洲一体化的理论困境,涉及欧盟性质及其发展的终极目标问题。
欧洲一体化理论流派林立、观点繁多。总体而言,涉及欧盟性质或发展的终极目标主要有两大主义,即“超国家主义”与“政府间主义”。前者指向欧洲联邦,需要转让国家主权,形成新的权力中心;后者指向欧洲邦联,无须转让国家主权,而是维系和发展成员国政府之间的合作。无论左右两端,或是游移其间的诸多其他理论假说或杂糅,归根结底均将“国家主权”作为至高无上的原则。
从欧洲一体化既有理论的层面透视欧债危机,不难看出,欧洲整合已经陷入一种理论死角,无论超国家主义或政府间主义等传统理论概念与框架,都无法提供令人满意的解脱危机方案。假如向前,即向超国家一体化的方向迈进,欧元区国家就要在结成货币联盟以后,还要在其他更多领域(譬如财政、税收、社会等领域)转让主权,以解决结构性缺陷问题;假如退后,即朝政府间合作的一体化目标举步,像在外交、安全与防务政策领域那样,将意味着某些危机国家退出欧元区,甚或解散货币联盟,重新回到德国马克、法国法郎、意大利里拉等民族国家货币的时代。
这些方案与倡议都在应对欧债危机中登台亮相过。问题是:具有超国家性质的欧洲货币联盟已经彰显德国的强势地位,欧洲整合进展没能增强欧洲在世界中的政治分量,相反却在销蚀其世界影响力。另外,货币联盟已经显现欧洲分裂的危情,不是经冷战时期的“铁幕”,而是沿欧元区的边界,形成欧元区与非欧元区、债务国与债权国的对垒。那么,后退到政府间主义合作时代、解散欧元区是否更为可行?结果只能更糟,因为德国将再次滑向“德意志特殊道路”,而这恰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欧洲历史反复出现、并给欧洲和德国自身带来巨大灾难的决定因素,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吸取历史教训、开启与发展一体化事业的直接诱因。欧洲一体化既是“接纳”,同时也是“框住”德国从而形塑一个“欧洲的德国”的工程。
由于现有理论均不能令人满意地解决现实问题,世人已经看到德国在欧债危机中手足无措、左右难以逢源的尴尬局面,即“欧洲困境”的投射。那么,有否一种非左非右的中庸之道,以解欧洲与德国之困?德国历史学家多米尼克·盖佩特(Dominik Geppert)曾经做过这方面尝试。着眼于“欧洲各国无论在传统、思维方式和利益等方面都差异巨大”的现实,他提出一种灵活多样的“横向”联合,而不是一以贯之的“纵向”统制的欧盟发展新模式,该模式高于自由贸易区,但也并非走向欧洲联邦或合众国。在他看来,这种非集权的、亦包括众多非欧元区国家的广而松的欧盟好处多多:可以中和或摊薄德国强势地位,有助于加强同英国及欧美关系的发展等。[27]
这种灵活多样的横向联合发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欧洲困境”,但仍未解决欧洲一体化理论的深层次问题,即欧盟的性质与终极目标问题。它虽避免从超国家主义到政府间主义的理论光谱上定位两极,但仍囿于传统思维定势,没有突破以“国家主权”原则为指导的欧洲一体化理论框架。
(二)欧洲联盟性质与终极目标释疑
什么是欧盟的性质或其发展的终极目标?长久以来,欧洲无论政客还是学者多在回避这一问题。2000年5月,德国外长约什卡·费舍尔(Joschka Fischer)在柏林洪堡大学发表关于欧洲一体化终极目标的讲话,提出建立欧洲联邦的愿景,[28]但并未在欧洲赢得积极反响。后有学者干脆指出,欧洲一体化是一个没有目标的过程。[29]为何呈现此种情景暂且不表,仅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一体化60多年的发展历程来看,让人上车,却不告知这是何车,开往何处,终究会出危险;英国人闹着要刹车下车,说明这一点。欧债危机中凸显的“欧洲困境”折射出的“德国困境”同样说明这一点。
对于欧盟的性质,中国曾有学者指出,欧洲联盟“就其实质而言,是一个具有联邦、邦联和国际组织混合特征、高度发展的、主权国家的经济一体化和政治合作的实体。[30]这种解释颇为周全,但主要是将欧盟的各种表征杂糅一起,没有突破旧有的理论。这里尝试一种新的解释,即欧洲联盟是一种奉行“辅助性原则”的“国家联盟”,区别于迄今为止世界上所有的宪制政体,古今中外独一无二。这种特质既是欧盟的性质,也是欧盟发展的终极目标。本文对有关欧盟的“未定性”“不成熟”“过渡期”等看法持否定态度。
“国家联盟”(Staatenverbund)是一个新创造的德语复合词,由“复数的国家”(Staaten)与“联盟”(Verbund)两个独立词语相加而成,其创造者是德国著名法学家、多年担任联邦宪法法院法官的保尔·基希霍夫(Paul Kirchhof),[31]在英语等其他语种中没有相应的表述。这个复合词的最大优点是整合了欧盟自身已有的超国家主义与政府间主义两大属性,“Union”一词无法体现这一点。
一方面,“复数的国家”及其利益是欧盟发展的出发点与落脚点。欧盟仅为一种在某些领域主权共享的超级权力(superpower),而非一个新式超级大国(superstate)。欧洲国家大多不愿放弃其国家主权,沦为一个欧洲联邦(或曰合众国)的邦/州/省。《里斯本条约》将《欧盟宪法条约》中所有可能刺激人们主权敏感神经的表述如“宪法”“联盟外交部长”“联盟的标志”等一并去除,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32]欧盟28个成员国无论大小强弱一律平等,体现在欧盟决策内容与程序的原则与规范上。欧盟政治系统通过条约组织起来,与民族国家经宪法立国完全不同,其决策内容的原则与规范是必须在条约规定的范围以内。欧盟成员国经过会商与谈判确定条约的目标、任务与限制条件,“联盟的目标应依照本条约的规定,根据本条约所提出的条件……予以实现”。[33]这一联盟目标可以与时俱进地加以修订,但必须经过欧盟全体成员国一致同意,甚至要经成员国政府和议会批准。[34]由欧盟成员国的国家与政府首脑组成的“欧洲理事会”仍然奉行“全体一致通过”的决策程序。另一方面,复合词第二部分“联盟”又意味着欧盟必须“具有共同行动的能力”。[35]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在决策程序上采用多数表决制,是为联盟超国家性的根本体现。“欧盟委员会”的决策方式系多数表决制,“部长理事会”也在愈来愈多的政策领域采用多数表决制。总之,“国家联盟”作为定性欧盟的概念尽管还不广为人知,但它比较准确地反映了欧盟的特质。
比“国家联盟”更能体现欧盟特质的是“辅助性原则”的确立,1993年11月1日生效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将此原则纳入其中。“辅助性原则”的本来意义与天主教的宗教社会学相通,主张只要个体或小社会团体有能力,就应由他们承担责任和完成任务,大社会团体或国家不要干预,除非个体或小社会团体不能解决问题之时。这一原则运用到欧盟意味着:只有当欧盟成员国不能足够承担某项任务,且只有欧盟介入才能更好地完成该项任务时,欧洲联盟才能介入与参与。[36]
“辅助性原则”的实施主要体现在两项具体规定中:一是成员国可以通过个别授权,向联盟转让部分主权;[37]二是联盟将以“共有方式”行使成员国转让出来的那部分权能。[38]这是一种新宪政原则,其法理基础和主导原则已经不是“国家主权”,而是“辅助性原则”。这是对欧盟成员国同联盟之间相互关系极有特色的表述,是一种纵向的分权方式。
这种纵向分权的宪政方式根本迥异于国家,不是“自上而下”而是“自下而上”;不是个体服从整体,地方服从中央,而是正相反:个体向整体授权,整体只能在这些被授权领域,以共有方式行使职权。这时,权力的流动是“自下而上”而不是“自上而下”,权力的行使需要受到成员国的监控。这说明,欧盟宪政的真正主人,不是联盟而是其成员国。[39]假如成员国愿意,可以随时退出欧盟,一旦主意改变,还可根据欧盟法律程序再次申请加入联盟。[40]总之,无论是在某一领域实行超国家的整合,还是继续保留政府间的合作,均由成员国说了算。
这种宪政安排自1648年《威斯特法利亚和约》签订以来从未有过,是独一无二的全新体制。德国政治学教授赫尔穆特·瓦格纳(Helmut Wagner)已将“辅助性原则”的确立视为国际关系划时代转折的标志。[41]对于这种高度的解读是否认同,可以进一步讨论,这里只想强调一点,欧盟的这种奉行“辅助性原则”的“国家联盟”性质已定,人们长久以来缄默不提或含糊其辞的欧盟发展终极目标问题也已解决。
(三)欧洲联盟“辅助性原则”的意蕴
欧盟奉行的“辅助性原则”是否行将取代自《威斯特法利亚和约》签订以来主导国际关系的“国家主权原则”,不是这里讨论的问题。它对欧盟乃至世界政治发展意蕴重要的内涵却值得深度挖掘,主要包含三个层面:(1)自愿性。这是“辅助性原则”的核心,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区域整合的特点即“共同协议建构欧洲”相辅相成。假如是强迫,那就等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欧洲历史上出现过的帝国征服与霸权统治了;[42](2)互助性。这意味着假如个体、低层级单位无力完成或做好某事时,团体、高层级单位就要施以援手。譬如,在欧债危机中。希腊、西班牙等南欧国家无力单独攻坚克难,这时欧盟就应介入,扶助危机国家战胜困难。这就是辅助性原则的精神;[43](3)功能性。辅助性原则的操作意义,或曰衡量的尺度是功能性,即看哪个层级的主体可以最好地履行职责、完成任务。例如,环境保护目标已经不能仅仅限于个体、低层级单位或国家,而必须在更高更广的区域直至世界层级通过合作共治才能实现。当然,在现实生活中,指导人们行为的并非完全是理性,还有其他重要因素在起作用,譬如,在外交、安全与防务政策领域,欧盟单个国家在全球化的世界中已经难以特立独行,然而,欧盟还未在这方面进行超国家的整合。只要还有一个成员国(如英国等)反对,欧盟在该领域就无法实现超国家的整合。
“辅助性原则”尽管(至少在中国)还不为人所熟识,对它的一些解读却已明显反映出一定程度的偏差。譬如,中国的欧洲研究学者曾经认为:“辅助性原则体现了欧盟与成员国分权的原则,实际上为欧盟在政治上走向联邦制确定了指导思想和法律基础。”[44]这一理解仍然受到自1648年以来占国际关系主导地位的“国家主权原则”影响,将欧洲联邦作为终极目标,归根结底还是一种旧的、传统性的而非新的、替代性的解释。
类似解读还可在对《里斯本条约》的介绍与评析文章中遇到,其中比较典型的有以下两种:一是欧盟“改革不彻底”;[45]二是欧盟“发展不成熟”。[46]什么叫“改革彻底”,“发展成熟”的标志又是什么?从文章中不难悟出,就是指欧盟成员国完全转让主权,特别是在外交与安全领域,成立欧洲联邦。显然,这同上述对“辅助性原则”的解读异曲同工,也是在“主权原则”导引下的传统思维定势中打转。问题是欧盟自己不愿成为国家,大多数欧盟成员国也认为根本不应这样做。
德国政治学教授瓦格纳指出,欧盟宪制的创新与魅力在于,即使没有“国家主权”,也能自行决定其职权,这就是“辅助性原则”的确立与运用。该原则被欧盟“发明”与“提升”为宪政原则,不是刻意的理论构想和政治举措,而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情势反应。这种情势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解决“德国问题”而建立欧洲煤钢联营,将作为战争物资的德国煤钢产业从“外来的管制”转成“共同的管制”,为此建立的“高级机构”(即欧盟委员会前身)遂一开始就有超国家性。这一将国家某一领域职权“共同体化”的程序成为先例,为后人所效仿,并且进一步衍生开来、发扬光大,最终作为约束性条款在条约中得以确定。[47]可以想见,差之分毫将失之千里,假使没有法、德两国1950年在煤钢领域将国家职权“共同体化”的大胆举措并得到其他西欧国家支持,欧洲煤钢联营的一体化胚胎不可能发育成长,欧盟也未必会有今日的骄人成就。
中国学者对欧盟奉行“辅助性原则”的理解出现某些偏差,情有可原,毕竟它属西方文化范畴,东方人对它尚感陌生。然而,若是欧洲学者特别是对该原则的释义做出划时代的创新性理论贡献的瓦格纳教授,也间或在其论述中谈起欧盟发展的“未成熟”“未定性”等,就令人费解了。这种现象出现在有关对欧盟民主合法性的讨论中。瓦格纳首先对诸多否定欧盟具有民主合法性的观点提出质疑,[48]指出,假如民主的衡量标准就是是否存在“一国人民”或“一国人民的直接统治”,这个世界就毫无民主可言。真正在地球上广为实施的是间接式代议民主,直接式全民公决(瑞士除外)此时只具辅助作用。从此意义上说,只要欧盟成员国政府均系各国人民选举产生,欧盟成员国共同形成主权,就是一种新的、基于两轮选举的民主形式。瓦格纳的结论是:欧盟是民主宪政集大成者,包括“直接民主”(如许多国家实施全民公决)“间接民主”(如议会制或总统制的代议制民主)和“欧盟的二元代议制民主”三种形式,这三种形式均同“辅助性原则”相关。[49]
显然,瓦格纳认为奉行“辅助性原则”的欧盟已经具有民主合法性,反对所谓欧盟“未成熟”“未定性”等看法。换言之,欧盟不必“成熟”“定型”到出现“欧洲人民”那一天,假如这一天永难到来,欧盟也就永远无法具有民主合法性?!这已反映出瓦格纳对“辅助性原则”理论辨析的彻底性,只不过,这种彻底性没有贯穿其文始终。譬如,他在阐述欧盟主权债务危机的根源时,竟提出欧盟结构的“未定性”(Unfertigkeit)是始作俑者。[50]另外,在论述欧盟作为国际关系行为体缺失效力的原因时,他认为不是欧盟与生俱来的缺点,而是欧盟的“未定性”“未成年”(Unmündigkeit)和“未竟性”(Unvollendetheit)使然。[51]这一文章上下自相矛盾、立论前后难圆其说的问题,缘由何在?也许“辅助性原则”自身就含蕴一种理论陷阱,抑或人们习惯于立法、行政、司法的“横向分权”,对辅助性原则的“纵向分权”问题还少认知。无论如何,需要强调的是,作为“奉行辅助性原则的国家联盟”,欧盟的性质与终极目标问题已经解决,上述“欧洲困境”及其折射出的“德国困境”也已化解。
三、“欧洲的德国”主导作用的发挥
(一)德国主导作用发挥的条件
“欧洲的德国”主导作用是指一种同德国在欧盟与国际政治中的分量,以及其他国家对德国期待[52]相适应的作用,其发挥主要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欧洲困境”的消除,二是德国主观参与和塑造意志的形成。第一个条件已经具备,对德国产生了积极影响。谨慎乐观而言,第二个条件也已形成,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欧洲的德国”主导作用已经具备法理基础。1990年10月3日德国统一,特别是1991年12月9日《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订以后,德国于1992年12月21日通过法律,将新修订的《基本法》第23条正式纳入宪法,新23条规定,德国致力于欧洲联盟发展,为此奉行“辅助性原则”。[53]至此,致力于欧洲整合事业并为此奉行“辅助性原则”已经成为国家层面的宪法目标,这是德国对欧洲一体化进入欧洲联盟质的飞跃发展新阶段的反应。[54]
从政策实践上看,在欧洲一体化具体问题的处理上,德国注意同其他伙伴国家特别是法国、波兰等国的合作,以及德、法、波“魏玛三角”机制的使用。这在应对“欧债危机”及“乌克兰危机”中得到反映。譬如,德国总理默克尔曾力主建立对银行业的监管机制,利用欧盟《里斯本条约》的“强化合作”条款,争取了至少九个成员国的支持,成立了“欧洲银行监管局”(Europische Bankenaufsichtsbehrde,EBA,2011年1月1日),这是为应对欧债危机取得的重要成果之一。2011年11月28日,波兰外长西科尔斯基(Radoslaw Sikorski)在柏林发表演讲,称德国是欧洲不可或缺的国家,应该承担起领导责任,不是主宰与统治,而是领导欧洲进行改革。这话从波兰外长口中说出,意义十分深远。[55]
在应对2013年末以来持续发酵的“乌克兰危机”中,“魏玛三角”机制发挥了作用。尤其是德法两国领导人默克尔总理和奥朗德总统的联合行动,无论是直接同俄国总统普京对话,还是在俄乌两国领导人之间(普京与波罗申科)进行调停等,都为化解危机、力争用政治与外交手段解决危机做出了贡献。
如果说德国外交政策中的“克制文化”由于历史原因而根深蒂固,至少在2013年底德国新大联合政府上台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正如文章篇首所述,德国政治精英已向国际社会发出明确信号:“克制文化”不等于无所作为和等待观望,德国外交政策将更具积极性、全球性和进取性等。在此情境下,德国如何应对新时期外交政策的挑战是世人所关注的。
(二)德国新时期面临的外交政策挑战与应对
具体来说,德国新时期外交政策面临三个方面重大挑战:一是巩固欧盟,欧债危机使欧盟遭受重创、国际影响力下降,必须下大气力重建人们对欧盟的信心;二是积极奉行全球秩序政策,应对多极化世界的变化,加强多边合作;三是致力于国际热点问题解决与危机处理,譬如伊朗、巴以、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等问题,应对“乌克兰危机”是最直接的任务。[56]上述三个方面的外交政策任务直接涉及德国对法、美、俄、中国等重要国家的关系。
德法和解与合作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一体化发展的决定因素,今后仍将如此。德国在欧盟发挥主导作用,不能没有法国的(政治)配合与支持,正如过去几十年法国领导欧洲整合不能缺少德国的(经济)配合与支持一样。正是在此意义上,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Frank-Walter Steinmeier)就职以后,旋即同法国外长法比尤斯(Laurent Fabius)发表共同声明(2014年1月21日),就强化两国合作达成一系列具体协议,如在欧盟部长理事会召开之前协调立场、就预防冲突和危机早期识别等密切接触等。[57]然而,德国统一以后,德法关系从此前的“不平等但是均衡的关系”转为此后的“平等但是失衡的关系”,是为一种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如何驾驭及效果如何,将是影响欧盟整合与发展的重要因素。
“乌克兰危机”是冷战结束以后德国面临的最严峻考验,其规模与影响完全能将过去25年间建立起来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体系完全或部分地摧毁,德俄战略伙伴关系亦会受到威胁。[58]德国的有识之士看到:冷战后建立全欧安全秩序的目标没能实现,原因在于没有把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ECD)作为基础,致力于“整体欧洲”(gesamt-europisch)的新安全体系建设,而是热衷于搞“局部欧洲”(teil europisch)的北约和欧盟持续东扩。建设欧安体系必须与俄合作,不能没有、绕过甚或针对俄罗斯,只有同俄紧密联系才能加强欧洲在多极化世界中的影响。[59]
问题是,德国如何克服或至少摆平一种结构上的矛盾关系:一方面,德国是冷战结束的最大受益者,避免欧洲重蹈冷战时期地缘政治对立与冲突覆辙,是德国根本的国家利益之所在;另一方面,德国是北约重要成员国,保持与发展同美国牢固的同盟关系是德国1949年建国以后至今“自由、安全与福利的关键”。[60]然而,强化大西洋联盟,势必影响对俄关系改善;致力于“整体欧洲”建设,美国与北约的作用又会被边缘化。“欧洲的德国”如何在政治理性与盟国义务之间权衡与抉择,对欧洲乃至世界格局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德国意欲在飞速发展的多极化世界中积极参与塑造全球秩序,同样面临诸多考验。譬如,为了应对全球化挑战,德国需要加强同新崛起大国如中国的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但与此同时又将中国视为危险的竞争者,认为德国与欧盟在非洲、拉美或中亚的传统伙伴正在愈来愈向中国或其他崛起大国靠拢,有损德国的利益,等等。[61]对于中德关系,笔者曾在2007年撰文提出并至今仍然坚持“中德天然盟友关系”(Natürliche Partnerschaftsbeziehung)的看法,[62]认为一个置身于“奉行辅助性原则的国家联盟”之中的“欧洲的德国”,同一个坚持改革开放的“亚洲的中国”加强合作,可以为世界的稳定、均衡与可持续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总之,在“欧洲的德国”原则框架中发挥“德国的欧洲”主导作用,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仍然面临诸多对法、美、俄、中国等重要国家关系中棘手的结构性矛盾。这些挑战是否或能否刺激欧盟在外交与安全政策领域进一步迈向深度整合,尚未可知。无论如何,至少从理论上看,“欧洲困境”已经解决,欧盟已经发展成为奉行“辅助性原则”的国家联盟,是为古今中外全新的一种宪政体制。它不是以近四百年来盛行国际关系中的“主权原则”,而是以写入1993生效的《马约》的“辅助性原则”为主导;展现给世人的不是“联邦”(Bundesstaat)或“邦联”(Staatenbund),而是将超国家主义与政府间主义杂糅而成的“国家联盟”。这就是欧盟的性质及其发展的终极目标。统一的德国已经将致力于欧洲整合和奉行“辅助性原则”提升为宪法目标并予以践行。这些认识,对于厘清目前有关德国与欧洲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或许能够提供一定的帮助。
来源: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