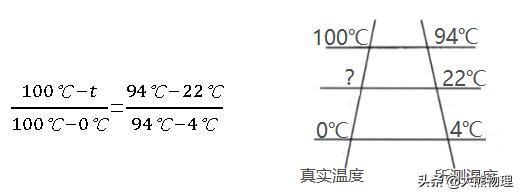看过张爱玲小说的人都知道,她的作品鲜有花好月圆式的结尾,《倾城》算是比较稀罕的一个。
“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流苏并不觉得她在历史上的地位有什么微妙之点。她只是笑吟吟的站起身来,将蚊烟香盘踢到桌子底下去。”
然而,这个结尾并不是单纯的欢喜,还有很多意味。
流苏为什么要笑?这个笑为什么放到最后——结婚之后?

陈数和黄觉主演的《倾城之恋》电视剧,跟原著同名不同款,一派皆大欢喜的景象,跳脱得完全没有张
流苏作为一个有失败婚姻经历的女人,年龄也到了二十八,能得到高富帅的垂青那是上辈子积德,还敢奢求何其多。
很多人是这么认为的。
这个结局传递了一个信息,就是如果范柳原和流苏终究没有结婚,就算保持了你侬我侬、如胶似漆的情侣关系,流苏的人生也是不完满的 。
相爱不就很好了吗?为何一定要结婚才能获得满足?
这是范柳原与流苏的拉锯中给出的态度,跟很多不愿意步入婚姻的人一样。
范柳原说:
“‘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我看那是最悲哀的一首诗,生与死与离别,都是大事,不由我们支配的。比起外界的力量,我们人是多么小,多么小!可是我们偏要说:‘我永远和你在一起;我们一生一世都别离开。’——好像我们自己做得了主似的!”
人生中的生离死别,我们自己真的做不了主吗?

首先,至少可以对彼此的婚姻做主。
也就是对“生死离别”中的“离别”与否做主。
流苏说就连她一个女子之身都能“初嫁从亲再嫁由身”,范柳原家中已经没有长辈,经济大权也紧握手中,谁能在他婚姻决定中说个“不”字?
只要他愿意,他想娶谁便是谁,他后半辈子想跟谁一起过就跟谁一起过。

但是他们所指的“做主”不在同一个频道上,范柳原说的身外之事,环境、命运或者其他不可测之事,它们会让人事与愿违。
流苏装作听不懂,但是心里明白得很,范是在逃避,逃避对爱人作出承诺、逃避担上两性关系的责任。
女人往往潜意识是知道的,在自己活着的几十年光阴里哪里会有天荒地老、海枯石烂,但是就喜欢听男人的承诺和誓言,因为那是在表达他感情上的恳切,表达他愿意负责到底的决心。
范反复表白说他爱流苏,但是唯独不愿意在爱上面加一个责任。

是的,我们无法把握命运的走向,无法知道哪天刮台风、哪天下冰雹、哪天炮弹掉到谁的身上,但至少在我们活着的时候能对自己的态度做主,是在一起还是形同陌路,任君选择。
流苏觉得,用婚姻去牵制,用爱情去维系,能最大程度让事情朝着自己的愿望方向走去,也是最大程度地用做主去应对无法做主之事。

其次,可以对逃离或者相依的选择做主。
在范明确结婚之后,他还重提了一次:
“现在你可该相信了:‘死生契阔’,我们自己哪儿做得了主?轰炸的时候,一个不巧——”
流苏很气恼,说道:“都到了这个时候了,你还说做不了主。”
事实上,范柳原早就做了主。
在全城炮声轰轰的时候,他做对自己的行程做了主:没有因为香港沦陷而逃之夭夭,而是在危险指数极高的环境中开着车往一个方向赶,不为生意兴隆不为前程似锦只为一个普通的女人无处可依,无人可托。

在找到这个女人之后,他又对自己的生活做了主:没有像之前那样养尊处优、高高在上,而是化身为最普通的丈夫角色,在人间烟火中计较一日三餐。
也许,范若没有赶到小屋去接上流苏,她就真的炸死了,或者饿死了,或者因为恐惧、绝望而崩溃了,但是因为他的选择,流苏得以幸存。
因为努力,因为做主,生死离别得以暂缓或者改期,人定胜天,总有时候。
最后他还做主了登报结婚,让那个女人得偿所愿。

一方面,范柳原用“不能做主”给自己一个完美的借口。
因着种种客观事实,范对流苏抱有怀疑。
柳原道:“我不至于那么糊涂,我犯不着花了钱娶一个对我毫无感情的人来管束我。那太不公平了。对于你那也不公平。噢,也许你不在乎。根本你以为婚姻就是长期的卖淫——”
他认为流苏吊着自己,无非想要名分,根本不存在情爱,而嫁给他更是为了长期利益。

因为摆在她眼前的现实很残酷:年龄不小,青春将逝,前夫已离,娘家嫌弃,身无长物,不学无术。
再嫁,或者说,再找个长期饭票,几乎是白小姐唯一的选择,也是非常迫切的需要,因为说不定哪天年迈的老娘两脚一蹬,那一窝尖酸刻薄的哥哥嫂嫂分分钟要把她卖到哪个旮旯。
范用理性去分析,推测流苏心理的不单纯、香港之行的功利性,但是他又抵挡不住心中的欲望,就像狐狸围着陷阱里的那只鸡兜兜转转,不下手也不放手。
但是作为一个男人,他又必须为自己令人费解的行为找个借口,而“不能做主”的理论简直量身定做,应对其时乱世的背景再合适不过了。
这是自私的人性,也是矛盾的人性,既要精神富足,但是又否定精神的存在。
更是爱得不够深切,不会设身处地理解对方的感受,也没有细细去发现情爱早已在那里。

另一方面,他相信“不能做主”。
范柳原反复强调这句话,多多少少心里是真的这么认为的。
他在相亲宴会上第一眼看中了白流苏,动用很多人力物力把流苏“骗”到香港,但是到了香港,他却君子风度的很,日日陪她游玩吃喝,却不越雷池半步。
“你不爱我,你有什么办法,你做得了什么?”

他觉得白流苏不爱他,所以才做不到情到深处水到渠成,他更觉得白流苏不够爱他,自己拿她没办法。
他喜欢把原因推到客观因素上,这样就可以把自己摘得一干二净:我们不能在一起,主要是因为你啊!
彼时世界又那么纷乱,说不定哪天时局又变了,他不再是他,她也不是她,或者世界已经没有她与他。
既然你的心意如此暧昧,今朝有酒今朝醉便好;既然人生有那么多的不可控,我何必要给自己套上婚姻枷锁!
范柳原却不明白用吃掉糖衣扔掉炸弹的心机去碰触爱情开出的小花,又如何能收获它的芳香和温柔?

首先是流苏。
在第一次香港之行,流苏死守着自己的原则,面对范柳原给予的情欲和物欲诱惑表现得云淡风轻,一脸的傲娇写满了自己的声明:要么你爽快地把我娶回家,要么咱们就不要浪费时间了。
本着“做主”的信念,有那么一会她觉得自己还挺是回事的。
然而人心不是纯净物而是混合物,流苏的心既有现实也有浪漫。
她心底也有爱的成分,在别人眼中的作态其实只是对自己的一个希望罢了,希望在这份爱的基础上能少一点卑微,多一点尊严。

婚姻对于她真的很重要,从名分上说,能挺直腰杆,自己就是范太太;从未来处境来说,就算范柳原最终厌弃了她,她还能得到一份养活自己的财产,这是受到法律保护的。
更别说,婚姻就像一座房子,就算要拆也要假以时日、耗费心力的,而在还没拆完的过程中,有时候它还能遮蔽风雨,那何尝不也是日子啊。
但是,她终究无法对自己做主。
这一趟,她早失去了上一次的愉快的冒险的感觉,她失败了。固然,人人是喜欢被屈服的,但是那只限于某种范围内。如果她是纯粹为范柳原的风仪与魅力所征服,那又是一说了,可是内中还掺杂着家庭的压力——最痛苦的成分。
一方面是范柳原的处心积虑,故意放出两人的“绯闻”烟雾;另一方面是那个两位嫂嫂居心叵测的造谣中伤以及其他家人的嫌弃驱赶。

当范柳原发出第二次召唤时,就连“爱惜名誉”的白老夫人都敦促流苏动身去港,流苏心里明白得很,这一去,是破釜沉舟,没有归路的。
总之,没有婚姻的保障而要长期抓住一个男人,是一件艰难的、痛苦的事,几乎是不可能的。啊,管它呢!她承认柳原是可爱的,他给她美妙的刺激,但是她跟他的目的究竟是经济上的安全。
当婚姻成为奢望的时候,流苏退而求其次,就是能得到经济上的保障和在热恋中获得情欲的刺激。
然而当战火燃烧到她所在的这座城市时,所有一切都又变得遥远了,“不能做主”真切地发生在自己身上。

望着情人决然离去的身影,望着落寞空虚的夜空,再到后来看着雨点般落下的炮弹,看着在逃亡中血肉横飞的路人,流苏那一刻觉得,脑子里完全失去了控制自己的能力。
当范柳原重新出现在她面前时,什么风光大嫁、什么衣食父母早已不记得何时计算过了,在那一刻,她的心湖清澈见底,既不为过去的不幸伤怀,也没有为前程的渺茫忧虑,她爱得很纯粹,除了挂念眼前这个男人别无其他,他不在身边的时候忧心忡忡,他在身边时又患得患失,生怕他就在自己面前死了无法承受,也生怕自己在他面前伤了或死了让他无所适从。
“炸死了你,我的故事就该完了。炸死了我,你的故事还长着呢!”“你打算替我守节么?”

再说范柳原。
范柳原第一次打脸是那封言简意赅的电报“乞来港”。
眼睛是“乞”字,哀求的意味,浓缩着他所有的思念和欲望。
这个字让我脑补了好几个情景:这位大男人在美女如云的风月场所嬉笑怒骂之间,脑中忽然闪现流苏含羞而骄傲的笑容,竟然觉得所有玉液琼浆与华丽风景皆是索然无味;午夜梦醒,他走到流苏曾经住过的房间,触摸着她睡过的床铺被褥,气味幽冷而愁肠……
这位爷肯定是犯了相思,才会那么的迫不及待,那么的毫不遮掩。
“不能做主”是唯物主义吧,但是显然这一次,范柳原是被感性主导着。
范柳原在细雨迷濛的码头上迎接她。他说她的绿色玻璃雨衣像一只瓶,又注了一句:“药瓶。”她以为他在那里讽嘲她的孱弱,然而他又附耳加了一句:“你就是医我的药。”

范柳原第二次打脸是本来可以离港的他穿过烽火烟尘来到流苏面前,把她接到避难的地方相依为命。
想当初他不知道自己有多酷,才刚从流苏的暖被窝下来就宣告一周后要去英国,还说不知道归期,一年半载也是有可能的。
流苏要求他带她一同去,他回说那是不可能的。
在炮弹没落下来的时候,流苏觉得自己就像笼子里的小鸟,不能飞,好歹有个窝;炮弹落下的时候,她连笼子都没有了。

流苏没想到一向认为人的命运不可控的范柳原会去而复返,范柳原自己可能也没理性分析过吧,不就是一个情妇吗,他都万贯家财了还怕找不到更好的么?
正如他的台词“谈恋爱时只顾着谈了没去恋”,只有真正去恋爱了才知道自己有多爱。
在那个狭小脏乱的避难之所,两人紧紧的相拥诠释了一切,他们真的渴望天长地久了。

结语:
流苏和范柳原的妥协和不妥协,是理性和感性的反复对抗,对抗的结果若是互相渗透,则是花好月圆,若是水火不相容,那只能不欢而散。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不能完全做主,也并非完全不能做主。
说到底,根本不是倾城的偶然才成全的恋,而是刚刚好遇上了对的人,既是天意也是心愿。
结尾处,白家嫂嫂也仿效流苏,与丈夫火速办起离婚,却不曾想范柳原只有一个,流苏也只有一个。
注:引用部分摘自《倾城之恋》小说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