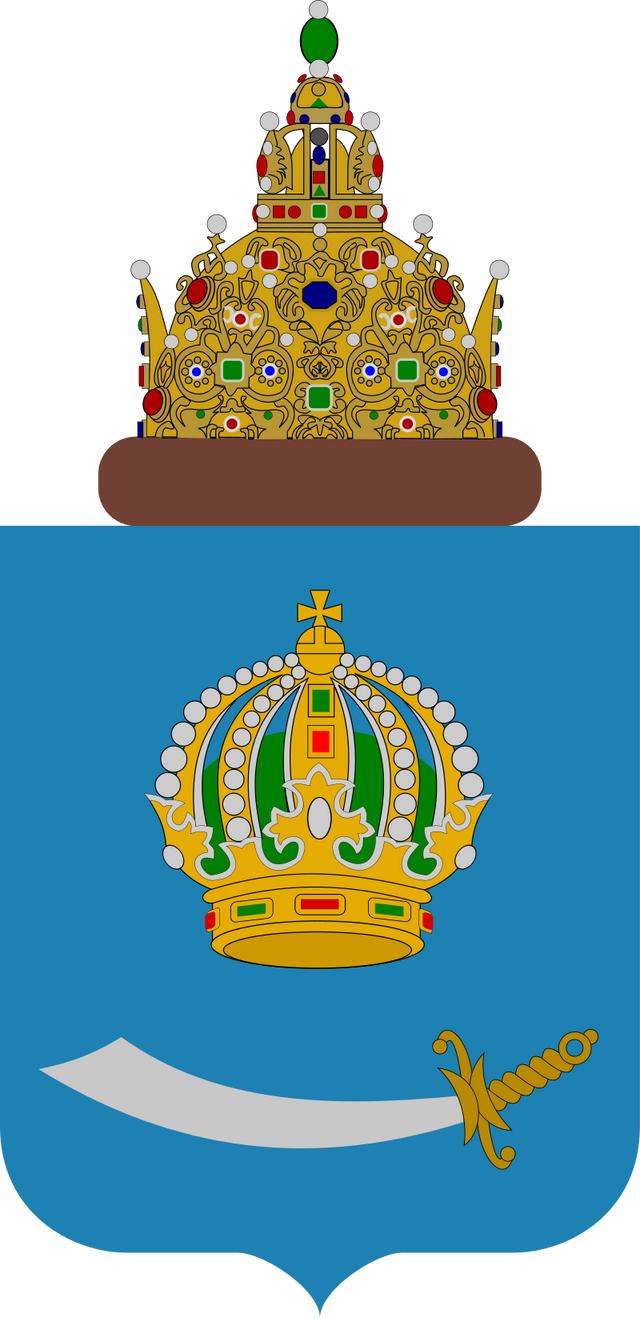来源:环球网文旅
【环球网文旅特约作者 米广弘】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少时读杜甫诗的这一联,不觉微感讶异,心想他写这首诗的时候已年过五旬,且古人寿限短晷,五十即称知天命,何言“青春作伴”呢?后来翻阅注解,才知自己愚钝,此处的青春,乃是春风和暖、青翠盈目的意思,战乱已毕,诗人要携同流寓蜀地的中原人返回家乡,又正值万物复苏的时节,自然是喜动颜色。

魅力山西 米广弘摄
读了陈师道的《和寇十一晚登白门》,其中有“小市张灯归意动,轻衫当户晚风长。孤臣白首逢新政,游子青春见故乡”两联,十分喜爱,以为诗人既然用“青春”对“白首”,那么这个“青春”该是我理解的“青春”了——至少也是双关语吧,游子羁旅之中萌生了归意,再见故乡时仍当盛年,这当然是值得高兴的事情,不料看注解还是不对,陈师道化用了杜甫的诗句,所以“青春”二字在意思上并没有什么不同。其他如钱谦益的“青春作伴更几回?紫陌看花是前度”,贝青乔的“终望桑榆收晚景,青春作伴放归航”,皆系化用杜诗,诗人赋咏之时,都已不再年轻,又迭经丧乱,所能够盼望的,也不过是在春风和暖的时节回到家乡罢了。
或许是第一印象太过深刻的缘故,尽管有了多次阅读经验,每念及“青春作伴好还乡”这句诗,还是会在有意无意间以为其中的“青春”兼有青春年少的意思,且悠悠然觉得好似有这样一种美妙情境:在正当少年时回到家乡,呼朋引类,于春暖花开之日聚饮高会,浑不知地老与天荒。似乎等到人生堆叠了沧桑的时候,回家便不是那么的轻快。然而,人总是世情浓则乡情淡,世情淡则乡情浓,到得老来,离这个热辣的世界越来越遥远,才会牵记起冥冥中的那个归宿。
读刘继庄的《广阳杂记》,有这样一段颇令唏嘘感喟:“予谓人至晚年渐归根本,此中有至理,非粗心者所能会也。予十九岁去乡井,寓吴下三十年,饮食起居与吴习,亦自忘其为北产矣。丙辰之秋,大病几死,少愈,所思者皆北味,梦寐中所见境界,无非北方幼时熟游之地,以此知汉高之思丰沛,太公之乐新丰,乃人情之至,非诬也。”刘继庄是北京人,十九岁(康熙五年)时迁至吴县定居,四十八岁病逝,其间虽偶尔返京,大体上还是在江南生活,如他所说,饮食起居乃至说话口音,都与吴地之人无异。他写下这段话时,已经“寓吴下三十年”,按时间推算,应不久于人世,一个长居异乡且已淡忘了早年生活的人,竟然在生命的最后时光如此迫切地渴望回家!
桑梓情深,落叶归根。如果把人的一生分成几个阶段的话,它们在记忆中的分量是不对等的,时间越是久远,分量越是沉重,从这个意义上,才能将“青春”与“还乡”联系起来——谁能说还乡梦的背后不是一种“归来仍是少年”的情绪在作祟呢?
所谓“近乡情怯”,于古人而言,怯的是道路梗塞,鱼雁罕通,如果发生了什么悲伤的事情,也往往只有回家见面后才知道;于今人而言,怯的却是世同时异,物是人非,不是故乡变了,而是自己不复当年,仿佛一切停留原地,等着回来。官不在高,技不在多,衣锦荣归当然令人称羡,世人记住的只有贡献,流芳后世的唯有才华,不在于地位高低,而在于眼界高下,最美好的体验便是“青春作伴好还乡”。(作者:米广弘,文化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