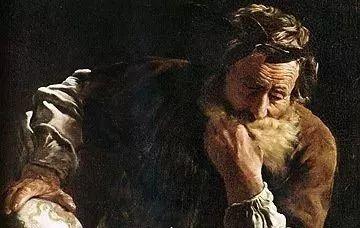早就知道李东辉这个名字。多年前,好友杨越峦就跟我说过他。说他大学毕业不到一年就因病导致双目失明,此后,就开始了文学写作。2012年春,省作协散文艺委会搞了一个大奖赛,李东辉以一篇《我没有草原,但我有过一匹马》在六千多篇参赛稿件中脱颖而出,赢得王宗仁、李晓红等评委一致好评,获得大奖赛唯一一个一等奖。也就是在这次颁奖会上,我跟他第一次见了面。
东辉眼睛不好,话却说的敞亮,舒朗。感慨之余,就想多给他点支持鼓励,我说:“以后有满意的稿子就给我……”
他笑着向我致谢,说“一定,一定。”然而,至今他也没给过我一篇稿子。偶尔在刊物上读到他的散文,愈发觉得他那篇获奖作品的确不是偶然侥幸,他的笔下确有独到之处。后来,又在几次颁奖会上见到他,算是一点点熟络起来。
前些时候,接到他的电话,说一家出版社要给他出一本集子。本以为是散文,他却说,是一本中短篇小说集。想请我给写个序。我欣然答应下来。一是愿意为他写这个序,二是想看看他的小说到底写得如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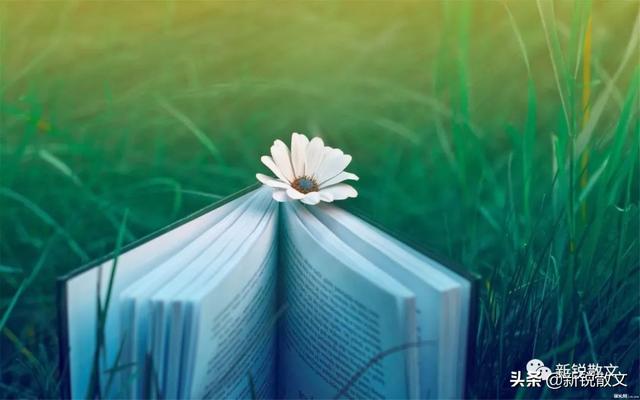
这本集子收录李东辉创作的中短篇小说15篇。其中中篇小说4部,短篇小说11篇。从写作时间上看,跨越近三十年。这正是他从青年走进中年,从光明进入黑暗的人生转折期。阅读这些作品,我们不仅从中看出他在小说创作方面的书写脉络,还可约略发现他失明以后所走过的心路历程。
通览李东辉收入这本集子的小说作品,农村题材或者叫乡村叙事占了绝大部分。这是李东辉小说写作的基调与底色。
古老的子牙河七折八弯从冀中平原上缓缓流过。稀稀密密的农家村落依傍在河两岸,河流连着村落,把岁月和岁月里的故事串在一起。
“十里湾,位于子牙河西南、东北流向转为东西流向的转弯处,在河南岸。这个村很小,不过百十户人家,虽说依傍着子牙河,却没沾上啥光,历史上就是一个穷村。解放初期,村子里搞土改,闹平分,全村居然没有一户够资格被划成地主的人家。”……(中篇小说《土屋里的女人》)
“河上有一架古老的小木桥,桥面上的青石板已被行人车马踏踩消磨出道道沟痕,岁月的风尘在桥两边的栏杆上留下斑斑驳驳的印痕。每有负重的马车,牛车从桥上走过,小木桥就吱嘎作响,尤其在寂静的夜晚。当吱嘎声响起的时候,村里少睡的老人们便在心里念叨一声“又有人赶夜路了,可要当心啊”!古老的小桥成了村里的一种象征,一个仪式。村里人送别亲人远行,总是送到桥头。他们从不陪亲人走过小桥,只是站在小桥的南头,依栏瞩望,直到亲人走到桥那头,然后转过身来,彼此招一招手,然后上路的上路,归家的归家。”(短篇小说《玍七》)

李东辉生于冀中平原,古老的子牙河流经的土地,是他生命成长的根之所在,祖祖辈辈的父老乡亲在这块土地上艰辛的劳作,顽强的生存。他们悲欢离合、命运沉浮里留下的故事与传说,成为李东辉生命记忆的源头,人生之路的开端;是他介入生活的一个角度,走向世界的一个起点。他早期的作品,我们明显看出:无论是故事情节的展开,人物性格的塑造,时代背景的投射,以及作品蕴含的命运意识,批判精神无不带有强烈的地域指向。
《土屋里的女人》是李东辉失明后创作发表的第一部中篇小说。他在小说开头题记里这样写道: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三年经济困难的最后一年,村姑马素花十九岁。她是在这年春天失的身。关于这个女人的故事也就从这里开始了。寥寥数语,就把小说的时代背景,人物身份与遭际呈现于读者面前,短短几行字,就奠定了这部小说的叙述基调,也给读者营造出一种阅读氛围。当我们读完全篇,回过头来再看题目,那座土屋,似乎成了一个象征,一种宿命。无论是母亲为了几块钱和两张白面饼断送了马素花的女儿身,还是主人公心甘情愿嫁给“肉蛋驴”王喜,给两个比她小不了几岁的两个半大小子当了后妈。无论是她为了成全王家两个儿子的婚事而委曲求全,还是她不甘受辱,与民兵连长广会的拼死抗争,无论是她跟王家老大发生的近乎乱伦的激情之恋,还是为了真爱跟先恨后爱的梁水泉出走私奔后度过的几年幸福时光。无论是改革开放后生存境遇的改变,还是她回村后成了顶仙看病的仙姑,马素花似乎始终摆脱不了冥冥之中某种力量或神秘之手的左右与掌控,最终重又回到那两间老旧的土屋。像子牙河晨昏里飘来荡去的雾气,《土屋里的女人》的书写语境,始终笼罩着一层伤感、宿命的意蕴,蕴含着李东辉某种命运意识的隐喻言说。

从某种意义上说,小说写作就是叙事写人。莫言就说,她是一个讲故事的人。讲故事就离不开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一部成功的小说的价值是通过他贡献的人物体现出来的。《土屋里的女人》就比较成功地塑造了马素花、梁水泉、文增、文林等人物形象。尤其是作品主人公马素花这个女人,作者通过对她的外貌描写,习惯动作,心理活动,处事态度以及一些细节上的刻画,使她那种隐忍而不屈服,穷困而不潦倒,为了真爱可以不顾一切,认命而不服输的性格特征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一点点凸显出来,直到最后,马素花这个女人的形象成为读者心里挥之不去又一言难尽的“!”号。
命运关照与人性解读是李东辉乡村叙事小说写作的一个明显特质。他不太讲究小说故事情节的结构铺排,很少刻意制造矛盾冲突和夸张的起伏波澜,而是把更多的笔墨集中于对人在社会环境,时代浪潮里的命运转换,善恶纠葛等方面上来。着重刻画人在命运转换、善恶纠葛中的挣扎与选择。中篇小说《出走》里的雅茹(后叫雅儒),初中毕业,美丽纯真的她,怀揣着一个作家梦,走出闭塞的乡村,到县城群艺馆做临时工。涉世未深的女孩子,挡不住物质的诱惑,在虚荣心驱使下,误入歧途,失足堕落。尔后幡然醒悟,回到农村老家。她想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她忍气吞声,她自谴诸己,默默忍受男人放肆的挑逗,村妇的冷言恶语,她低三下四的讨好同学旧友,跪地哭求恶毒的嫂子:“我过去是做了错事,给家人丢了脸,可我现在改了,我改了还不行吗……”她甚至自毁自贱,甘心嫁给一个大她十多岁的穷光棍做老婆。然而,就连这么一个被人蔑称为“老废(窝囊废)”的男人,竟也在第一次相亲的时候去扒她的衣服,雅茹不从,他竟颐指气使的骂雅茹是“破鞋,骚货,不识抬举……”
短篇小说《呜呼,金喜》里的罗锅子金喜,本来是一个人见人爱,健康聪明的孩子,却在爹妈争竞拉扯中被弄成残疾,爹妈争来争去的孩子又成了谁都不要的弃儿。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发了财,娶了一个豁嘴龅牙的女人,贪心的他到北京大医院为媳妇做了整容手术,媳妇却背叛了他,卷了他的钱跟别人私奔了。此后的金喜,再也不相信任何人,他宁可把大块大块的肉喂狗,也不肯舍一点给年关都过不去的上门求帮的年轻村妇。在他患癌将死之时,年轻的村妇来看他,他拿出两万块,说:这是还你的情分钱,拿着钱走吧,以后咱谁也不欠谁的了。就是这么一个从身体到内心都有些畸形变态的男人,死后,却把几十万块钱捐给了希望工程。而当那位村妇知道这件事,在心里恨恨的说:“这个死鬼,才给我两万块,早知道他有这么多钱,还不如当初……”诸如此类人物,是李东辉的小说作品贡献给读者的一道别致的风景。
白描手法和散文化叙事是李东辉小说写作的风格特色。文字所呈现的田园风情与内在的诗性韵味水乳交融,完成了作者写作意图的表达。

“子牙河近水岸边,生长着一片片芦苇。夏天,绿油油的芦苇又高又密,仿佛在一片片深深的绿色里隐藏着许多神奇的故事。苇丛里栖息着许多水鸟”……(短篇小说《绿鸟》)
“爷爷回到望帆台后的第二天,就和刘平上路了。他们假扮夫妻,一路西行。秋天的冀中平原,呈现出一派如诗如画的景象,处处都是一望无际的青纱帐。红的高粱,绿的玉米,黄的谷子,白的棉花,把田野点缀的特别好看,乡间的土路大道都淹没在庄稼地里,秋日的阳光暖暖地照着,如洗的蓝天飘动着朵朵白云。兵慌马乱的年月,大自然仍是一个宁静安详的世界。”(短篇小说《我本无心讲故事》)
这些文字,明显带有荷花淀派的风格。收入本书的几个短篇是李东辉系列人物小说《子牙河风情》中的选摘,无论是《绿鸟》中,四爷爷与县长千金的传奇爱情,还是描写抗战时期战争与人性的家族往事——《我本无心讲故事》。无论是《圣人心》里的怪人“大头庆”不合常理的为人处世,还是《老少爷们小写意》里几个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司空见惯,又个性鲜明的典型人物,都可从中看出“荷花淀”派含蓄内敛,清新浪漫的写作特质。
近几年,在原有写作基调中,李东辉又揉进了汪曾祺的写作风格与审美追求。散弹白描的叙述中透着浓浓的温情与人道关怀。
“先生是个女的。很年轻,二十岁上下,姓马,叫月。身材不高,但匀称,肤色白皙,这在乡下女子中是不多见的。我们那里的村姑女子大都长得比较黑,可能跟水土有关。其实,在孩子眼里,无论长得是黑是白,年轻的女先生总是美的。”(短篇小说《学堂往事》)
“玉山是个人名,姓李,一个村长起来的。都是1962年的虎,但他比我差远了,个子矮小,头大脖子细,尤其在他的头顶中间部位,有一道明显的半弧形凹痕。那是小时候被筐系子压出来的。他家成分高,穷,学校不要他,整天就是背一个跟他身高差不多的筐子去地里打草。一大筐青草,小山一般,背不起来,只好用脑袋顶着筐系子,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鸡蛋粗细的竹筐系子硬生生在他的头顶上压出了一道凹痕。只等长到十六七岁,虽然摘了富农的帽子,个子也没长起来。翘起脚,也不过一米六。”(短篇小说《我和玉山》)
贾平凹说:“写作,说到底是在写自己。”乔叶说得更直白:所有的作家都是在写自己。李东辉的写作是对这个观点的最好诠释。如果说他那些农村题材的小说是他乡村记忆的隐喻言说,子牙河是被他艺术化了的一个文学符号,他笔下的故事人物,无一不是他自己对自然社会,世道人心,人生命运的解读与表达,是他借助文学写作的言说方式抒发自己的内心情感,表达自己的生活认知与理性思考。那么,他的另一个写作领域简直就是他自己的精神心灵成长史了。

一个曾经的高考状元,一个风华正茂,春风得意的青年才俊,就在他写下“生活真好,每一天的太阳都是为我升起的时候!”上帝却看不惯他的骄狂自负了。23岁,一场大病,把他推向阴阳界的边缘地带,十八个月死去活来的折腾,病魔留下了他的生命,拿走了他的眼睛。用李东辉自己的话说:“没了眼睛,心性尚存,这是一个错误而又不可改变的安排。”要死要活的闹过之后,李东辉终于明白:上帝所以这样做,是想拿他做一个实验。上帝想看看,一个被无端拿走眼睛的人究竟会怎样?
李东辉会怎样呢?起初,他不想跟上帝玩这个游戏,曾以死相拼,没有得逞;想行尸走肉了此残生,终又于心不甘。无可奈何间,他想起了文学。他想用写作跟上帝讨论一下天堂、原罪的问题,想通过写作搞清楚命运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他试图在黑暗中看清生之来路,死之去向。
《撕裂》是李东辉完成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的一个中篇。作品主人公肖晖,一个双目失明的中年男人,妻子多情漂亮,幼子纯真可爱。然而,一时的浪漫激情,挡不住琐碎生活的消磨,曾经的海誓山盟,在物质诱惑面前不堪一击,当年非他不嫁的妻子在一个雨雪交加的日子,亦然抛子弃夫,离他而去。因为写作,肖晖有了点小名气。阴错阳差间,两个女人走进他的生活。一个是心直口快,朴实善良的出租车司机玉珍,一个是喜爱文学,年轻漂亮的大学生纪华。前者文化水平不高,直来直去,敢恨敢爱,玉珍对所谓文化人心存仰慕,真心对肖晖好,生活上照顾,钱财上帮助。如果想做柴米油盐的烟火夫妻,玉珍无疑是最佳人选。然而,偏偏还有个年轻漂亮,温柔多情的女孩子站在肖晖面前,纪华善解人意,时而风情浪漫,时而孤高矜持,纪华如诗如梦的青春气息不可阻挡地撩拨着他的心魂。于是,肖晖就在这两难选择中,在物欲与虚荣纠葛里一步步走向自我毁灭,终以自戕了断。
《撕裂》看上去是一个司空见惯的,一个男人与两个女人之间的情感故事。实际上,作者想要表达的是人的生存境遇,两个女人,实则是一种象征,一个是现实的,生活的,一个是精神的,心灵的,两种需求,如同两股相反的力,神兽之间的人,在这两股力量的作用下,就有了强烈的撕裂感。内心的矛盾重重,人格的撕裂整合,把人置于两难甚至多难选择,游走于崇高与卑微的边缘境遇之中。正如存在主义作家米兰·昆德拉所说的那样:生活永远在别处。

黑暗,蒙锁了李东辉的眼睛,他却在黑暗中看清了在阳光下看不到的真实。写作,视他为自己找到的一条自我救赎之路。
如果说《撕裂》揭示的是生命存在的困境,那么,短篇小说《清明时节》、《颤抖》、《双色苹果》等则从不同层面,不同视角表现了人性的复杂与多元,爱愿的痴迷与空渺,生命存在的悖谬与终级困惑。李东辉是一个探险者,找路人,无边的黑暗让他时刻睁大心灵的眼睛,对生活,对人生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他以写作的姿态走进自己的内心世界,走进历史的深处,走进人性的角落。他在困境与绝望中寻找着,发现着,小心而执着的为自己探索着前行的路径。
凭借写作,史铁生从自身的残疾发现了人的残疾,并以此确立了自己的生命哲学与救赎之路。同样的,凭借写作,李东辉从自身的困境发现了人的困境。他在一次获奖感言里这样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都生活在某种有形、无形的限制与困厄之中,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着一个挣脱与突围的问题。没有限制与困厄感的人生是不丰富,不完满的……”
毋庸讳言,李东辉的写作,远没达到尽善尽美的水平,存在着诸如文本过于单薄,对题材的挖掘深度不够,叙述手法单一等诸多瑕疵。但他的写作是真诚的,他对文学是满怀敬畏的,苦难没让他的生命凌乱不堪,没让他的心灵蒙污染垢,他的写作充满人道关怀,他对这个世界依然温柔以待。爱是他为自己扬起的一面旗帜!行文至此,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句话:“我只担心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苦难。”愿与东辉兄以此共勉。
2019年夏于石家庄

作者简介:李延青,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河北省作家协会巡视员、副主席。著有:《延青短篇小说集》、长篇系列散文《鲤鱼川随记》、报告文学《追踪开国英雄》、小说集《人事》。主编:《文学立场——当代作家海外、港台演讲录》;“中国学者海外演讲丛书”——《境外谈美》、《境外谈佛》、《境外谈文》;《曾国藩日记》(全本注释)等。曾获河北省“文艺振兴奖”、《小说月报》第九届百花奖、小说《匠人》入选2017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