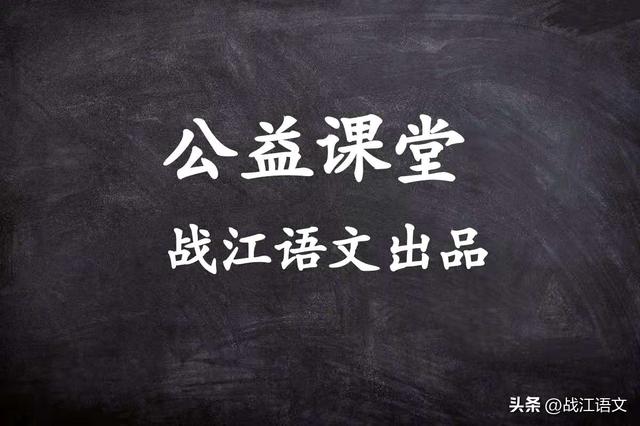1.铁匠铺子入社,家里开支捉襟见肘
我们祖上是铁匠铺子、后来我爷爷带着父亲、两个叔叔,爷四个带着打铁的家伙什,举铺并入了八义集铁木业社(1990年改名为邳县工程机械厂)。
我爷爷作为技术骨干,和儿子们、徒弟们以及其他铺子过来的工友,共同撑起了这个新兴的厂子,这个铁木业社级别还是挺高的,归属于县工业局管辖,当时属于铁饭碗。
铁木业社的位置在八义集供销社和老派出所中间,老五金店、布匹店和酱油店的对面,位置是镇中心,不过现在大部分地界已经转为他用了,几乎找寻不到当年兴盛繁荣的痕迹了。
爷四个入社之后,铁匠铺子流水的活钱没了,只有每月固定的工资,实际上的家庭收入,少了许多。
我们祖上虽然有些积蓄,但架不住家里孩子多,父辈十个兄弟姐妹,各自结婚成家后,又是生儿育女,第四代孩子越来越多,大家庭已经虚有其表了,日子过得都很紧巴。
在原来大家庭的环境里,在当时祖奶奶重男轻女的做派下,大姐从小就懂事勤快,体贴父母,帮家里干一些力所能力的活。
正如现代京剧《红灯记》中所唱的那句“提篮小卖拾煤渣,担水劈柴也靠她。里里外外一把手,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栽什么树苗结什么果,撒什么种子开什么花。”
大姐和二姐十几岁的时候,就分担了家务,承担了与年龄不相匹配的劳作,带妹妹、洗衣做饭、洗碗烧锅、扫地清洁、薅草喂兔子........街坊邻居没有不夸的,我们家当时虽然没有男孩(我当时还没有出生),但几个姐姐都特别省心。
在当时的家庭条件下,祖奶奶是不同意大姐上学的,觉得女孩迟早是要嫁人的,上不上无所谓,白花钱,可爷爷还是给她报名了。
大姐从小学习刻苦、外柔内刚、自尊心特强,小升初、初中升高中,都是过关斩将,顺风顺水,爷爷在世时一直悄悄地资助她、鼓励长孙女好好上学,盼她能鲤鱼跳龙门、考中“女状元”,给祖坟冒缕青烟。
2.分家单过
祖奶奶去世后,已结婚成家的父辈几个小家庭,就和爷爷奶奶分家过了。
我们搬离了祖宅,在东河外的圩子的宅基地上,东拼西凑,七借八借,盖了大一点的三间“较为宽敞”的土坯房,面积是原来两间矮屋的两倍多,还用多余的物料捎带盖了一间锅屋,院子是用玉米杆、棉花杆扎成了,也就防点鸡鸭猫狗跑院子里来。
我记得我们房梁上的横木,都毛笔记录着借给我家木头的培朋叔、四表叔、麻子舅等亲友的名字,房顶上的芦苇还时不时地会朝下掉,但这个房子,比我们在圩里的,真的大多了,尤其是圩外海阔天空、绿色青青,当时周围大部分都是庄稼地,我们大概是第一家住户。
我母亲从大家庭喧闹争吵的阴影中解脱了,心情十分好,一心侍弄庄家,披星戴月的,家里洗衣做饭、喂兔子喂猪、磨面糊......这些家务,统统交给了大姐带着妹妹干。
父亲当年体弱身虚、嗜好烟酒、铁厂工作之余的热情都在结网、撒鱼和酒后唱戏中,在家基本是甩手掌柜,看到大姐干得不好,还要嘟囔几句。
3.大姐上了高中
那时家庭虽然困难,有爷爷的支持,父母也不反对大姐继续上高中,大姐当然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尽可能地压缩上学开销,风雨无阻地往返于八中和家之间。
为了有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爷爷曾给大姐靠着他的土屋,收拾了一间偏屋,让她一门心思学习,免得受到家里一群弟弟妹妹叽叽喳喳的影响。
大姐感激爷爷奶奶对她的疼爱,也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每晚点着煤油灯,要看书到深夜,高中期间,她的学习成绩一直在班中名列前茅。
然而就在预考结束,准备迎接高考时(江苏省当年高考,是预考制度,先筛选一大半,剩下的高考成功的几率大增),最疼爱大姐的爷爷因浴池泡澡突发脑淤血、撒手人寰。
这噩耗沉重打击了正积极备考的大姐,在其后的时间里,她的眼前都晃动着爷爷的影子,无法精力集中地投入到紧张的复习中,白天昏昏欲睡,晚上头痛失眠,结果在七月高考中,因五分之差与大学失之交臂。
4.落榜之后的选择
落榜的大姐也曾想过复读,但复读一般要去县里,成功率高一些,爷爷去世了,一直资助她的来源没了,我们家孩子又多,填饱肚子都够呛,她也没法向父母张口,要求继续读书。
十八岁的她,面对捉襟见肘、负担沉重的家庭,含泪做出了无可挽回的决定:不再复读,拿着高中毕业证回家,分担家庭的重担!
下学半年后,父母托人给大姐认了个裁缝师傅,做了三年学徒,又帮师傅白干了一年。在四年起早贪黑学裁缝的日日夜夜,大姐很快脱颖而出,能独当一面了。
但当听说当时成绩一般的同学,复读了两三年,陆续考上大学、跳出农门后,大姐心里既羡慕、又隐隐作痛。
她默默地告诉自己:行行出状元,自己既然选择了这一行,就要认真地学下去,争取做个好裁缝,支撑这家庭,把心中的遗憾,化为培养弟弟妹妹的动力。
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家境如此,人心劲儿再高,也得接受现实,从此计议。
1988年,我小学毕业考上八中时,大姐辛苦学艺四年后,在街里终于开了一间属于自己的小店——春风裁缝店。
当年大姐裁缝出师后,选择有三个:一个是遵从师傅的意愿,继续跟师傅做活,师傅按件给开工资;二是去徐州、邳县的大服装店去打工,领取固定工资;三是自己在街里开店。
其中,第三条路风险最大,因为一个女孩子创业,当时街里还是很少见的,还有一些世俗的偏见。还有,女孩子最后还是要嫁人生子的,在苏北农村这样的环境下,真能指望一个女裁缝能顶门立户、养家糊口?
“要生存,先把泪擦干,走过去,前面是个天……从来女子做大事,九苦一分甜……”后来,我每次听到《上海一家人》这部剧的主题歌,从主角若男的身上,总能看到大姐当年的影子,虽然年代相差了50年,一个是上世纪30年代,一个是80年代,但她们同是用自己的裁缝手艺,靠辛苦劳作,支撑起了整个家庭。
那时,我父亲所在的厂子,已经濒临倒闭了,工资几年都没发了,他又嗜好烟酒、手无缚鸡之力,家里的开销用度,都是大姐带着二姐、三姐踩着缝纫机一点点赚出来的。
事非经过不知难,女子在街里开店并不容易。记得当时经常有地痞、流氓的骚扰,工商税务的各种费用,还要面对一些刁钻古怪的顾客以及同行前辈的打压,但大姐还是坚持下来了,春风裁缝店,一度成为街里做新潮衣服口碑最好的铺子。
当年,我新疆五姨家爱民表哥,当年曾来老家借读一段时间,来裁缝店玩,还帮大姐打跑了几个上门收保护费的地痞,后来看大姐这么辛苦,赚钱这么少,曾力劝大姐这么好的手艺,去新疆开个裁缝店,肯定赚钱,说那边都是做民族服装,针线粗、出活快,不还价。
我2000年去了新疆之后,爱民哥带我在富蕴县城转了几圈,指着几处豪华楼房告诉我,这些都是十几年前做裁缝的,他们那手艺,跟大姐没法比。大姐十年前,如果来新疆干裁缝,早就发财了。
新疆地方虽然偏僻,给人荒凉贫穷的感觉,但老百姓爱吃爱穿,消费水平不低,我后面连着去新疆七次后,对风土人情和消费习惯有了进一步了解,方知道爱民哥当年所言不虚。
但当时,大姐虽有赚钱养家的心思,但奔赴新疆的大胆想法,也只能想想而已。家里几个妹妹弟弟都上学,作为长姐,顶门立户,她觉得自己有理所当然的责任。
为了承担养家的这份责任,开店头几年,大姐在裁缝事业上精益求精,废寝忘食,裁剪、缝纫、锁边、熨烫......忙得不可开交,希望裁缝店早点进入正轨,以至于耽误了自己的终身大事。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