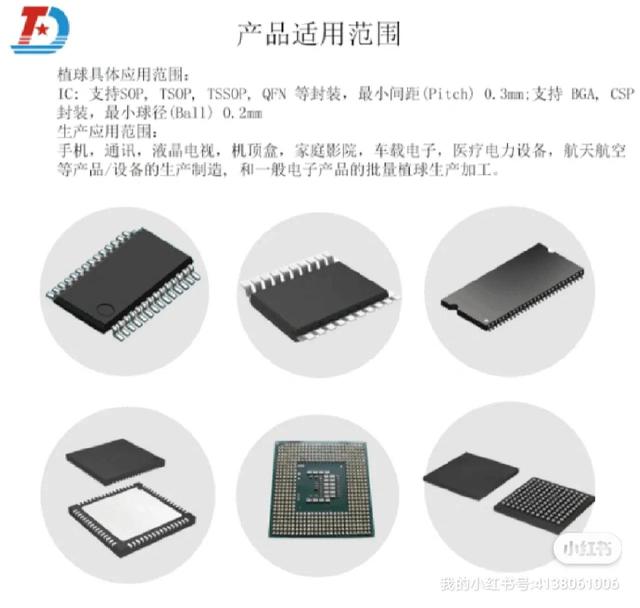澎湃新闻记者 巩汉语

黄桅 设计
【编者按】
魔都上海,都市与野性并存。在开阔与隐秘的地域,人和动物不期而遇。
居于上海的獐、貉、猕猴、胭脂鱼、震旦鸦雀,是我们的动物邻居。于上海而言,它们中有的是土著、外来客,还有的经历了从消失到重归。人类社会忙碌运转,动物邻居带来惊喜、美好与“麻烦”。
城里生活,并不简单。动物们努力适应环境,它们在小区、绿地、湿地公园默默演进,繁衍生息,寻得一席之地。
与此同时,城市努力更新。上海正布局更多人与自然亲近的空间,要累计建成20个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恢复、新建湿地和野生动物栖息地近6300余亩,给更多野生动物成为“市民”的可能。
从“园在城中”到“城在园中”,人与动物如何共享城市,上海已给出答案:“十四五”期间,构建公园城市、森林城市、湿地城市,为人与动物和谐相处探索最佳实践。更长远的目标也已规划好,到2035年,一座生态之城将基本建成。
又傻,又笨,又冷,又孤独。
我的老朋友陈珉教授常常这样描述我们獐家族,很“无语”,但好像也确实如此,我们大都独居,有点社恐,常常自闭。没办法,天性使然。
我们是著名的上海“土著”,几千年来扎根于此,却在过去百年间销声匿迹。再度“引入”,“社恐”的獐家族,不得不担负起种群延续的使命,闯荡野外,适应未知的世界。
起源远古

獐 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说起獐家族,可是“有点东西”。
我们从新石器时代一路走来,家族庞大,很长一段时间内,整个黄河流域都有我们的足迹,后来因为气候等因素变化,才逐步转移到长江流域等地。
人类和其他天敌的捕猎,给我们带来不小的生存压力,但谁让人家食物链上的位置比我们高呢,好在獐家族还是以强大的繁衍力和适应力延续至今。

颜值之一块,在我们身上一直是个迷。在古代,人类用“獐头鼠目”形容相貌丑陋,把我们跟老鼠相提并论,多少有点伤自尊。到了现代,可能因为属于鹿科,沾了“麋鹿”“梅花鹿”等鹿界高颜值代表的光,不少人上来就把我们叫做“远古精灵”,也有不少游客看到我们直夸“好可爱”。
在我们家族,“雄竞”(雄性间的竞争)是很激烈的,獠牙便是武器,“长牙如匕”,可达8cm。吃东西时,雄獐的獠牙会倒下来,避免碰坏。当你看到我们的獠牙立起时,也就预示着一场求偶大战即将上演。
我们还有很多“花名”,土麝、香獐等,被认为是最原始的鹿科动物,也是著名的食草系动物,很早就活跃在中国东部和朝鲜半岛。1870年,我们还被被引入英国,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在中国,我们被严禁猎捕。
有据可考的,我们家族最早踏足上海可能要往前追溯大约6000年,人类在青浦崧泽遗址的出土的化石中发现了獐牙。遗憾的是,大约100年前,獐种群从上海消失。直到2006年人类启动“重引入”项目,我们才回归本土。
社交恐惧患者
好吧,我摊牌了,我是重度社交恐惧患者。

前不久,陈珉带了位记者来到上海浦东华夏公园的獐园,这是一片面积近5000平方米的林地,生活着五、六十头半野放状态的獐。
陌生人的到来,让我们这个小群体有点紧张。本来倚着树休息的獐A,看到来人,慌忙跑到獐园对角线到另一头;獐B更夸张,老实卧在草丛里其实谁也看不到,但他还是应激似的跳了起来,顿时吸引全园目光;獐C大胆地站在距记者十米左右的地方,但一动不动,显然不怎么“放得开”。于是,人类不得不拿出3台望远镜来观察我们。我们可能是最“怂”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了。
“敏感且孤僻”,陈珉总是这样描述獐。这里要介绍一下我的这位老朋友,陈珉是华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系的教授,长相温柔,对我们也关怀备至。她研究獐有二十多个年头,经历了我们几代獐的生老病死,有人类称她是“獐妈妈”,所以对于她的很多说法,獐家族内部都是持认同意见的。
“记者说他看到我和其它几只獐在一起厮混?”
这里需要澄清一下,我与别的獐走着,只是凑巧我们在同一个地方,步行速度相近,这有基因的成分,也有地利的原因,但骨子里我是不想跟他们交流的。
“社恐”属性对我们来说,有时候是种保护,会让我们对可能面临的“危险”敬而远之,但有时也会产生悲剧,比如,如果遇到天敌,惯于独居的獐是无法集体战斗的,所以结局往往不尽“獐”意。
有时候,外界环境的变化与刺激也会让我们产生应激反应。我记得那是一个大雨倾盆的初夏,明明还是下午,天色就已经黑压压的。华夏公园内,一只獐妈妈,我们暂且叫她小花,在怀孕6个月后迎来产期。
草场的围栏旁,有人类发现了小花,小花也察觉到了人类,或许是雷雨,也或许是陌生人类的原因,小花产生了应激反应,抛下两只刚出生的獐宝宝就离开了。刚出生的幼獐无母亲照料,又加上雨水很可能导致幼獐失温,人类研究者进入草场实施救助,我看到他们把其中一只幼獐抱回了人类居所,后来听说他们给幼獐取暖,用羊奶粉喂养,但最终没能把幼獐救回来。

不过,獐家族也有极少数比较“open”的例外。9年前,一只雌獐出生了,獐种群几乎通体同色,唯她额间一抹白,所以人类研究者们叫她“白脸”。我们獐一般即敏感又高冷,但白脸却不是,她对于来吃她奶水的幼獐来者不拒,多年来喂养很多只幼獐,研究者称她“英雄妈妈”。只可惜,白脸在今年上半年去世了,死于难产。
消失百年后回归
时光如白驹过隙,獐家族在上海兜兜转转生存了至少6000年,见证了它从农耕文明到工业文明的发展,但“陪伴”在上世纪初戛然而止。
那是人类社会快速发展的时代,工业化伴随城市化来势汹汹,大量自然生态环境被占用,我们不得不一步步后退。陈珉也跟我说,那时的太湖流域流传着一种民间偏方,说幼獐喝母乳后在胃里形成的奶块,又称“獐宝”,可治人类幼童的消化不良,是稀有“良材”,因此大量幼獐被扑杀贩卖,这对一个种群的延续造成严重打击。
总之,那时起,我们从上海消失了。
再次回到上海,已经是100多年之后的事情。
人类的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出了本《重引入指南》,定义“重引入”:在一个物种的历史分布区内的一部分区域内(该区域此物种已经消失或绝灭)重新建立该物种种群的一种尝试。一群人类学者觉得从历史来说,獐家族在上海消失的时间不算久,符合重引入条件。
2006年,在陈珉等专家学者的指导下,上海市“獐的重引入项目”在浦东华夏公园试点。2007年3月,人类从浙江岱山的繁育中心,引入21只一岁大小的獐,尝试让獐家族“回家”。
不得不说,我们獐家族还是很争气,第一年,80%的獐活了下来,并在第二年把数量攀升到70只。
不过,重引入并不只是“换个地方喂养”,它的最终目的是让獐家族在野外自主生存,并在一定时间和空间内,持续达到一个稳定的数量。
根据人类干预程度的不同,重引入往往分为人工圈养、半野放、野放三个步骤。所以,在经历了一段人类伺候着、衣食无忧的日子后,獐家族还是要直面“充满无限可能”的自然界,其中包括危险,或是死亡。
好在,獐家族回到上海十多年,经过繁殖,华夏公园已为滨江森林公园、松江浦南林地、明珠湖公园和南汇东滩输入了不少野放獐。
野外求生
“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一个问题。”有时候,不得不承认,人类的一些文艺作品总能精准表达出我的内心所想。
华夏公园里的獐,几乎全部会被野放,包括我。人类为了最大程度保留獐的“野性”,所以我打生下来就没得到人类太多的眷顾。当然,这才有了现在的我,一只虽然社恐,但独立自强,可以去野外闯荡的獐。
我很早就听说了野外有多可怕,诸如成群的野狗、遍地的捕兽夹等等,但我也听过,上海野外有成片成片的芦苇荡,春天时芦苇荡节节长高,孕育生机,到了夏天,去水塘边喝水,青蛙和小鱼会在你嘴边游来游去,我还没见过鱼。我喜欢游泳,可还没真正痛痛快快地游一次。

在某个冬季的一天,我来到了滨江森林公园,与我曾经所期待的一样,这是一片沃野。
从木箱里被放出,我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跑”。跑过草地,跑过树林,跑出人类规划的景观世界,我见到了芦苇荡,毫不犹豫地冲了进去。
在野外的日子里,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自由的同时,也发现了一个愈加残酷的自然界。
近些年,野外的流浪犬也多,丧家之犬,凶猛异常,它们成群结队,一旦碰上,我们很难逃脱。我曾在野外看到过不少具同类被撕扯的尸体,多数是流浪犬所为。陈珉说,像我们这类无公害的食草动物,有一定数量的天敌,能够让我们维持运动的状态,有利于维护种群的发展。但陈珉也觉得,如果流浪犬数量过多,反而对我们家族的生存造成威胁。
我想,大多数流浪犬来自人类社会,不要遗弃,对它们对我们都是更好的安排。
陈珉告诉我,獐家族在上海的总量多年来都稳定在300只左右,这是个不错的数字,但如果问一句“重引入”成功了吗?我和陈珉都会摇摇头,真正的成功可能还需要几十年甚至百年的时间,其间会发生什么,很多无法预见。陈珉说,从生物学的角度,野外的獐至少要有500头繁殖种群,总量约1000头,才基本达到种群恢复的标准。
世界复杂,但于自然法则而言,或许我所面对的,必然是我要面对的。希望多年后,我们能在城市的某个角落偶然相遇,并成为朋友。
责任编辑:高文
校对:施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