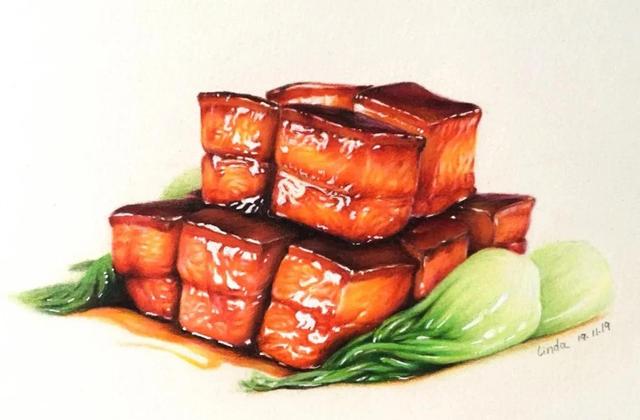——学习笔记
白璧德是20世纪初米囯新人文主义运动的首倡者与奠基人,也是一位与中国颇有渊源的思想家。
新人文主义是一场基于东西方的文学与哲学思想资源的文化复兴运动,企图通过复活古代人文主义精神来拯救现代社会的混乱与危机。白璧德的思想研究不仅将中国的传统儒家思想纳入他知识考察的范围,而且将孔子誉为东方的亚里士多德,认为孔子思想与西方传统哲学可以帮助西方文明走出现代困境,他出版的《卢梭与浪漫主义》就这样写道:“古老的东方经验用一种有趣的方式完成并确认了西方欧洲的经验,如果我们期待找到真正普遍的智慧来批判目前自然主义中可恶的片面性,那我们万不可忽略远东经验。从目前实用的目的看,远东经验主要集中在两个人的教谕与影响里,这两个人便是孔子与释迦摩尼”,需要指出的是,他对于儒家思想的阐述与借鉴主要集中在以孔子为代表的古代儒家人文思想传统上,因为白璧德的人文主义思想丰富厚重,涉及文学、哲学、历史、教育和宗教等多个方面。
白璧德的节度法则与儒家的中庸之道有契合之处,节度是白璧德人文主义哲学思想的重要内核,在他看来,人类社会存在一系列二元关系,如“一与多”、“常与变”、“永恒与暂时”、“同情与选择”等等,然而,人们却会常常走向一个极端,让个体的本性无限扩张,成为泛滥的人道主义者,只有采取节度的方式,避免趋向极端,这样才能成为人文主义者。
白璧德坚决反对现代社会存在的两种趋向,其一是以培根为代表的功利自然主义者,他们迷信机构与效率,将机器视为达到效率与道德目标的手段,一味追求物质进步;另一是以卢梭为代表的情感自然主义者,他们主张回归自然,以一种不加选择的同情来取代道德意义上的工作。白璧德认为前者对自己的才智不加节制与选择,混淆了物质进步与道德进步,一心营求物质利益,导致西方文明表现出离心式的个人主义症状;认为后者则是对自己欲望不加约束和限制,放纵情感和美化德性。卢梭主义者的性本善理论与回归自然观会引发人类欲望的无限扩张,因此,白璧德在坚决反对卢梭的“在万有和虚空之间没有中间词的表达”时引出节度法则,并指出人应该在普通自我与更高意志之间进行协调。即使普通自我体现为情感的放纵,更高意志也不能任意行事,必须遵循一定的标准,人们应该用制约意志来约束放纵的情感,在他看来,真正的人文主义者既要反对过分的同情与选择,又要防范过分的自由与约束,要在两个极端之间进行协调,并填实二者之间的空白。白璧德认为一个好的人文主义者应该是中庸、敏感与得体的,他的中庸主要指克己、节制;敏感指不麻木不仁但也非好奇立异;得体则指合乎标准,不随心所欲。白璧德的节度法则与孔子的中庸之道不仅在表述上存在惊人的一致性,其内涵在某种程度上也存在一致性。中庸思想是贯穿孔子儒家思想的一条主线,其中过犹不及是孔子中庸思想的理论核心,《论语》中记载子贡问孔子:“师(子张)与商(子夏)也孰贤?”孔子答:“师也过,商也不及”,子贡再问:“然则师愈与否?”孔子回答道:“过犹不及”,从这段对话中可以看出孔子认为“过与不及”均为事物的两个极端,其产生的后果是一样的,也反对用这两种方式处理事情,同时将“无过无不及”的适度视为一种最佳的状态,即他主张的中庸,要求在为人处世上做到克己复礼与仁者爱人,强调加强内心修养和将内心修养达于外,做到立己立人,达己达人。与孔子中庸哲学稍有不同的是白璧德的节度不提及爱人,他注重对内在生命的自我克制,按照节度法则来抑制自然人的欲望,要有怀着敬畏与谦卑来仰望某种更高意志,并通过遵循某种标准来约束规训自然意志从而保持中和。
白璧德对孔子的中庸之道是高度肯定的,他在著作《民主与领袖》中认为孔子将此世的生活艺术发挥到了极致,孔子本人对“人之所以为人”这个问题有着深刻的、真切的洞察,他称之为“内在制约的原理”,坚持儒家传统中的东西会让社会获得一种内在的力量。需要强调的是,无论节度法则还是中庸之道,两者即是一种生活哲学也是一种政治伦理,不仅适用于个人也适用于国家,都需要更高意志来约束自然意志。白璧德就曾运用节度法则评击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产生,认为战争爆发的原因在于人性的蒙蔽和欲望的扩张,人性的自我膨胀体现在国家层面上,个人的生存扩张意志演变为民族权力扩张意志,正是由于个人内心泛滥着道德混乱,便产生无限制的权力欲望,进而取代了国际关系上的伦理控制。白璧德试图在政治与经济之外,去从哲学与伦理角度解释国际之间的权力与利益争斗。白璧德的认识论与实践论也与孔子的政治伦理存在呼应,孔子认为春秋时期各诸侯为争夺土地、开拓疆土而发起的战争均为统治者个人私欲膨胀导致的,是天下无道的表现,孔子的中庸之道也同样适用于他的政治主张,其伦理思想的核心“仁”便体现了“无过无不及”的中庸适度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