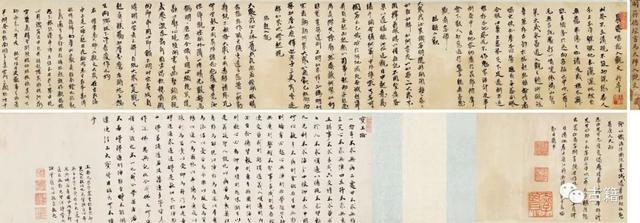崇祯元年七月,浙江一场水灾害得不少百姓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有人借此趁火打劫。海宁县二十多岁的朱安国就携家仆摆船打捞东西,天色已晚,漂来两只绳捆的木箱,上面各骑一位十七八岁的女子和一位老妇,两人大声呼救。朱安国见两人舍命顾箱,认为内中必有财物,遂心生恶念,接连两篙将老妇戳入水里。
女子半沉半浮,求告救命,朱安国恐留后患,又一篙将女子打入水中,然后只顾埋头捞走箱子。女子落水后,撞到一张木桌,顺手抓住桌脚在水面漂浮,结果被水浪冲卷到一户遭水淹的人家门口。这户主正是朱安国的族叔朱玉,朱玉小朱安国两岁,他救起女子,得知其姓郑,住袁花镇。洪水退后,邻里闻朱玉从水里捞救一女子,无不认为是天赐良缘,纷纷撺掇两人拜堂成亲,郑氏无家可归,倒也十分愿意。于是由朱玉的娘舅做主,杀猪宰羊,摆宴请客。

当天朱安国到场,一问新娘郑氏是漂流而来的袁花镇郑家女子,想到自己也曾定亲在袁花镇郑家,不由疑心族叔朱玉捡到的是自己的未婚妻。他火急火燎赶回家细加检视,发现箱子里有几锭银子与花绸竟然与自己当初下的聘礼一模一样。复经媒人证实,郑氏正是自己原来聘定之妻。朱安国找上小叔,称其违背人伦夺走侄媳,而碰巧不巧,郑氏也认出朱安国是当晚将自己和母亲打翻落水之人。
朱安国被郑氏喝骂离开后,思谋郑氏如状告自己谋财害命没有人证,而自己告朱玉欺占老婆则有媒人作证,于是先下手为强,状告朱玉灭伦奸占,朱玉也反告朱安国劫财反诬。海宁知县开堂审理,查明郑氏的确是朱安国的原聘妻子,而郑氏属于劫后余生,与朱玉结为夫妻。对劫财一事,经当堂质证,郑氏说出朱安国所劫箱子的特征及箱内物品清单,朱安国却语焉不详。知县以其谋财害命为由,准备用刑,不料朱玉跪地求情,称族兄仅有此子,且尚未娶妻,若动刑正法,不免绝了子嗣,恳求官府开恩。

众人也下跪求情,表示不少百姓此番趁灾捞财,若将捞物之为当作劫财之举,只怕纷乱迭起,况郑氏说朱安国杀她母亲,也无人当场见证。朱安国也叩首说未曾推郑氏落水,也未见过老妇,是箱子撞了他的船后,人才滚下水去的,未婚妻子情愿让给叔叔朱玉。
知县见状,便令朱安国具结保证日后不得谋害朱玉,并立案申报都察院,以威慑朱安国,然后提笔判道:“朱安国乘危射利,知图财而不知救人,已聘之妻落入朱玉之手,是天祸凶人,夺其配也。人失而宁知已得之财,复不可据乎?朱玉拯溺得妇,郑氏感恩委身,亦情之顺第,郑氏之财归还郑氏,朱安国之聘礼亦还安国。事出异常,法难深绳,姑从宽宥,立案以杜绝争端。”
这是《三刻拍案惊奇》第二十四回《缘投波浪里,恩向小窗亲》讲的一桩案例。乍看这起数百年前的案子,发觉知县难免姑息纵奸,竟放过了图财害命的朱安国。但细究一番,官府在判案时审情度势,适可而止,做出了令各方满意的判决,体现的却是司法的谦抑性与灵活性。对官府而言,有关朱安国劫财害命的指控,唯有郑氏一方的控词,并无其他人证,箱子虽获证是郑氏之物,然亦不能排除朱安国的辩解,即所谓箱子是因撞到船上被其捞得。

要想查明事实,按明代的司法程序,就要对朱安国刑讯,此时作为控方的朱玉反而为侄子求情,恐绝族兄后嗣。如此,查清事实,将凶手绳之以法,已非各方所愿,兼之案情本就难以查证,故知县称“事出异常,法难深绳”,所以“姑从宽宥”,只是立案存留官府,以防其日后加害控方。这不仅多少体现了疑罪从无的理念,也显示出官府在审案时能审情度势,适可而止,在穷根究底未必适当的情况下,对司法权做到“适当”而灵活地运用。
当然,这是由于在传统司法体制中无国家公诉制度,此案虽属劫财害命,然朱玉实际仍是“刑事自诉”,因此尊重当事人的意志,做到司法谦抑,就当时而言,倒也适当,对现代司法来说就另当别论了。此案对劫财的指控,更充分体现了司法的谦抑性,诚如众人所言,水灾中百姓多有打捞,若将捞取财物作为劫财,不免纷乱。对官府而言,若定要将所有此类案行为都诉诸法办,司法机关将不胜其累,也无此可能。

相较而言,灾后及时安定社会秩序显然更为重要,至于朱玉娶他人已聘之妻,本属非法,但一场洪水使原有婚约所据情势变更,郑氏感恩委身,“情之顺第”,知县并不“严格执法”,横加拆散,而是维护既存事实,巧妙做到人情与律法的平衡,同样也是司法谦抑与灵活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