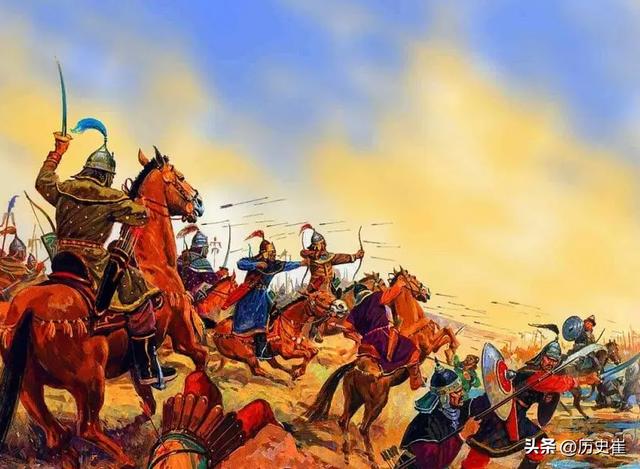一、斗蟋蟀的历史渊源
斗蟋蟀又称“斗促织”、“斗蛐蛐”等,其作为我国一项传统的民间游艺具有悠久的历史,久盛不衰。 早在西周时期人们就以蟋蟀所居地方的改变来感知天时气候的变化。如《诗经·唐风·蟋蟀》中云:“蟋蟀在堂,岁聿其莫。今我不乐,日月其除。”又如《诗经·豳风·七月》中云:“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由于蟋蟀体现着物候变化,提示这秋天的来临,在我国传统的民族心理中,蟋蟀一向是文人墨客笔下悲苦情怀的意象。
蟋蟀善鸣,至唐代开始作为宠物进入人们休闲娱乐生活中,“毎至秋时,宫中妃妾辈皆以小金笼捉蟋蟀,闭于笼中,置之枕函畔,夜听其声,庶民之家皆效之也。” [1] 唐代宫中的妃嫔、宫女们以笼饲养蟋蟀听其鸣叫以尽耳娱之乐,很快成为时尚传到民间,在生活中人们也发现蟋蟀善斗的特征,斗蟋蟀这一娱乐活动也开始进入人们的休闲生活。《负暄杂录·禽虫善斗》中载道:“斗蛩之戏,始于天宝间。长安富人刻象牙为笼蓄之,以万金会之一斗”, [2] 可见斗蟋蟀作为一项娱乐活动至迟在唐天宝年间就已出现,但还是只是富人阶层能玩的游戏并非普通大众的娱乐。
澄泥蟋蟀罐 明宣德,高8.8厘米,口径12.3厘米,足径12.5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青花云龙纹蟋蟀罐,明隆庆,通高10.6厘米,口径13.2厘米,足径13.4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三、蟋蟀的斗法与局矩
斗蟋蟀之俗虽是南北共有的风俗习惯,但是在斗法上尤为不同。南方地区以江浙一带为盛,“江浙风俗,每届秋期,率以畜养蟋蟀比彩斗胜”[11]竞斗地点多在酒肆、茶馆、茶棚等娱乐场所。在斗法上有着统一的局矩,朱从延在《蚟孙鉴》中对清代苏杭地区的斗蟋蟀的局规描述道:
“掌菣人与各府州客虫到局,秉公相合。俟虫主自心两愿,编号上柜。临斗,两虫主监局点动咶鸣,徐徐用菣,先在头背并其尾腰,如即张牙鼓翼者,无病方可交锋。如虫无尾菣,沿走无情,非失雌则患病,不可即斗。亦有虫性未旺,须再㸃呌咶鸣,菣其须脇,次讨小脚,有情,方捻牙口一菣。左提右调,俟性发势旺,鼓翼数声,待翅收好,才可领到中闸。各待回报,方提起中闸板。两架菣不许过闸,如横各㸃正,不得挑拨,但观其交牙两跌开。如肓虫、多领正一菣再交锋。跌开或胜或负,虫主自看。喝呌两下菣,即当两下菣。或虫主愿认下锋者,即㩇下锋落中闸。俟复时,上锋手㸃咶噪,下锋手细修菣,如斗绝无情,再使游四角讨菣。果无情, 硬㩇撞头三次。下锋手落中闸板,赶出取彩。如下锋三畨四次有菣有斗性,方许上锋手使菣,领上锋逼住常鸣,但不许追扑。若上锋惜虫,愿减分数而决胜负,此苏杭至公之法规也。如掌菣人私心,该下菣不下菣,过棚追赶,咬失腿脚而负,使菣之人赔虫、赔银。此一定之例,无容争辨者也。”[12]
从上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出,江浙地区的蟋蟀斗局规则严密,赛前要给蟋蟀编号、检查蟋蟀的健康状况,挑起斗性,一切准备就绪后才可开斗。在斗蟋蟀过程中有的力量悬殊、一战告捷,有的势均力敌、不相上下。对于不遵守规则、使诈的主人还有较为严厉的处罚措施,体现了斗局公平原则与信用意识,对于人们树立公正的处事态度以及弘扬人类高尚的竞争精神有一定的意义。当今社会的蟋蟀斗局规则也多来源于此,现代人们在竞斗前都会将蟋蟀交给“公信人”处饲养,公信人都是出自当地的斗蟋能手,他们有着好的人缘与公正的处事态度。蟋蟀从准备阶段的称量、喂食、闷花、看虫到进入斗栅的芡草、别头、点牙、计时、判胜负等各项环节,都有系统而又严格的规则,整个环节接受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