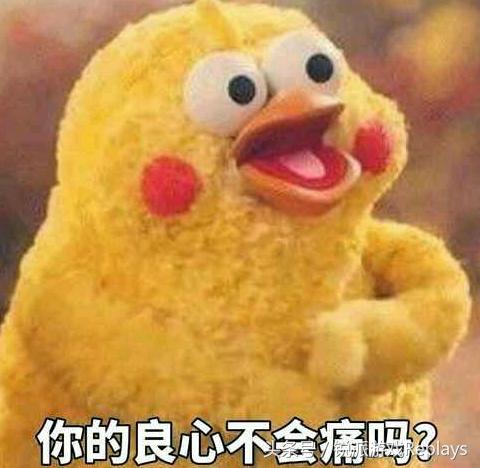文/龚莹莹
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中,包含了人类的一切行为,甚至思想,最终是要效法自然及其本质规律的。推而广之,文学的生态伦理若以自然、精神、社会“三态”同构为准则,在此视域下的文学作品,也可称得上是生态文学。杨献平的散文集《黄沙与绿洲之间》正基于西北沙漠的特殊环境,彼此“三态”蕴含的艺术特色和精神特质,交流呼应,正反互动,显性、隐性的多层共生,可遇不可求。
首先,杨献平的边地散文写作中,始终体现着精神生态和文学叙事的交互感。
杨献平出生于南太行山区,以散文、诗歌和小说等文学体裁活跃于文坛。他离开故乡,从军于巴丹吉林沙漠,按他自己的话说,“像纸片跌落在黄沙与绿洲之间。”成年后的杨献平,依然不断省察和审视作为故乡的南太行,在其文学叙事中,还把“灵魂的胞衣”葬在了故乡。从南太行到巴丹吉林,成为他精神乡域的两个地标,也是他散文写作的一对翅膀。
沙漠特有的澄明和混沌,雄浑与精微,是自然中一个横亘的巨大存在。在对春天的期待中,杨献平领悟到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的律令与节奏,不可违抗,人也无法逾越和掌控自身之外的任何事物(《巴丹吉林:沙漠中的人事物》)。杨献平的文学叙事遵循着巴丹吉林的自然伦理,与各有姿态和尊严的动植物相互关照扶掖,谛听沙漠给予的智慧,经过沙漠的“思想改造”和“心灵引发”,不断用文学的方式不断发现和表达自己“所属的时代”。
第二,杨献平的边地散文写作,始终努力达成自然生态和人性共建的文学审美。
杨献平认为,散文的语言应当“是诡异的利箭,是呼啸的风声,河流一样斗折蛇行,如线如弦,如泣如诉”。他的文字简洁有力,很多篇幅断行成诗。例如《秘密的河流》《风中的河流》和《巴丹吉林:落日与废墟》等,不论周遭路过、戈壁峡谷、红水河,甚至从一棵枯树的正面看见的雪山,下笔短长逶迤,节奏慷慨流转,每个意象都带着金戈铁马的腔调与玉帛笙歌的交织落差。
生态文学是基于生态伦理的人学,它立足现实,进而表现人性并思考人性。《乌鸦或幻境》就是一篇反映人性的返魅之作,由一只白色瞳孔的乌鸦开始。作者少小在故乡,南太行的人与自然为一体,是“附魅”的。杨献平通过西北地区灿烂辉煌的历史,联想到乌鸦的图腾崇拜与民族流变、军事冲突相关,在对乌鸦这个文化符号进行查证的时候,还发现它在上古传说中承担过相当特殊的使命——太阳神鸟。
基于对西北文化的深刻理解,以及对生存之地的敬畏和虔诚,文章对乌鸦的叙事,展现出人性理智的一面。当自己的前途命运变得迷茫,乌鸦便带着魔幻色彩一再地出现在梦里。
附魅、返魅都是文学艺术的形式,在“天人和美”的生态视域下,人与万物相互联系、共生共荣,体现文学艺术的包容性。当现代科学斩钉截铁地为世界祛魅的时候,是文学赋予的神秘和浪漫,支撑世间温和、从容,让人在恶劣的环境中生存,并从中获得强大的自我救赎的力量。
第三,杨献平的边地散文,始终强调呈现社会生态和精神特质的主题性。
在沙漠这样的特殊环境里,人类中心主义很难生存,充满“破”与“立”的较量。例如《那斯腾》中的牧民生活,在高天阔地的戈壁,一个牧人,就是巴丹吉林沙漠的王,这是典型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
《双重的废墟》更是对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彻底摒弃。壮美的哈日浩特,战争和死亡的宏阔被历史淹没,芨芨村的女孩,却被继父杀害。人心荒芜造成的万劫不复,比真正的废墟还可怕。在这里,读者看到了时间的废墟和人心的废墟组成的双重废墟。
纵观全书,整体主义思想从《秘密的河流》开始构建。当弱水这汪“穿梭于时间和空间的血液”注入杨献平的体魄,丰富了并成为精神特质持续发展的源头。其中的《额济纳的农民生活》可与《那斯腾》互文照应,戈壁虽然荒凉,但少过多的吵闹纠纷,从不亏待善待它的人。
《唇齿之间的痕迹》则出现较大的拓展。作者拜访芨芨村,见到西汉将军的后人,虎姓、前姓、杨姓、年姓、李姓、呼延、郎姓、雒姓等等各色人家,除了遗留的王朝的局部影像,还有他们身上万世不灭的精神文化。
但人和生命,能让一切荒芜之地逐渐变得诗意和美好。《犹如蚁鸣》将视角打开,把鼎新镇出租车司机的故事展现给读者,让人感同身受。不论多么不可思议的故事在沙漠中发生,自觉声如雷霆,却犹如蚁鸣。
杨献平的文学叙事在抵达《简史或自画像》时,已经渐入佳境,呈现丰满的状态。他把自己对生活的认知付诸写作,并进行充分概括和展示。《夜行者》《风中的河流》等文章都是在生活周遭的环境下,深度思考地加深和持续。
《虚构的旅行》讲述沙漠中的一场旅行,成为成长过程中的隐秘标志。《在沙漠失声痛哭》书写了成年人对青春与人间亲情的抚摸。《沙漠爱情故事》讲述军人的爱情。有人选择放弃,与环境一起沉沦,有人则用书籍、游历和饮酒等方式来排解。
《盛夏的沙漠,秋天的沙漠》一文,作者在历史中宣泄悲怆,并再次提到李陵,称其为“千古第一伤心人”。这既是遗忘当下的选择,也是在匮乏中,不断与千年前的智者发生碰撞,让思想的力量超越时空,与天地同在共生。
《巴丹吉林:落日与废墟》也是极美的文字。落日与马,展现宏大无匹的苍凉悲怆;边关古塞的气概,让军人的内心和灵魂中,始终飘扬着高贵的旌旗,也回荡着冲锋的号角与金铁交鸣的黄钟大吕之音。
《疫情之下,陌生人的痛与乐》写到10年之后重回西北,对人以及生活的回眸。《黄沙中的城与乡》还不厌其烦地书写曾经的延居海、额济纳,包括在自然资源日益匮乏的鼎新绿洲生活的故人。
可以说,《黄沙与绿洲之间》的文学叙事、艺术特色和精神特质,没有按照精神、自然和社会“三态”进行简单的分门别类,而是以生存的方式,“天人合美”多层交织,呈现了人与环境同生共荣的文学景观。
书名:《黄沙与绿洲之间》
作者:杨献平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欢迎向我们报料,一经采纳有费用酬谢。报料ihxdsb,33864057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