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记者 高丹 实习生 代方莹
【编者按】对许多中国作家而言,无论在文学意义,还是在思想与精神层面上,鲁迅都是一个特别的存在。今年是鲁迅诞辰140周年,在“读鲁迅”这个系列中,我们将请作家、研究者们谈谈他们最喜欢的鲁迅作品以及鲁迅对其创作的影响,并附上他们欣赏的鲁迅作品原文(片段),让我们一起来读鲁迅。

鲁迅先生雕塑。人民视觉 资料图
当被问起对鲁迅哪些话印象比较深刻,学者、鲁迅研究专家、北京鲁迅博物馆前副馆长陈漱渝谈道:鲁迅最早发表的一篇白话短篇小说叫做《狂人日记》,也就是中国现代白话短篇小说的奠基之作。作品中他借狂人的口对旧的宗法社会和旧的伦理道德提出了质疑。有一句话就是七个字:“从来如此,便对吗?”
“这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后来根据这句话,我编过一本鲁迅语录,现在有一些文化公司根据这句话还做了一些文创产品,比如手袋。这句话体现了一种科学的怀疑精神。科学的怀疑精神是打开一切科学大门的钥匙。人们在求知的过程当中总是由怀疑到无疑,如果不会怀疑,学业也就不可能有长进。当然这个怀疑不是怀疑一切,而是说要探求真理,而探求真理的过程是漫长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怎么样判断正误,靠的是事实——历史上的事实,现实当中的事实。我是相信事实的,是相信真相的,不像西方现在流行的相对主义。它否定一切。当然,真相被人叙述出来,可能有一定的主观色彩,可能被扭曲,也可能被有选择性的呈现。但是怀疑精神是我们追求真理过程当中不可或缺的精神。所以我对这句话印象很深。这是一个真理,亘古不变的真理,不仅适合于鲁迅的时代,也适合于今天和明天。”陈漱渝谈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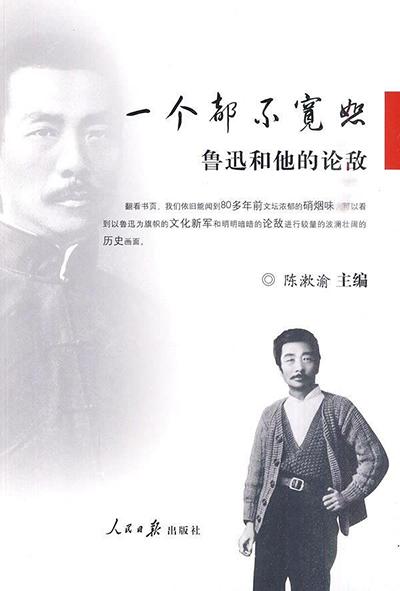
《一个都不宽恕:鲁迅和他的论敌》
而除了这些只言片语的话,鲁迅的很多文章也让陈漱渝至今记忆真切,他谈道:“我在中学时代,在语文课本当中学过鲁迅的两篇杂文,一篇叫做《记念刘和珍君》,一篇叫做《为了忘却的记念》。这两篇文章影响了我的一生,也影响了我的文化性格。现在有一些学术大咖公开讲鲁迅进行的是仇恨教育,是不可取的,是毒害青少年的。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能够成立的。”
“在鲁迅看来,在旧时代,人可以粗略地分为两种:一种是压迫者,一种是被压迫者。鲁迅对人有着一种大爱,无疆的大爱。鲁迅爱个体的生命,爱大众的生命,更爱战士的生命。所以他自然就痛恨生命的摧残者,痛恨一切专制制度,痛恨一切的暴君酷吏。所以在《记念刘和珍君》当中,他心中常存着刘和珍君的微笑,痛恨北洋军阀政府的暴行。《为了忘却的记念》当中,他热爱像柔石殷夫这样的革命青年,所以他痛恨摧残革命烈士的国民党法西斯政权。鲁迅有句话我印象很深,大意是,说一个文人不应该随和,因为随和只会使你成为一个和事佬。鲁迅的很多文章都是论争性、论辩性的文章,这是鲁迅文章当中最宝贵的一部分,所以鲁迅他自己是爱憎分明的。他的爱是神圣的爱,他的憎也是神圣的憎!这个影响了我的文化性格。所以我在当下面对很多问题,我是敢于站出来的说真话的。我不愿意做鲁迅笔下的那种‘正人君子’。虽然说真话,可能被误解或者是被攻击,我都无怨无悔。当然,一旦有了错误,我还是要承认并加以修正。然而,我还是要有明确的是非,要做一个有血性的人,一个真实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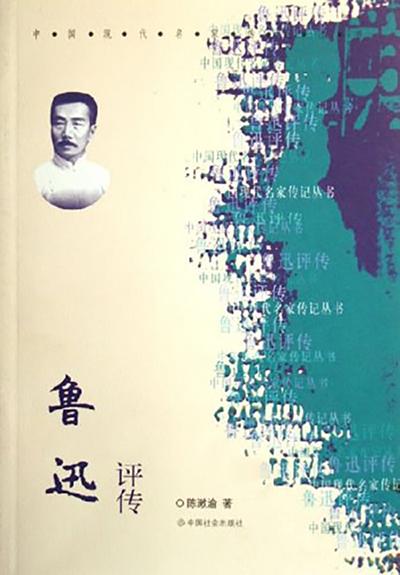
《鲁迅评传》
陈漱渝是从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的,他关于鲁迅的第一篇研究心得是1961年发表的,到现在已经60年了。开始比较系统地读鲁迅的著作是在1974年左右,到今天已经是47年了。“我在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专门从事鲁迅研究的工作,也是被人说是‘吃鲁迅饭’,前前后后是32年。”陈漱渝说。
虽然很长的一段时间陈漱渝调侃自己是“吃鲁迅饭”,但是他谈道,自己研究鲁迅,以鲁迅研究为职业,完全是一种机缘巧合。“因为我当时任教的中学的原址,就是鲁迅曾经任教过的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所以学生就老让我讲鲁迅与女师大学生运动的一些事情。当时的首都图书馆有一个书库,研究北京史,大约叫北京地方史料,所以我就开始研究鲁迅在北京时期的生活,从1912年到1926年这14年。后来出了一本书,叫做《鲁迅在北京》,那是很早出版的。这本书现在看起来很单薄,也很肤浅,但是提供了鲁迅研究的很多的学术生长点。比如鲁迅北京时期在教育部的工作,鲁迅和北京一些文艺社团的关系,鲁迅和北京一些报刊的关系,鲁迅在北京住过的地方,乃至于什么鲁迅与北京的公园,等等。但是我后来也都没有很深入的研究下去。现在很多人在这个基础上都有了研究的专著,把我远远的抛在后边。但是我提出这些问题应该比较早。开始的时候我比较关注这些问题,后来因为我接受了撰写《鲁迅传》的任务,给作家出版社出了一本鲁迅传,叫做《搏击暗夜》。这样一来,我对鲁迅生平的方方面面都需要了解,不然怎么能够写一部反映鲁迅一生的传记呢?”

《搏击暗夜》
“但是现在我也老了,我觉得研究鲁迅的重点是应该研究他上海时期的活动。鲁迅在上海虽然只生活了10年,但是他的创作的数量超过了以前的20年,是鲁迅思想成熟的阶段。所以,不研究上海时期的鲁迅就可以说是不懂得鲁迅。这是我需要补课的地方。但是上帝能不能再给我时间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我已经过了80了。”陈漱渝说。
长期浸淫于鲁迅的作品中,陈漱渝常常觉得鲁迅的价值不止于文学,而常常能为自己的人生提出指引:“1966年,那个时候我才25岁,刚工作三年,没有经过‘文化大革命’这种世面。自己的性格有弱点,既自尊但是又脆弱,不想苟且偷生,所以曾经有过了断自己这一生的想法。在这个时候鲁迅的书就成了我的救命书。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读到了鲁迅散文诗集《野草》当中的一篇,篇名叫做《秋夜》。作品当中有两株枣树。枣树叶子已经落尽,枣子也被打尽,只剩下了遍体鳞伤的树干。然而在那个暗夜当中,光秃秃的枣树,依然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但是枣树不仅只是这样倔强地活着,而且还跟小粉红花一样在做着梦。在阴冷的夜气当中还梦见春的到来,梦见秋的到来,因为秋虽然来了,冬虽然来了,但是此后接着的是春天。这篇散文虽然短,可是在那种特定的历史情境当中,我感受到了这是我的精神支柱。我自己应该承受一种生命之重。鲁迅这篇文章使我从绝望当中看到了希望,在暗夜里看到了微芒的曙光,所以我就顽强地活下来了。从那个时候到今天,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要成为一个鲁迅研究者或者是鲁迅研究专家。当时把鲁迅的书当做一种精神支柱的,不只我一个,很多人都是。”

《他山之石:鲁迅读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
而对于“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阅读鲁迅的精神有哪些现实意义?”这个问题,陈漱渝回答:“很好,很尖锐,很敏感,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这个不同人可能有不同的感受,说出来还可能挨骂。这个我是经受过的。但是我可以讲,鲁迅作品的现实意义是方方面面的,是有多重的意义。比如现在社会比较的功利,而鲁迅提倡的一种精神,用四个字概括叫做‘损己利人’:就是牺牲自己,为国家为民族做奉献。他说,‘在生活的路上,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以饲别人,虽自觉渐渐瘦弱,也以为快活。’剥削者的道德损人利己,这个是不可取的。‘人我两利’是五四时期的道德观,这是很难绝对做到的。因为在‘人’、‘我’天平的两端,你很难把它绝对摆正,有的时候会向‘我’这一边倾斜,有的时候会向‘人’这一边倾斜。这只是我举的两个例子,此外的还有很多。”
附:鲁迅《秋夜》
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这上面的夜的天空,奇怪而高,我生平没有见过这样奇怪而高的天空。他仿佛要离开人间而去,使人们仰面不再看见。然而现在却非常之蓝,闪闪地䀹着几十个星星的眼,冷眼。他的口角上现出微笑,似乎自以为大有深意,而将繁霜洒在我的园里的野花草上。
我不知道那些花草真叫什么名字,人们叫他们什么名字。我记得有一种开过极细小的粉红花,现在还开着,但是更极细小了,她在冷的夜气中,瑟缩地做梦,梦见春的到来,梦见秋的到来,梦见瘦的诗人将眼泪擦在她最末的花瓣上,告诉她秋虽然来,冬虽然来,而此后接着还是春,蝴蝶乱飞,蜜蜂都唱起春词来了。她于是一笑,虽然颜色冻得红惨惨地,仍然瑟缩着。
枣树,他们简直落尽了叶子。先前,还有一两个孩子来打他们,别人打剩的枣子,现在是一个也不剩了,连叶子也落尽了。他知道小粉红花的梦,秋后要有春;他也知道落叶的梦,春后还是秋。他简直落尽叶子,单剩干子,然而脱了当初满树是果实和叶子时候的弧形,欠伸得很舒服。但是,有几枝还低亚着,护定他从打枣的竿梢所得的皮伤,而最直最长的几枝,却已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使天空闪闪地鬼䀹眼;直刺着天空中圆满的月亮,使月亮窘得发白。
鬼䀹眼的天空越加非常之蓝,不安了,仿佛想离去人间,避开枣树,只将月亮剩下。然而月亮也暗暗地躲到东边去了。而一无所有的干子,却仍然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一意要制他的死命,不管他各式各样地䀹着许多蛊惑的眼睛。
哇的一声,夜游的恶鸟飞过了。
我忽而听到夜半的笑声,吃吃地,似乎不愿意惊动睡着的人,然而四围的空气都应和着笑。夜半,没有别的人,我即刻听出这声音就在我嘴里,我也即刻被这笑声所驱逐,回进自己的房。灯火的带子也即刻被我旋高了。
后窗的玻璃上丁丁地响,还有许多小飞虫乱撞。不多久,几个进来了,许是从窗纸的破孔进来的。他们一进来,又在玻璃的灯罩上撞得丁丁地响。一个从上面撞进去了,他于是遇到火,而且我以为这火是真的。两三个却休息在灯的纸罩上喘气。那罩是昨晚新换的罩,雪白的纸,折出波浪纹的叠痕,一角还画出一枝猩红色的栀子。
猩红的栀子开花时,枣树又要做小粉红花的梦,青葱地弯成弧形了……我又听到夜半的笑声;我赶紧砍断我的心绪,看那老在白纸罩上的小青虫,头大尾小,向日葵子似的,只有半粒小麦那么大,遍身的颜色苍翠得可爱,可怜。
我打一个呵欠,点起一支纸烟,喷出烟来,对着灯默默地敬奠这些苍翠精致的英雄们。
一九二四年九月十五日。
责任编辑:梁佳
校对:张亮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