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鲁迅关于音乐的日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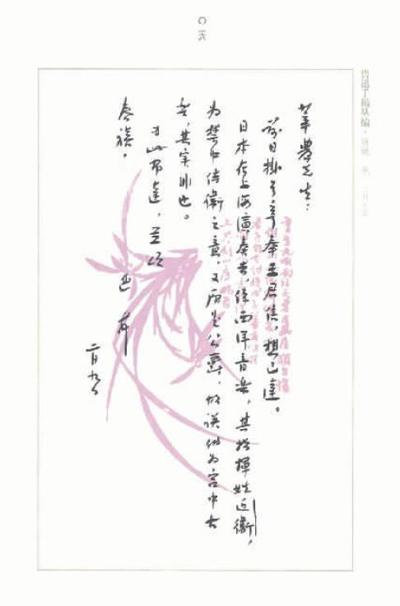
鲁迅关于音乐的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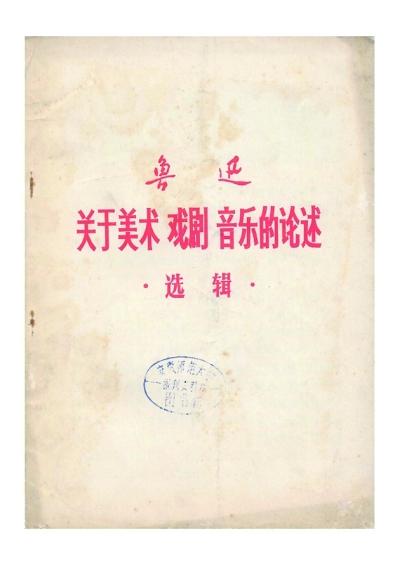
《鲁迅关于美术·戏剧·音乐的论述》封面
在蔡元培看来,“先生于文学外尤注意美术,但不喜音乐”。然在鲁迅的散文与小说中,我们不难看到他对流行于绍兴乡野民间的戏曲音乐所作的诸多描述,字里行间流露出他对民间文艺的由衷喜好。
在《五猖会》一文中,鲁迅以动人的笔触描述他在孩提时代,对民间迎神赛会的热切向往,“要到东关看五猖会去了,这是我儿时所罕逢的一件盛事”。被收入初中语文课本的名篇《社戏》中对乡间演出社戏细致入微的描写,更是深深印刻在无数读者心中。1916年12月,鲁迅特地从北京赶回绍兴为母亲操办六旬寿诞,在日记中留下了“下午唱花调”“夜唱平湖调”等聆赏民间音乐的记载。
在绍兴山会初级师范学堂(今绍兴文理学院)教书时,鲁迅曾请在家中帮工的王鹤照为其传授绍剧《龙虎斗》中“手执钢鞭将你打”和目连戏的唱法,“我一边讲一边做给鲁迅先生看,他静静地细听,记住了”(《回忆鲁迅先生》)。于是便有了阿Q准备“投降革命党”而陷入亢奋的一段唱词:
得得,锵锵!悔不该,酒醉错斩了郑贤弟,悔不该,呀呀呀……得得,锵锵,得,锵令锵!我手执钢鞭将你打……
直到被绑缚刑场游街示众的当口,阿Q所想到的,仍是“《小孤孀上坟》欠堂皇,《龙虎斗》里的‘悔不该’也太乏,还是‘手执钢鞭将你打’罢”。无聊看客所遗憾的,不过是“游了那么久的街,竟没有唱一句戏”。鲁迅以如此神来之笔描写阿Q的悲剧人生和群众的麻木冷漠,如果没有对绍兴民间戏曲音乐的切身体验,是无论如何也写不来的罢。
1912年,鲁迅在教育总长蔡元培的提携下,出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第一科是当时社会文化艺术事业的最高管理机构,蔡元培力倡美育,提出“以美育代宗教”,改造国民性,作为第一科科长的鲁迅自然要责无旁贷地担负起这一重任。次年2月,他便在《教育部编纂处月刊》上发表了《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为中国艺术学学科的建立和非遗保护指明了方向。
鲁迅将“美术”界定为“美术云者,即用思理以美化天物之谓。苟合于此,则无间外状若何,咸得谓之美术,如雕塑、绘画、文章、建筑、音乐皆是也”。随后他援引西方对艺术的不同分类,认为音乐是在时间中展开的“动美术”,具有“不可见不可触者,是为音美”的审美特性;音乐又是“独造美术”,“虽间亦微涉天物,而繁复腠会,几于脱离”,注重内在情感表达,而非直接描摹客观事物,故亦为“非致用美术”,“皆与实用无所系属者也”。鲁迅对音乐艺术本体的认知,以当时的艺术学研究水平而言,是较为全面系统的,这也对其音乐审美观的形成起到了重要影响。
鲁迅认为,播布美术的目的在于“使与国人耳目接,以发美术之真谛,起国人之美感,更以冀美术家之出世也”。就音乐而言,他提出应建造奏乐堂,“当就公园或公地,设立奏乐之处,定日演奏新乐,不更参以旧乐”,同时应刊布音乐欣赏指南,向民众普及音乐常识,“先以小书说明,俾听者咸能领会”。对中国传统音乐的保存与研究,鲁迅提出要建立中国古乐研究会,传承保护华夏国乐,“令勿中绝,并择其善者,布之国中”,而非盲目否定传统旧乐。
1923年5月14日,日本音乐史家田边尚雄来华讲说“中国古乐之价值”,鲁迅亲赴北大听取了此次讲座,足见其对传统音乐一以贯之的学术兴趣。鲁迅还亲手校辑《嵇康集》,“第欲存留旧文,得稍流布焉尔”,已成为中国音乐史研究中一份珍贵的文献。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对民歌有着难以割舍的情结。据周作人回忆,当时他在绍兴搜集歌谣,便请在教育部供职的鲁迅代为留意,“他特别支持我收集歌谣的工作,大概因为比较易于记录的关系吧,他曾从友人们听了些地方儿歌,抄了寄给我做参考”(《鲁迅与歌谣》)。1927年,鲁迅委托高尔基给北方俄罗斯民族合唱团寄去了几首有谱的中国民歌,“借以表示崇高的敬意与谢忱”(《鲁迅年谱》),向世界传播“中国好声音”。他还编创出《好东西歌》《公民科歌》《南京民谣》《“言词争执”歌》等,用通俗的市井语言配以民谣体裁,予国民政府和反动军阀以辛辣讽刺。
1917年11月,鲁迅与蔡元培等一起审听了萧友梅所作的国歌《卿云歌》,并对蔡元培说“余完全不懂音乐”。蔡元培却认为这是鲁迅的谦辞或反语,“我不知道他这几句话的意思,是否把‘懂’字看得太切实,以为非学过音乐不可;还是对教育部这种办法不以为然,而表示反抗”(《记鲁迅先生轶事》)。1919年12月,教育部筹设国歌研究会,鲁迅被选派为干事之一。
1922年4月,俄国歌剧团来华演出,鲁迅不仅以极大的兴趣观看了演出,还亲自撰写《为“俄国歌剧团”》,热诚地将这“美妙而且诚实的,而且勇猛的”音乐加以“广告”,并在这“比沙漠更可怕的人世”,“唱了我的反抗之歌”。鲁迅还以希特勒禁唱穆索尔斯基作曲的《跳蚤之歌》为例,“这决不是为了尊敬跳蚤,乃是因为它讽刺大官”(《华德保粹优劣论》),说明音乐独特的战斗性。
1933年5月20日,鲁迅欣赏了俄国作曲家阿甫夏洛穆夫的新作,在日记中写道:“先为《北平之印象》,次《晴雯逝世歌》独唱,次西乐中剧《琴心波光》,后二种皆不见佳”。交响素描《北平胡同》(即《北平之印象》)以小贩走街串巷的叫卖调为素材,借助各种自然音响,生动形象地刻画出平民生活场景,贴近中国民众的欣赏口味。对这种来源于生活且主题鲜明的标题音乐,鲁迅自然持肯定态度。
1936年2月,姚克曾邀请鲁迅去欣赏日本音乐家近卫秀麿来华举办的音乐会。考虑到近卫秀麿的长兄乃是日本侵华主谋之一的近卫文麿(后任日本首相),且其来华公演背景复杂,鲁迅遂以“日本在上海演奏者,系西洋音乐,其指挥姓近卫,为禁中侍卫之意,又原是公爵,故误传为宫中古乐,其实非也”一类较为含糊的托词加以婉拒,体现其一贯的爱国立场。
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奠基人,鲁迅在译介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等人文艺论著的同时,吸收其理论精髓,结合《吕氏春秋》《淮南子》等文献载述,对“艺术起源于劳动”这一马克思主义艺术起源论予以深刻揭示:
我们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劳作,必须发表意见,才渐渐地练出复杂的声音来。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大家也要佩服,应用的,这就等于出版;倘若用什么记号留存了下来,这就是文学;他当然就是作家,也是文学家,是“杭育杭育派”。(《门外文谈》)
正是基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鲁迅对音乐领域内神秘主义思潮与故作姿态、脱离人民的倾向尤为深恶痛绝。在唯一一篇题为“音乐”的杂文中,他以匕首般辛辣的笔触,对徐志摩“你听不着就该怨你自己的耳轮太笨或是皮粗”的论调进行针锋相对的驳斥,“但倘有不知道自怨自艾的人,想将这位先生‘送进疯人院’去,我可要拼命反对,尽力呼冤的,——虽然将音乐送进音乐里去,从甘脆的Mystic看来并不算什么一回事。”同样,鲁迅对黎锦晖的《毛毛雨》和梅兰芳的《天女散花》等“软性音乐”也有过讥讽,“莫非电影明星与标准美人唱起歌来,也可以‘消除此浩劫’的么”(《法会和歌剧》)。在今天看来虽不无偏颇,但在国难当头的历史环境下,确有其必要的现实性与积极的美学意义。
(作者:黄敏学,系绍兴文理学院艺术学院副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