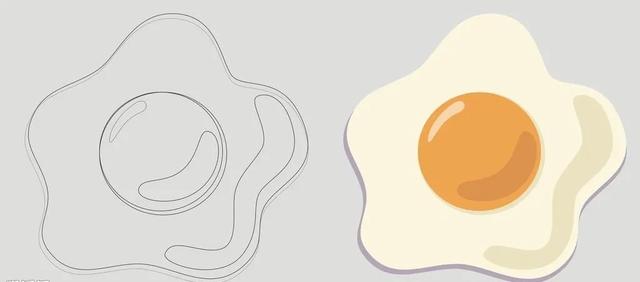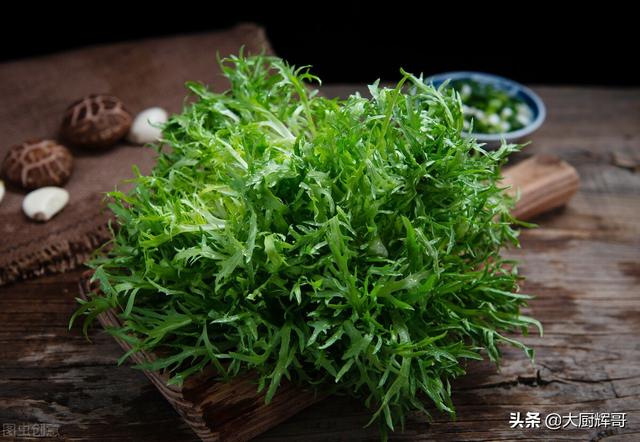本文作者“鲸书”,欢迎去豆瓣App关注Ta。
精神病院护士小安:我会警醒着别滑入黑暗

文丨鲸书
把试图用鞋带上吊的精神病人从厕所水管上猛拽下来,小安意识到,呼救已经来不及了,必须马上做人工呼吸,她半跪在厕所水槽旁,光线太暗,她摸索着才找到病人的嘴唇,嘴里很快沾满那名病人的痰液。这是1987年的午夜,小安做护士的第三个年头。
小安本名安学蓉,是成都市第四人民医院的一名护士。四医院是西南地区最大的精神疾病诊疗医院之一。当地人骂人脑子有病,就说“龟儿是四医院放出来的。”
去上班的第一天,小安太害怕,就郑重地化了妆,点头哈腰的跟病人打招呼。结果被病人追着看,现在想想,倒觉得有趣。
从重庆军医大毕业后,小安转业到四医院。许多病人有妄想症状:住院八年的招待所服务员,突然认定自己是有超能力的国安局特工,吵着要帮小安管其他病人;说话喜欢用“你的,我的,大大的”句式的老头,从未去过日本,却坚持给自己叫“夏子”的日本恋人写信;以为自己是开国将领的女儿的农妇,人生理想是做昭觉寺的千手观音,发功让女人多生儿子,早日实现共产主义······小安从不点破他们,觉得既然无法根治,留点幻想也是好的。
两名女病人厮打起来,她上去拉架,被两人围攻扯头发。另一名胖胖的女病人冲上来帮她。她没用“感动”来形容当时的感受,而是美滋滋地感慨到,“哎呀,我觉得好有趣哦。”
脑子里有个无法抗拒的声音的女人,那声音叫她杀人吃屎她都一一照做;住在同一病区的男同性恋病人晚上悄悄睡在一起,床上脏得让她脸红;把父亲的头割下来,却以为那是南瓜的大学生。有暴力倾向的病人,踢打撕咬病区里的医护人员。还有的意志消沉,一心求死。悄悄用牙刷、鞋带之类的小物件自杀,小安早年间值夜班,最害怕的去厕所,担心又碰到病人挂在水管上。因为病人自残自杀率高,治疗手段存疑,较之普通医院,精神病院发生医闹更频繁。
护士最怕的是病人逃跑,一跑就是严重事故。她曾写到,“天生有星星月亮太阳,就是没有亲爱的疯子···又经历了一次疯子逃跑后的焦虑,恐惧,绝望,白天黑夜疯了似的寻找,不敢想最绝的后果,以及确实希望奇迹发生。”
小安的神色里有一种见惯世事的索然,天天与他们打交道,既无嘲讽也不悲悯,只觉得彼此平等。一名女病人生日,想脱了病号服,穿着护士服拍照。小安就把自己的制服脱给她。小安不试图跟病人讲道理,像是在纵容不讲理的小孩。她在文章里毫不掩饰的把病人叫“疯子”,认为“疯”是正常的,“疯子”一词不含贬义。“我觉得医院的疯子很幸福呀,有吃有穿,还经常提意见,饭难吃啊,衣服不时髦,护士太丑挡了他的视线。”但她又说,变成什么都不重要,绝对不能精神病人,那只会是无穷无尽的痛苦。
她曾反省,把病人叫“疯子”是因为自己缺乏爱心不够善良,可又觉得“精神患者”、“有问题的人”并不准确。“我决定把自己看得很淡很轻,几乎到无形,这样想当然地和他们平起平坐了。”
小安已经调离病区,在咨询台工作。让资历较深的护士不再去病区,是医院的隐性福利之一。30年来,四医院和我国的精神疾病治疗现状都得到极大改善。她对这些改变无知无觉,在精神病院待了三十年,她对医院的体制改革的了解仍近乎于零,医院里最让她振奋的一片花园,她扳起手指给记者数,“里面有铁脚海棠、桃花、樱花、栀子花,还有条河,都没了,哎呀,有点可惜。”她还为医院外已经变成楼盘的油菜花地惋惜,那里曾是病人春游的地方。护士们带病人坐在田边唱歌,男女病人悄悄牵手亲热,按规定是不许的,小安低头扯燕麦,假装没看见,就让他们高兴高兴吧。
她甚至搞不清楚自己的收入组成,唯一知道的是工资里包含一项“挨打费”,即对被病人打的医护人员的补贴。她理解精神病人,觉得常人和精神病不过一线之隔,却不要求旁人也能理解。有人当着小安的面骂精神病人,还说精神病院待久了护士也不正常,她懒得辩解,觉得被理解是最不要紧的事。她说,连病人之间吵架也会对骂,你简直是个神经病。
她把医院的病人叫“家疯”,路边的病人叫“野疯”。在街上看到精神病人,小安觉得亲切。还给拿吃的,问他家在哪儿。“不是我多善良,而是我不怕他们。野外的疯子就像孤儿,只有进了医院才有归属。”
小安把这些经历写在《我们这儿是精神病院》一书中,以童话般的口吻。小安写一个叫“丽九”的女病人,她爱唱《甜蜜蜜》,她写到,“天亮了,到处都是她的歌声,甜蜜蜜,甜蜜蜜。头发里衣服里,地板上。我坐上火车,歌声跟着我,唱到成都来,二十年,甜得要命。”女病人最后跳青衣江死去,小安把黑暗痛楚的故事包裹在孩童般荒诞甜美的的句子里。
同事都不知道,这名会让病人吐舌头确认他们是否把药吃下去的小姑娘,工作之外是名写作者,还是“非非主义”的代表诗人之一。
小安毫不掩饰对诗歌的狂热,朋友也多来自诗歌界。她夸赞某诗人极有才华,记者问到“那是你爱人吧?”“前夫。”她坦然地纠正到。小安觉得精神病院的护士跟其他工作没什么两样,她没有被这份工作改变。而后她又补充到,“还是有好处,就是快滑入黑暗中时,你会自我警惕,别再跌落下去了哦。”这是在精神病院做护士给她的生活的警醒。“我经常感觉太无能太渺小,还欺骗自己,这个世界不适合我,肯定有一个更美的在等我,我是先苦后甜。偷听病人说话,好有趣,让我好些了。”她有了新的恋人,不想再结婚,与前夫关系良好,还一起聊诗。
近日一场名为“诗歌之美”的讲座上,小安作为讲者出席,她拿着讲稿,拘谨地念完不足50字的提纲后一言不发站在台上,追光灯下,小安被近千人注视着,她垂下头抠讲稿的卷边,羞涩得不知所措。主持人宁远来解围,郑重介绍了小安精神病院护士和诗人的双重身份。又代表观众提问,问她为什么在精神病院做护士,如何坚持下来的,打算换工作吗?她愣了下神,然后小声说,“啊?···因为一直在做嘛···”
1998年,小安曾被诗人何小竹拉去做过几个月的杂志编辑,她不适应到何小竹不再忍心勉强,她又回了医院。
2014年初的一个下午,病人们结束“放风”(即公寓疗法)回病房。数百名精神病人成群结队穿过医院走廊,动作迟缓呆滞,如同集体梦游。大部分病人在蓝白条纹的病号服里裹着厚衣服,被撑得鼓鼓的。空气里混合着消毒水味,药味,部分病人身上的恶臭味。
队伍在电梯口前停了下来,有病人突然发作,躺在电梯口,厉声辱骂医生,还要求给病房换一台能看娱乐节目的电视。一名护士高声安抚那名病人,“回去我给你调,保证可以看湖南卫视!”四名医生站在队伍外,点数,维持秩序。其余病人仍面无表情,一名不足十岁的小男孩指着面前的空气,表情专注地说:“糖糖,糖糖。”
小安在咨询台笑嘻嘻地看着他们,天有点冷,粉红色护士服太单薄,她一直在搓手。这是小安做护士的第三十个年头。
(全文完)
本文作者“鲸书”,现居北京,目前已发表了69篇原创文字,至今活跃在豆瓣社区。下载豆瓣App搜索用户“鲸书”关注T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