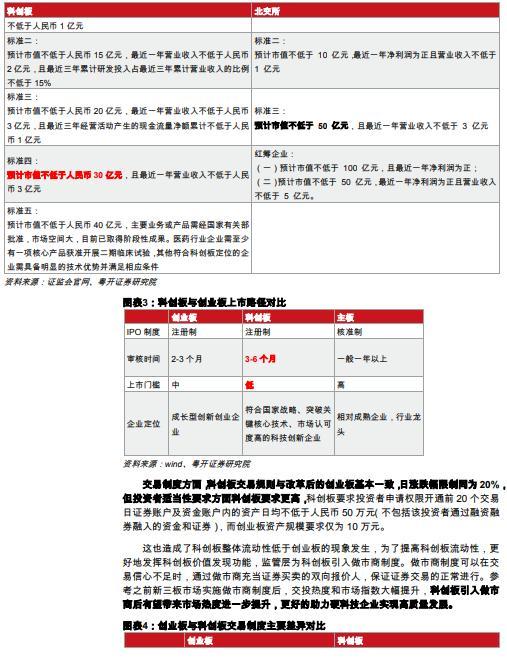张炜先生在《文学:八个关键词》中把“童年”排在最前面。
他说:“一个人精神的成长,其实就是从儿童时代出发,一步一步向前,走到非常遥远的地方,最后再回归到童年那样的‘单纯’。这好像是一个生命的圆形轨迹,也是文学表达的全过程。”
近日,读完洪浩兄新作《北风啊北风》,再来印证张炜老师的观点,更觉豁然开朗。
《北风啊北风》是一本很奇特的书,“既是一部关于童年的回忆录,也可视为一部成长小说”,更可以当做一本诗集来品味。

◆ 回忆录:童年最起码的拥有
童年需要最起码的拥有,比如田野、游戏、蓝天、河流、鸟鸣、远山和林地等。(张炜《文学:八个关键词》)
我们常常在一些颇具传奇色彩的故事或传记里发现,那些非凡的人物,似乎从童年起就过着开挂的人生,要么家世显赫,要么天资卓绝,要么屡有奇遇。
于是便顺理成章地告诉自己:我们之所以平凡,是因为童年就很普通。
但在这本书里,你会惊奇地发现,一位作家的童年,竟然也和我们差不多——有些地方甚至还不如我们呢!
比如,他家住着普普通通的瓦房,院墙是木槿编织成的篱笆,小院后是一片小树林,“春天和妈妈一起采摘榆钱,夏天听知了在树上长鸣,秋天看螳螂树干上产卵,冬天看鸟雀枝头间追逐。”
比如,他的爸爸妈妈就像大多数被柴米油盐消磨了温情的伴侣,“极少有和睦相处的时候,他们经常吵嘴,相互之间似乎也没有什么感情可言。”
比如,他童年时候的游戏,是玩泥巴、“摔娃娃”、摔纸包……甚至只是爬上土窑独自凝视天空。
比如,他常常㧟起篓子到山上拔草,也常常挨妈妈的揍。
比如,他会找各种理由逃课,他也因老师的表扬沾沾自喜、对老师的批评惴惴不安。
在这些朴素的故事中,在这些真挚的文字里,我们总是不自觉地回忆起自己的小时候,那些久违的悲与喜,那些尘封的人和事,忽然就模糊了双眼。
现在的孩子们拥有些什么呢?
等他们长大、等他们老去,拿什么来回忆呢?

◆ 成长小说:影响一生的童年视角
由于家庭或者性格方面的原因,他可能从出生起就是一个独处的、孤僻的个体,经常自觉不自觉地远离群体,时常将自己置于一个寂寞的角落。(张炜《文学:八个关键词》)
我始终没法把《北风啊北风》当作一本虚构的“小说”来看,因为洪浩兄的讲述太过真实,也因为他的很多经历让我感同身受。
因为父亲是被称为“西莱子”的外来户,作为村里极少的姓氏,作者自小就被同伴们当作异类,“小伙伴们常常分成许家和吴家两大营垒,把我排除出去,于是我就成了局外人”。
幼时缺少玩伴,上学后便会觉得大多数同学都很陌生,加之作者不愿意加入任何一个“派别”,就更容易被孤立。
久而久之,这种被动排斥变成了主动远离,“实际上,我是走在一条与大多数人决裂的道路上,而且越是如此,我越感到与别的孩子无话可说”。
正如到外村去念书的那条崎岖小路,象征着那一段踽踽独行的人生历程。
最终走上文学道路的人,似乎注定是要与人群“疏离”的。
因为疏离,他们的目光往往会投向书本,他们的心声往往会诉诸笔端。
“四五岁的时候,我表现出对阅读的饥渴,开始到处搜寻字纸阅读”,甚至“铤而走险”,只为看到外祖母针线笸箩里糊着的报纸——那种饥渴,相信每一个对文字求而不得的人都懂。
五六岁的时候,作者开始给北京的姨妈写信,这是“最初的练笔,姨妈则是我最早的读者”,后来,又受哥哥影响,喜欢上写诗。
最令人羡慕的是,作者拥有一位极具教育智慧的妈妈,一直小心翼翼地呵护着他对阅读与写作最初的兴趣。
涓滴细流,终将汇成江河。

◆ 诗:更多面对永恒的机会
我们与童年结成的关系,是最有力量,也是最强有力、最丰沛的诗性源头。人类的童年与世界结成了单纯的、非功利性的、非成见的纯洁关系,这种关系具有永恒性。(张炜《文学:八个关键词》)
作者郑重地将丛老师对他的评语写进了书中:心地纯洁而善良,为人真诚而文雅;聪慧而且感情丰富,内向所以敏感沉静。
这大概就是诗人的特质吧!
小学时候,得益于吴老师和丛老师对他写作能力的赏识和培养;到了中学,又遇到了诗人朱老师的专业训练,“读与写,将我从贫乏和寂寞中拯救出来,又让我深陷其中不能自拔”,汪洋的诗情倾泻而出:
那青青的麦苗是诗,“妈妈,我不愿踩那嫩嫩的麦苗//因为,因为我的梦在上面缭绕”(《麦苗》)。
那小小的蜻蜓是诗,“妈妈,我的梦//蓝色的//天空的梦//还粘在黄昏的//篱笆上呢”(《蜻蜓的话》)。
童年的嬉闹是诗,“蹑手蹑脚,花枝上捏住了蜻蜓的翅膀//慌里慌张,碰掉花骨朵也要捉住螳螂”(《木槿花》)。
消失的橡树林是诗,“时光的流水冲洗了多少胶卷//记忆,也像飘零的落叶一般//但橡树林却还留驻在我的心底//我至今记得那一片老树的容颜”(《橡树林》)。
当然,还有爸爸的老家,“爸爸的根移到丘陵//在妈妈的村庄扎下”(《爸爸的老家》);还有母亲离去那刻骨的伤痛,“为何你走得一无所顾//你使我有泪流不出,使我//站成荒原上的一棵孤独”(《写给母亲》)。
所有的一切,终将随着成长,“化为澄明豁达的诗意和坚韧的人生信念”,如此,又何惧人生途中雨雪风霜?
你吹吧,冬天的风
愈显俏丽的是梅花
更加坚毅的是青松
苍蝇早已在绝望中僵死
老鼠只能于洞穴里悲鸣
而那些勇敢的人
将在你的呼啸声中
倾听季节的足音
眺望春天的身影
(《你吹吧,冬天的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