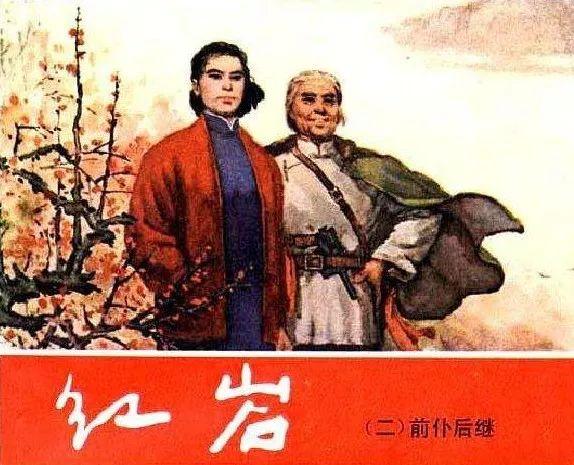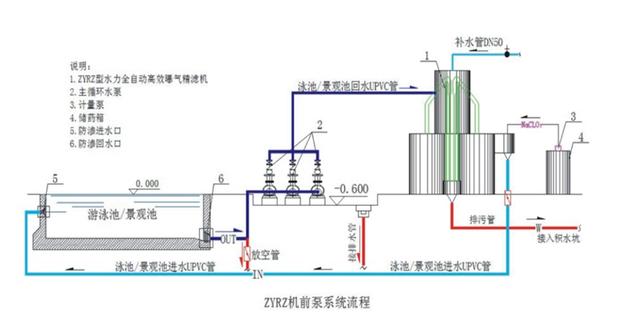教学中的俞丽拿
文 | 徐丽梅
今年适逢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诞生60周年,这首堪称最经典的小提琴中国作品至今在世界各地盛演不衰。而它的首演者——上海音乐学院教授俞丽拿已年近八十,她打算对“梁祝”所代表的人文精神做一个新的诠释。
60年,“梁祝”伴随俞丽拿从一位青葱少女到耄耋之年,如今,她也在细细梳理自己走过的大半生。
一生践行奉献精神

1959年,俞丽拿在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首演中担纲独奏。
“我这一辈子都是围绕着小提琴转的;所有重要的事情都是被分配的,我自己没有主动选择过,都是被动地接受。比如,小时候我喜欢弹钢琴,1951年考入上海音乐学院少年班,成为第一批学生,那时我的钢琴程度已经不错了,但是因为学生专业分布不均衡,弦乐专业学生少,手掌宽的学生都被要求改学提琴,其中,手指细的学小提琴,手指粗一些的学大提琴,我就被分配学习小提琴。”最初,俞丽拿并不喜欢学小提琴——大家都知道,刚开始拉小提琴的声音实在太难听了,但是,做事一丝不苟的性格让她一直坚持用心学习,逐渐喜欢上了小提琴。
5岁读小学,还不到17岁的俞丽拿就上了大学,她和同学们满怀热情地到工厂、农村演出,但是让大家很受打击的是,听众们并不喜欢小提琴——因为那时演奏的大多是外国作品,中国作品太少了,听众感觉和自己的生活、情感距离太远,没有共鸣。
同学们都很苦恼——什么时候小提琴可以讲中国话?学校组成了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尝试把一些民族器乐、民歌改编成小提琴作品,《梁山伯与祝英台》就是在那个期间诞生的。1959年5月27日,“梁祝”在上海首演,后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它随着电波逐渐传播到全国各地。“梁祝”使用了中国人听得懂的音乐语言,它的传播促进了中国人对小提琴这种西洋乐器的了解与喜爱,学小提琴的人也越来越多,由于这部小提琴协奏曲,大家也逐渐接受、喜欢交响乐队演奏。
“梁祝”后来的影响之深远是主创团队始料未及的。俞丽拿说,那时参加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的创作和演出都要牺牲课余时间,投入很多精力,其实会影响自己的学业,但是,那个时代的人创作、演奏都不计得失,也不会想到要给自己带来什么名利。
海纳百川的世界学派

俞丽拿、陈钢、何占豪在一起
从上海音乐学院毕业时,在重要的择业关口,俞丽拿又一次被分配——留校担任小提琴教师。她起初很不情愿——在学校期间并没有系统地学过教学法,她认为,自己只会拉琴不会教学,但是,她的个性是这样——既然组织上让我教学,我就要做好。
“当时国际上是瞧不起我们的弦乐水平的,毕竟我们起步比较晚,那时我下决心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把弦乐教学质量搞上去。”多年来,俞丽拿从来没有教过一个私人学生,从上音附小、附中、本科、研究生到博士生她都教过,她在寒假和暑假都会为学生们补课,不收任何费用。在俞丽拿心中,课比天大,如果学生有课,想让她参加任何社会活动都免谈。
58年了,作为上音终身教授的俞丽拿一直在努力教学。她上课从来不迟到,总是会在琴房里耐心地等着学生。她笑言,“我其实并不像外表看起来那么严肃、那么凶,我从来不会骂学生,但是如果我批评学生的语气比较重了,学生会明白,那就表示俞老师生气了,学生一定会很自觉地改正。”在课堂上,为了更好地启发学生,她有时唱有时跳,有时幽默风趣。
俞丽拿的学生屡屡在国际、国内比赛中获奖,她培养了黄蒙拉、王之炅等一批实力派演奏家。常常有外国人好奇地问俞丽拿,从哪里学的小提琴,俞丽拿骄傲地回答,在上海学的;有人问她是什么学派的,她会骄傲地回答:“我是世界派——我把全世界最好的拿过来学习,我担任30多个世界比赛的评委,从参赛选手身上学到他们老师的教学法。外国人很难想象我们的艰辛,因为国外的音乐学院是把最好的学生留下来担任教学,而我们不是,一切都要靠自己摸索前进。”
她很自豪地说,中国人现在可以把小提琴拉得很好,培养出不少具有国际水平的学生。她分析,中国小提琴教育的过人之处在于,把一些才能只是中等的孩子培养成可以靠小提琴为生的程度。“我们教外国作品其实有文化隔膜,要花费很多精力分析外国作品,很困难。我们拉巴赫作品的水准,和外国人拉中国作品的水准相比,应该说是高得多。”
一句话让她坚持三十年

上海女子弦乐四重奏
俞丽拿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几十年如一日,她有一股特别认真、执着的精神。
1960年,她与丁芷诺、吴菲菲、林应荣组成上海女子弦乐四重奏,与文化部组织的出国比赛团体一起去德国,参加第二届舒曼国际弦乐四重奏比赛并获奖。当时国内还没有固定的弦乐四重奏组合,在获奖回国之后,团长李刚说:“你们回去之后不要散啊,否则中国就没有弦乐四重奏了。”这句话让俞丽拿坚持了三十年,其间,其他声部由于各种原因都换过人,只有她一直担任第一小提琴,坚持利用课余时间练习。由此,上音建立起重视室内乐训练的传统,不论是钢琴重奏还是弦乐重奏,对学生每学期都有重奏的分数要求,达不到要求不能毕业。
她回忆,那时大家工资都不高,到外面演出没有任何经费支持,还要自己负担各种费用,即便如此,大家还是坚持弦乐四重奏的排练、演出。经过了几代人努力,中国的室内乐开始发展起来了,俞丽拿却决定退出了——毕竟其他声部的人已经不是同代人,应该激流勇退了。
让小提琴说中国话
俞丽拿演奏小提琴协奏曲“梁祝”
“梁祝”脱胎于越剧,在小提琴演奏中的一些滑音要学习戏曲中二胡的演奏方法,它表达的是中国人含蓄的、欲说还羞的爱情,想要很好地表达出那种特有的韵味比较难。在17岁时第一次演奏这样的曲子,没有人能教俞丽拿,她只能向中国的民族音乐学习,她演绎的“梁祝”情感细腻丰富、表达真挚,被公认为最权威的演绎之一。
在俞丽拿看来,不会演奏中国作品就等于不会说中国话。在她的推动下,上音附小、附中、大学的学生每年考试都要演奏中国作品。
为了推动小提琴中国作品的创作发展,1993年,俞丽拿小提琴艺术基金会筹资的100万元征集小提琴中国新作品。不过,从当时征集到的作品来看,并没有能够超越“梁祝”的新作品,俞丽拿感到颇为遗憾。但她转念一想,等到天时地利人和、所有机缘成熟时,自然会有更好的作品出现,自己只要尽力了就好。
创新“梁祝”诠释中国大爱

“梁祝”讲述了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但俞丽拿认为,在新时代,它所表达的含义更丰富,比如,中国人有一种为了大事业牺牲小我、成全大爱的奉献精神。那么当代人怎样看待“梁祝”?俞丽拿组织了一个创作团队,选取了三个不同时代为了家国而无私奉献的故事,创作了音乐剧场《真爱·梁祝》。她说,“我们这一代人就是这样,会为了国家需要的事业全身心地付出,我理解的爱国就是把自己的事业做好。”
除了弦乐之外,《真爱·梁祝》加入舞蹈、舞台剧、音乐剧等富有当代气息的艺术表现形式。在该剧最后一部分,俞丽拿的弟子、上音小提琴教授王之炅与中国爱乐乐团演奏“梁祝”的经典旋律,而俞丽拿本人也会上台演奏一段。自从70岁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举办了告别舞台的音乐会之后,她再也没上过舞台,“我觉得在自己状态还不错的时候告别舞台很好,至少给大家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我不想以后让别人说,这个老太婆怎么还霸着舞台呢。”
母子情深系“梁祝”
“妈妈,您别再这么累了。连续11个小时教琴已经不适合您这个年纪了。”在一个文化论坛活动中,钢琴家、指挥家李坚对俞丽拿说。他发现,年迈的母亲仍然全身心铺在工作上,就在不久前,她因为肺部感染住院治疗,出院后马上又投入到《真爱·梁祝》的策划之中。
俞丽拿坦言,自己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到事业中,对家庭的照顾不够。以前她并不想把儿子李坚培养成音乐家,因为他上小学时正处于“文革”期间,那时,音乐学院都停课了,俞丽拿也陷入困惑——音乐还有用吗?音乐家的未来会怎样?当时小学每天下午没课,担心儿子到处跑学坏,她就用钢琴和小提琴把儿子的课余时间填满。“我一生的习惯就是,要么不做、要做就必须认真完成,严格地要求淘气的儿子每天保质保量地练琴。”
俞丽拿还记得,1976年1月,李坚因为伤口感染患败血症,被送到医院里急救。她在病房里等着抢救儿子,听到周总理逝世的消息,心情更加难过。痊愈之后,李坚好像突然长大了,出院回家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弹钢琴。
“儿子的天赋比我好,当年的钢琴老师就建议他一定要报考音乐学院。”虽然合作过上百次,但作为风格、性格迥异的两位音乐家,母子俩在艺术观念上有很多分歧,儿子自认为是最懂母亲的,而母亲感觉儿子的很多观念难以理解。在2009年之前,俞丽拿和生活在国外的儿子见面多半是因为要合作演出“梁祝”。
时光如白驹过隙,倏忽间,一个甲子过去了。儿子也回国定居十年了,俞丽拿感到这一生很充实。她的琴声又将随着音乐剧场《真爱·梁祝》、随着蝴蝶翩迁继续流光溢彩。
版权声明:本文摘自音乐周报,作者Music Weekly,仅供参考、交流、学习等非商业目的。转载的稿件版权归原作者和机构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删除,谢谢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