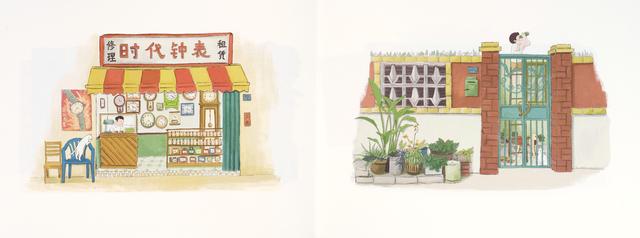“粽子香,香厨房,艾叶香,香满堂。桃枝插在大门上,出门一望麦儿黄。这儿端阳,那儿端阳,处处都端阳。”
但凡国人都知道端午节有诸多习俗,比如包粽子,买艾草菖蒲插门来避邪,饮雄黄酒,赛龙舟,但少有人知道端午也叫端阳,少有知晓过去传唱有这么一首歌谣。我喜欢端阳这一说法,有一点煦暖的味道,我喜欢在古旧的歌词中回味端阳的气氛,我想在记忆的点点滴滴中领悟端阳对于我们存在的意义。
盼过节其实是期盼美食。虽然老师也会在课堂上讲到端阳的来历,讲到楚国诗人屈原,告诉我们楚国百姓为了不让大鱼吞食诗人而把做好的粽子丢入江中的做法,可是对于几岁的孩子来说实在是有些遥远而模糊,在校读书的我最想过节的是胃,最温馨的是写完家庭作业后看奶奶包粽子,奶奶会在端阳前三天赶早去菜市场买来新鲜粽叶,把叶片放在瓷盆里用井水泡湿,再用淘了几遍的白白净净的糯米装在青绿色的粽叶里,有的糯米里加红豆或绿豆,有的加咸肉和甜枣,还有的干脆什么也不加。裹紧之后,再拿细麻绳扎好。我托着下巴在一旁看着,也想尝试包两个粽子,给奶奶当帮手,可奶奶总不让我插手,让我安心写作业。一般奶奶要忙一个下午,在厨房和厅堂之间的过道来回穿梭,留下缓缓移动的背影。从中午吃过饭开始裹粽叶,到四点钟就能全部包裹,奶奶在厨房锅灶里先架大柴把水烧沸,再用文火慢慢把粽子煮熟煮透,整整一大锅粽子的香气溢满厨房,溢满庭院,溢满奶奶的脸上。放学归来的我饥肠辘辘,像小馋猫一样守在厨房门口急不可待地要尝个鲜,奶奶怕粽子里的肉没熟,就用筷子先挑出两个甜枣粽子给我,我也不怕烫,扯开麻绳,剥开粽叶,狼吞虎咽起来,两个粽子下肚后,齿颊生香,连晚饭也不想吃了。
在外求学、参加工作的十余年间,如果不能回家过节,就和朋友一起去超市里买一些现成的粽子回寝室煮着吃。工业化的生产使得粽子四季皆有,供不应求,品种丰富繁多,包装更精致好看,但是对我而言不过是没有温度没有温情的食品,是可以无限复制的成品,它可以充饥,但不可以慰藉乡愁。就像现在大量印刷的春联固然便捷实用,却无法替代自己用毛笔写的春联,印刷品终归与心灵隔了一层。长大后的我不再那么嘴馋,奶奶过世后,我和家人包粽子的心情与兴致没有了,我凝望烟霭迷蒙的山岚,看到奶奶手上半个多世纪的老茧,浑浊的双眼,零乱的白发,满是沟壑的额头,而是那个想象的矮矮村庄里,青白的炊烟慢腾腾地升起,远空有一只不归的候鸟。
参加了工作阅历后,我渐渐把过节理解为追念故国文化,寻找精神图腾的方式。作家汪曾祺说,民俗是一个民族的集体抒情诗。正是极具文化感的仪式和极具象征意义的物象。使得后世族孙不管相隔多久相距多远都能获得共同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从而深耕脚下土地,仰望阔远天空。重商主义的时代,万众狂欢的背景,人人争着出名谋利益,追风逐浪,冷眼向洋看世界,世相滔滔,沙泥俱下,年轻人似乎很难贴近汉语的创造者,文化的守护人。提及屈原,提及曾经上下求索的人物,往往是一脸茫然,漠不关心。重读《史记·屈原贾生列传》,重读长诗《离骚》,我似乎又走近了屈原那愁痛惨怛的一生,遥想两千多年前屈子行吟泽畔、怀石投江的场景,顿生一种既遥远又切近的感觉,既悲怆又温暖的感觉。他是一盏点了千年的煤油灯,烛照长夜,烛影摇曳,他的名字就像是滚滚江河里的一朵晶莹的浪花,他的故事是我们民族生命的远歌。
精神的传承是割舍不断的。我们常说,一个人要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到那里去,一个人不能忘本。走近屈原,走近端阳,就带有一种强烈的寻根情怀。无论时空怎样改变,社会怎样变迁,只有信守汉魂唐魄,才不至于在汹涌而来的大潮中迷失方向,迷失自我,才有可能走得更远,走出一片更为灿烂的风景。想起一位诗人为端阳写的一首小诗,读懂了它才能读懂自己,读懂我们这个民族。
“你埋下一坛老酒/酒坛上是一张红纸/沉沉地写了一个黑字“魂”/每当汨罗江悲怆的日子来临/这酒坛就溢出芦苇的清香/激荡起亘古不变的激昂/几千年了/喝了这坛酒的人/都醉成了龙的脊梁/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