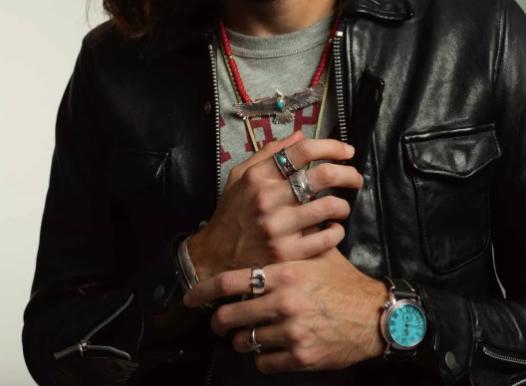叶少兰 /文
“音配像”是一项伟大的文化工程,它为京剧事业的振兴发展,为京剧剧目的挖掘、拯救,包括为京剧人才的培养所产生的效果和作用,都是难以估量的。它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越是历史地看“音配像”,越能发现这项工程的伟大。这是一个绝妙的构思,一次空前的文化创举。尤其对我们京剧工作者来说,一提起“音配像”,每个人都会身有所感,都会非常地激动。

1961年 ,叶盛兰教叶少兰练功

难得的机遇
“音配像”前前后后加起来近30年了,从1994年正式启动算起,也有20年了。1985年,李瑞环同志在天津做市长的时候就开始筹划酝酿“音配像”,并作了一些尝试。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是后来才听说的。1994年“音配像”正式启动的时候,张君秋先生、谢国祥先生,还有马崇仁先生、迟金声先生、张学津先生都参加了。后来邀我录《四进士》,我从此就投入了“音配像”工作。也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开始跟瑞环同志有了接触并日渐相熟。
《四进士》是“音配像”正式开始后录制的第一出戏,袁世海先生、张学津先生也都参加了。这出戏是试验性的,不是给前辈的录音配像,而是我们自己录音,录完音再由我们自己配像。这个戏录得很成功,后来紧接着又录了杨派的《杨家将》。我第一次正式录的“音配像”是四个折子戏,其中一个就是我为父亲叶盛兰配的《罗成叫关》,这也是我配的第一个戏。
从一开始参加“音配像”,我就非常地珍惜,非常地重视,总觉得时间宝贵,应该争分夺秒。再看导演、摄影师、全剧演职员反复录制,大家都挺辛苦。为了争取时间,我上午个别场次排完之后,虽然很累,但为了不让大家久等,我不是卸掉脸上的妆到饭店吃饭或回家休息下午再来,而是在休息厅找个长条凳子,裹一件胖袄躺会儿,饿了就吃点馒头。张君秋先生看到了以后,很受感动。
令我难忘的是录《打侄上坟》。《打侄上坟》也叫《状元谱》,是一出穷生戏。我父亲在解放前经常演这出戏,多与马连良先生合作,解放以后多年不再演。1960年,父亲在中国京剧院一团的时候,和李少春先生在天津演过一次。我还记得演出以后父亲对我说,这个戏演得非常好,观众反响很热烈。这是父亲和李少春李先生第一次合作,李先生也只演过这么一次。李先生不愧是大艺术家,一点儿都看不出来是第一次演,真是炉火纯青。这出《打侄上坟》也是余叔岩先生的拿手戏,李先生宗余,所以他唱得余味十足,非常正宗。
“文革”开始后,不可能再让演这样的戏,这次演出就成了“绝版”。有一位曾在天津电台“支左”的同志告诉我,天津电台有这个录音。那时候刚刚破完“四旧”,这种录音说扔就扔,扔了就再也不会有了。我想方设法通过私人关系从内部秘密录了一份。这在当时是相当冒险的,让人知道了,这不是“复辟”嘛!而且万一追查起来,也会给好心帮忙的人招事儿。
听着这个录音,我真是特别地激动,特别地兴奋。光听录音就能听出戏来,就跟看到了一样。这样好的表演、这样好的唱念,我觉得真是精品!我早年在戏校学习的时候学过这出戏,是跟萧连芳先生学的。我父亲也跟萧先生学过戏,老先生的穷生戏非常拿手。后来我在戏校做老师,为了教这出戏,又跟我父亲学了,但就是一直没有机会演。我多么盼望有一天让再演这样的戏,还能复原这出戏!所以,“音配像”的时候,我就提出有这么一出《打侄上坟》,希望能到天津电台找一找,要是有最好,没有的话我这儿有。结果,有关的负责同志果然找到了,后来我就照这个录音配了像。
为录这出戏,我下了很多功夫。尽管我经常听录音,印象很深,尽管我会这出戏,但是,在录之前,我还是天天跟着录音排练,可以说练到了跟录音严丝合缝。我是和谭元寿先生合作,我为我父亲配像,他为李少春先生配像。谭先生经验丰富,我也听得多、练得多、吃得透,这出戏配得非常成功。无论是张君秋先生,舞台导演迟金声先生、马崇仁先生,还是录像的导演们,以及同仁们,所有的演职人员都特别满意。尤其是瑞环同志,他看了以后特别高兴地说,听这个录音都能听出戏。他还说:什么叫大师?什么叫表演艺术家?就是不一样!

1985年,叶少兰赴美讲学期间在京剧形体艺术课程中教“洋学生”
录了《打侄上坟》之后,我录的其他几出戏也得到了瑞环同志的肯定。我还接到大家的一些反映,都评价很好。一块儿工作的同仁们、老艺术家们,特别是很多的戏迷观众,都觉得很满意,觉得我配的这些戏还是有谱的、有质量的。瑞环同志对我非常鼓励,觉得我很认真,很负责任,对“音配像”特别珍惜、重视。他说:“我这里接到很多信息,对少兰给他父亲的配像是一致肯定的。今后叶先生的戏,都由少兰来配。姜妙香先生的戏,少兰学过,也多配一些。”

小生艺术的新生
我确实对这个机会极其珍惜、重视。要没有“音配像”,我父亲的这些戏一出也留不下来,全得失传。没有“音配像”,叶派戏、小生戏就都没有了,是“音配像”救了小生这门艺术。
我们这个行当跟其他行当不同。小生这行出人才难,要求的条件太高。小生首先是真假发声的方式,比其他行当的表演要夸张。顾名思义,小生是表现古代青少年的,既有周瑜、吕布这样的将军统帅,也有张生、梁山伯这样的书生才子。小生的表演要能文能武,剧目不同、人物不同,表演也不同。所以,小生这行很难,对气质要求很高,要有朝气、漂亮,要儒雅、清秀,要表现武将还一定要有英武气。要是没有气质,上去以后观众就不喜欢。气质不是挑眉立目,不是瞪眼使劲,气质是内涵、是修养,是内在流露出来的,不是外在装出来的。小生还有一个声腔的问题,既不能脂粉气、像女孩子,又不能像大嗓的老生,要真假声结合,还得悦耳好听、宽厚圆润。有好的假声还不够,得会唱、会念、会表演,观众才喜欢。
小生这行本来出人才就难,历史上又中断了十几年。从1964年京剧现代戏剧目汇演开始,小生这个行当就没了,“文革”时期更不用说。其他的行当,现代戏、样板戏都能上,唯有小生不能上。“文革”当中,曾内部组织录制过好几十出京剧传统戏电影,我父亲那时候身体还可以,但是因为政治原因不许他录,结果闹了不少笑话。最有意思的是录《白门楼》,谁录的不知道,但这可是我父亲的代表剧目。戏里有一句台词是“内侍臣看过了皇封御酒”。结果弄好字幕排成了电影,这些人还是说不好准确的台词是什么,最后无可奈何去问我父亲。父亲一看,他们把“皇封”给写成了“蝗蜂”,把“御酒”写成了“玉酒”。我父亲说,这个不对。这才改过来。“文革”对父亲和叶派艺术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损失。我父亲留下来的就只有一部《群英会》的电影。要是没有这个电影,我父亲一个影像资料都没有,这要感谢北影。
“拨乱反正”之后,刚恢复传统戏的时候还是老生或武生代替小生,又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才恢复小生。我为了重振叶派艺术,真是争分夺秒、日以继夜地干,尽力让自己多演戏,多培养接班人。但是,如果没有“音配像”,我再怎么努力也演不了“音配像”中的40多出戏,也没有机会让我演这么多。我演不了,这些叶派的代表剧目就不能跟观众见面,后面的接班人也无从学起。这些录音长时间散失或封存,慢慢也就会毁掉或失传。有了“音配像”以后,观众不仅看到了许多以前没见过的戏,像经常见的《赤壁之战》《西厢记》《玉簪记》《蝴蝶杯》《桃花扇》《罗成》《打侄上坟》《金田风雷》《白蛇传》《柳荫记》这些戏,观众看后也反应非常热烈。大家听到了我父亲当年的精彩录音,了解到了我父亲创作的叶派戏。我父亲当初是怎么创作的,戏是怎么设计的,怎么穿、怎么戴、怎么表演、用什么身段……观众一看:原来这就是叶派艺术,真好啊!瑞环同志跟我说,你父亲的戏非常好,他的资料,只要能找到的,有一出录一出。正因为有瑞环同志的重视,我父亲和姜妙香先生的小生表演艺术才能得以传世。

补录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音配像”首先要挖掘、整理录音资料,这是一个非常艰苦的大工程。这些录音大部分早就无案可查,谁都不知道在哪儿,中央电台的很多资料是通过内部退休的老同志,或其他各种线索找到的,其中有的在破“四旧”时被人为地破坏,有的丢失,有的因保存条件不好受潮甚至被雨淋水泡,损失很大。为了使用好这些得来不易的宝贵资料,就得用各种现代的技术进行保护性的处理,重新编辑、剪接,把能用的录音提炼出来,再进行去噪、还原。我录的我父亲和程砚秋先生的《玉堂春》,是1945年父亲在上海天蟾舞台的演出录音,这个资料非常宝贵。用的是钢丝录音带,一是不清楚,二是声音太小,另外还有金属声。我们做录音的时候非常艰苦,一字一字、一句一句地调音。先把音提起来,提大以后噪音也更大,完了再去噪,做到既要去掉噪音,还不能让演员的声音失真。现在再听,还会觉得跟今天的录音相差很大,可这已经是千方百计费了很大功夫了。

1980 年,叶少兰在《白蛇传》中饰许仙,许嘉宝饰白素贞
另外,因为录音的年头太长了,有的地方短几句,有的地方短一段,这怎么办?我就得设法录音添补。我父亲跟杜近芳的《白蛇传》,现在听“音配像”的录音,和剧场实况一样,那可是多少张唱片接成的!当年录唱片不可能全剧都录,而是以唱和主要的念白为主,这样的话,有些锣鼓比如上下场的、武打的,还有念白多的场次就被掐掉了,像其中的《盗仙草》《金山寺》,这两场除去前面白蛇、青蛇和法海的对话念白以外,没有什么唱,结果整场的录音就没有,《游湖》的结尾、《结亲》、《说许》、《逃山》,唱片中都没有,还得由杜近芳老师和我补录。可又要做到尽量听不出来是后补的,这就要自己去下功夫。好在我见过父亲是怎么演的,也跟父亲学过,对父亲的念、唱,我有一定的把握。可是,即便这样,我还是得反复听父亲的录音,领会念白的劲头、语气、感情,声音、声调的轻重缓急,等等。剧目不同,念白也不同,得从人物出发、从剧情出发。为了补好一段录音,我要不断地用功、反复地训练。
唱、念如此,缺的音乐锣鼓同样也要这么一点一点地补。现在的舞台演出,声音的音质、音色跟当年的录音都不一样,但现场乐队还是要尽量接近、还原录音资料,工作难度可想而知。比如打击乐,光是锣这一种乐器就不下十几种。锣又分很多不同的用法,相应的,在锣的制作上就有很多讲究。戏的情节不同、人物不同,用的锣也不同。相对来说,文戏用的锣比较大一点、薄一点,声音低一点。武戏多用虎音锣,其中又分低虎锣、中虎锣、高虎锣。比较激烈的武戏要用高虎锣,这种锣的中心比较小,调门比较高。所以,京剧作为一门国粹艺术非常之讲究,不是有个锣就行,而是有要求、有标准、有门道。乐队要补好一段音乐,得跟原来的录音接近,不能突然跳出去,当然纹丝不差也不现实,但是得努力做到,包括音乐的节奏、调门,原来录音处理的效果、感觉,都要尽量贴近。乐队得反复听,得跟着排戏,了解戏的内容、感受表演的风格,再根据戏的要求来处理,这些都要下很多功夫。
比如,《罗成》这出戏的武场多,也缺少音乐锣鼓,演员和乐队都得先把这个戏吃透。对我来说,比如这个起霸有多长、我父亲当时是怎么起的,那个四击头打在什么动作上、动作是怎么走的……了解了以后还要练准确,然后再去补锣鼓。补锣鼓不能是在录音棚里弄一个大概齐,按四击头的程式走一个动作、打一个锣鼓就行,配像演员得能走出与老艺术家当年演出一样的动作,锣鼓也得是当年的样子。所以,补出一段完整的录音,无论是演员、现场的乐队还是做录音的技师,都要一遍遍地反复打磨。我记得《罗成》这个戏,就一个起霸,大小动作反反复复,我在录音棚里走了有50多遍才接好这一段录音。

“音配像”锻炼了京剧队伍
录音找到了,也通过各种现代技术基本还原了,可还是只能听。可京剧是要看的,它跟听说书的不一样。一出戏,怎么勾的脸?戴的什么盔头,穿的什么行头?身段怎么做的,武打怎么打的?都是老生,为什么有马谭杨奚不同的艺术风格、艺术流派?都说马连良先生非常潇洒,怎么潇洒?“音配像”这些前辈老艺术家的表演,现在年轻一点的演员根本都没见过,更甭说观众了。让观众爱京剧,得先让他见到,才能影响他、吸引他。所以,为这些录音配上像就是非常核心的一步。
“音配像”对我们配像演员来说受益匪浅。通过“音配像”,我的表演更加成熟了。虽然之前大家就认为我是一个知名的演员,能独当一面,但是我得诚实地说,没有“音配像”,我演不了这么多戏,也没有机会演这么多戏。我录的这些戏,原来都学过,但有的没演过,有了“音配像”,我就能穿上、戴上,全本全出地演下来。
对于青年演员来说,“音配像”更是难得的机会。所以,我父亲的戏,我也请我的学生录了几出。《佘赛花》是李宏图录的,现代戏《白毛女》是江其虎录的,《十三妹》是宋小川录的,《雅观楼》是靳学斌录的。这对他们是一次锻炼,是接触叶派、理解叶派的好机会。当然,每录一出戏,我都先辅导,讲解每出戏的艺术要点和风格特点,还有表演、动作、舞蹈、位置,以及唱、念的技巧。瑞环同志希望我承担更多的剧目,也主张说如果学生的条件很好,有相当的水平,在老艺术家的指导下,有适当的剧目也可以录。特别是有的艺术家年岁大了,形象不如年轻演员好,可以让学生来录。我的这几位学生,条件都很好,也很努力,他们都在戏中发挥了各自的特长。像《雅观楼》这出戏,我父亲当年在人民剧场作为展览演出的时候,大家伙儿都站起来鼓掌,连李少春先生都站起来,就这么精彩。我虽然学过这个戏,父亲教过我,茹富兰先生也教过我,打下了挺扎实的基础。但是我当时快60岁了,虽然也能踢腿、能扳腿,但是说还跟20多岁时一样,不太可能了,还是让自己的学生录更好一点。靳学斌就很适合,因为演这出戏得腿功好,身上得利索。录之前,除了我教他,又请了茹元俊先生精心地加工指教。
“音配像”不仅锻炼了演员,对其他方面的人员也是这样。比如搞录像的导演、技师,以前哪有机会录好几百出的戏?京剧演出不好录,不像电影的分镜头,要通过展现演员的唱念坐打武表现全剧、表现故事情节。而且,台上这么多主、配演员,怎么使用镜头才能让观众看到一出原汁、原味、原貌的戏,这都非常重要。录“音配像”的导演阎德威先生,现在都已是录制戏曲的专家,今天再来录新编剧目的演出,质量都非常高。此外还有美术、服装、化妆、音乐、道具、舞台布置、剧务,包括录音制作、编辑、整理……十几年的“音配像”,锻炼了跟京剧有关的方方面面的队伍,尤其是全国各院团和相关部门的团结协作。

不仅救戏,而且救人
“音配像”并不只是复原了400多出戏,更重要的是,它再现了京剧前辈艺术家敬业勤业、勤学苦练、艰苦奋斗的精神。“音配像”不仅让我们听到了前辈艺术家的录音,更从中听到了精神,所有参与其中的演员都深受教育。前辈的艺术这么讲究、这么细致,我们真觉得自己还差得远。京剧是国粹,就因为它的讲究,唱念做打舞手眼身法步,化妆、服装、脸谱、道具,一腔一调……无不如此。不同的人物有不同的行当,有不同的走法、指法、舞蹈、动作,处处体现着细致。有的演员乍听觉得容易,以为排一遍就齐了,其实差远了,绝不是一听就能达到的。我见过、学过、演过都觉得差距大,照样要跟着录音一招一式、一腔一字地学,去悟道,何况没见过、没学过、没演过。凡青年演员参加录像,瑞环同志都要求安排经验丰富的本行艺术家手把手地指教。
另外,什么叫“一棵菜”?通过“音配像”我切身感受到前辈艺术家的这种精神。听《蝴蝶杯》的录音,只大衙的一个公堂,哪怕是一个小花脸的小院子都演得非常讲究,更别说花脸、旦角、老生、小生这些主演们了。这就是“全梁上坝一棵菜”,体现在台上,体现在了艺术上。

2009年,叶少兰在《群英会》中饰周瑜
我从小就跟着父亲边看边学。直到现在,我每演一次《群英会》,之前都会看一遍我父亲的影像资料。这个电影,每看一次我都会有新的感受,真是感到学无止境。我演的不计其数,演一次看一遍,还默默复习我父亲当年是怎么手把手教我的,怎么给我说的。如果只看个大概齐,那根本就没会。学会了不等于学对了,想学对可难了。这次的“音配像”就教育了演员们:不是光学会,而要学对。对不了就是功夫不到,还有是修养不到。
我为老师姜妙香先生也录了几出。给姜先生配像,对我来说又是一次再进修、再复习的机会。姜先生教过我八年,我在戏校学戏的时候,姜先生已经是中国戏校的正式教员。我毕业前跟姜先生学,毕业后还是追随姜先生,跟他学的戏非常多。想当年姜先生教我们非常耐心,一堂课几十遍满宫满调地唱,身段也全都走出来,跟在舞台上一样。“音配像”不但是复习老师的戏,也让我不禁回忆起老师教课的情景,对我也是一次激励。我给姜先生配的戏,都是他当年手把手教我的。比如说《奇双会》,我跟我父亲学过,也跟姜先生学过,又跟俞振飞先生学了一遍。在跟梅葆玖先生录这出戏的时候,我配姜先生,梅葆玖先生配梅兰芳先生,我就是按照姜先生的路子来。《穆柯寨·穆天王》也是梅先生和姜先生的戏,这出戏我跟姜先生学过,我给姜先生配,给梅先生配的是董圆圆。

“音配像”是在瑞环同志亲自指导下完成的
瑞环同志在全国政协做主席的时候,我就开始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到现在已经有五届了。瑞环同志为人非常正直、朴实,处处有工人阶级的本色。他从小就好学习,非常喜欢看书。那时候家里头比较苦,一次要过年了,他母亲给他一点钱让他去买油条包饺子。他却在书摊看上了一本书,恋恋不舍,最后拿买油条的钱买了书。对他来说,看书比油条、比过年吃饺子还重要。做工人的时候,大家下了工都很累,别人都睡了,他却在电线杆底下借着路灯的灯光看书,或在蚊帐里打着电筒写笔记。瑞环同志没上过大学,但是,这种争分夺秒的求知精神,我瞧着要比上过大学的还抓得紧、摄入的知识还多,何况他还有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瑞环同志在当工人的时候就是全国闻名的劳动模范,有“青年鲁班”的美誉。那时候我还在上学,谁不知道“青年鲁班”啊!他是当时青年人心目中的模范和榜样。1959年铺设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的人字地板,从设计到制作、安装,全是他带着做的。十几年前重新整修的时候,还得再去请教他。
上世纪50年代,瑞环同志经常在工会给工人讲历史课,甚至给中学老师也讲过。他讲完课就到旁边的北京工人俱乐部看戏,看马连良、谭富英、张君秋、裘盛戎、赵燕侠等名演员的演出。瑞环同志看的戏不比内行人看得少,生旦净丑各个流派都爱看。他不光看戏,还和很多艺术家成了好朋友。他不是看完就完,还喜欢研究。“文革”前后京剧是怎么发展演进的、演员是怎么成长的、流派是怎么形成的……对他来说犹如身临其境。所以,后来抓“音配像”的时候,他对每一出戏的剧本、每一出戏不同行当的表演、每一出戏的特色和标准,都了解得非常准确、深透。大家都说,瑞环同志谈起戏是个内行,所以才能有“音配像”这样的创意规划及指导。
瑞环同志对于我们民族文化事业的传承可谓是尽职尽责。他一不是唱戏的,二不是演戏的,只是一名京剧爱好者。他跟大家一样地热爱民族文化,但是他不是出于娱乐,也不是出于爱好,而是从传承民族文化事业的高度关心京剧的发展。经过十年“文革”,民族艺术遭受了重大损失,眼看京剧面临剧目断档、演员断档、观众断档,国粹艺术正在流失、濒临失传,瑞环同志非常焦急,甚至比我们干这一行的还要焦急,于是有了“音配像”这个绝妙的创举。
“音配像”是一个非常庞大复杂的工程,比如说,“音配像”首先需要挖掘资料,这可不是那么容易。谁手上有这些资料?即便有,人家凭什么肯拿出来?任何一个剧院、剧团,任何一个演职员都没这个能力。这些资料不光来自电台,还包括全国各地的音像机构甚至私人珍藏。有的人早年间有录音的条件,自个儿录下来了,听说瑞环同志抓“音配像”,觉得真了不起,出于佩服和感动,就主动把保存多年的资料拿了出来。这就是人格的魅力。还有,提供出来的录音,由谁整理、怎么整理?人力、物力从哪儿来?瑞环同志都会亲自过问。20年前,且不说整理这些资料,就是复制一段录音也是要收费的。大家的经济条件都有限,谁也不会有这个钱。
另外,在整个的京剧界乃至戏曲界,大家伙儿都对他服气。为了京剧艺术,他不遗余力,废寝忘食。“音配像”期间,他一个剧本一个剧本逐字逐句地校对,跟以前的版本作对比,力求原汁原味,把精华点点滴滴都再现出来。原创这出戏的老艺术家不在世了,就请亲传弟子,请见过的、学过的,还有当年合作过的老艺术家,把这些人凑齐。还要保证他们在最好的表演状态下,把这出戏原汁原味、保质保量地留下来。即便是有些老前辈已经力不从心,达不到当年的水平了,也要教给年轻演员,用相当的时间指导、训练,达到一定标准才能录。所以,别看有原配录音,“音配像”每排一出新戏,都艰苦得多。“音配像”不凑合、不迁就、没有人情,是为了留下最好的资料,把艺术精华传承下去。
“音配像”这样一项庞大复杂的工程,需要所有参与者的无私奉献,瑞环同志做到了身先士卒。他是国家领导人,每天已是日理万机。可他觉得国粹艺术是我们民族文化的代表,不能在我们这一代垮掉。瑞环同志没有门户之见,不管哪一行当,生旦净丑,只要哪里有资料,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要求千方百计、不惜一切代价去挖掘、寻找。工作再艰苦,也要把录音整理好。还要选最合适的演员配像,把戏的质量完全表现出来。处处精益求精,处处把功夫下到家。
“音配像”不但挖掘出宝贵的资料,将这些资料配像、再现,也让健在的老艺术家们焕发了青春。刚听说要搞“音配像”的时候,老艺术家们都非常兴奋,工作热情特别高,他们不讲名、不讲利,风里来雨里去,全身心为这项事业奉献着。对这些老艺术家,瑞环同志不是召之即来,“通知你你就干”,而是事无巨细,关心得非常周到。事先要派工作人员到家里探望、了解健康状况,征求老艺术家的意见,看能不能排戏、或能不能给青年演员排。征得同意之后,还要把方方面面都安排好、照顾好,比如排这一折戏要一天的时间,老艺术家来了,排了半天,说精神不太好,那就马上让休息。那时候租场子是要花钱的,还有演、职等各个方面,都是需要钱的。但是,瑞环同志为照顾老艺术家的健康,宁肯不排,也不让坚持。甚至是老艺术家的饮食起居,瑞环同志也都亲自关心。对他们的伙食标准从不作限制,一切以保证健康为重。每个人家里有什么困难也都关注着,随时帮着解决,让这些老艺术家们感到特别温暖。
“音配像”工程阵容浩大,前前后后共有百余家单位三四万人参加其中,涉及全国各地院团的演员以及舞台、服装、道具、音乐等方方面面的专业人员。这么一个宏伟工程,瑞环同志没有用国家的专项经费。这几百出戏,从挖掘、整理录音,到排戏、录像、合成、制作,都是来自支持、响应“音配像”事业的热心捐助,甚至海外、港澳的爱国人士也纷纷伸出热情的援手。由此可看出瑞环同志的号召力,以及大家对他的敬重、支持。

感恩与敬仰
对于“音配像”,我一直带着感恩的心情。我要为父亲争气,为小生艺术争气,所以我倍加珍惜这个机会,刻苦练功。我不是要求自己努力干,而是拼命干。是带着感恩、敬仰之心参加“音配像”的。
我感谁的恩?一是感我父亲的恩。没有他的成功创作,没有他这些经典的录音,就谈不上我今天的配像。父亲是叶派小生的先驱,是他的这些剧目创出了叶派这门经典艺术,我们是踩着前人的肩膀上前行。所以,瑞环同志说,“音配像”就是尽忠尽孝,尽孝就是对前人尽孝,尽忠就是对京剧事业尽忠。
再一个是感瑞环同志的恩。没有他的创意、指导,这460出戏就没了。他不光有创意,还能给出具体的方法。从什么样的戏开始录,每个阶段分别录什么样的戏……非常了解京剧的艺术规律,这很了不起。另外他还有很科学的管理,在进展紧张的时候,能让各方面的工作同时有序进行、全面铺开。
另外就是敬仰之心。一是敬仰京剧艺术。京剧艺术博大精深,前辈艺术家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财富,瑞环同志认识到了,我们是从业人,更得认识到。前辈艺术家的这些创作,真是千锤百炼的艺术精品,丢了太可惜了。所以,我是带着对京剧事业、对前辈艺术家、对我父亲开创的叶派艺术的敬仰之心,参加“音配像”的。
另外还有对瑞环同志的敬仰。如果没有“音配像”,该是京剧多大的损失!从1994年正式开始到现在,张君秋先生、袁世海先生、张学津先生……多少位参与其中的艺术家离开了我们!像张学津先生录的马连良先生的戏,录得真好。如果没有录下来,不要说马先生的资料丢了不能复原,张先生去世了,现在青年的老生演员没人见过马先生演的这几十出经典剧目。而且,越往后越是如此。再过若干年,连我们这些人也都没了。就像瑞环同志说的,过50年后再看“音配像”的成就。50年以后,参加过“音配像”的一些青年演员也不一定在了,可这些艺术精华永远留下来了。
瑞环同志对于京剧事业的发展,对我们京剧演员,真是恩重如山。正因为如此,我和其他同志一样,争分夺秒、日以继夜地干。“音配像”后期,瑞环同志还让我负责当年国家京剧院四大头牌——我父亲、杜近芳老师、李少春老师、袁世海老师的若干戏,除了录像,还做些组织工作和排练工作。后来又请我和天津市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的领导叶厚荣同志,到上海专门组织完成周信芳先生的十来出戏。这是对我的信任,我非常投入地工作,争分夺秒,一点不耽误。那时候我家里有母亲和爱人两个重病号。我母亲90多岁,两只眼睛看不见,跟我住在一起。我是一边工作一边照顾着她们。那时候医疗也挺麻烦,尤其是我母亲,我不但要安排住院,有时候还得陪着她,就得见缝插针地挤时间。瑞环同志非常关心,千方百计地帮助我解决困难,操了不少心。他甚至还跟丁关根同志商量怎么能帮上我。瑞环同志和关根同志见着我头一句经常是:“你母亲怎么样?什么情况了?”“你爱人怎么样了?住在哪儿?”丁关根同志曾多次请中宣部帮助解决我爱人的医疗费用,解我燃眉之急,保证了我安心工作。瑞环同志还帮着找医生,请天津的专家赶过来会诊。我母亲故去的时候,他还送了花圈。我爱人故去的时候,他亲自出席了追悼会。

继承与发展

1957年,叶盛兰与言慧珠排练《吕布与貂蝉》
叶派小生在京剧艺术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我的父亲叶盛兰是叶派艺术的创始者。至于我,首先是一个继承者,并在继承的基础上,结合时代的发展,根据我自身的条件,继续把叶派艺术发扬光大。我父亲讲过,有些戏他还要整理、要改编、要发展,但没来得及去实践。我演的《吕布与貂蝉》,就是在我父亲的基础上,把他未能够实现的想法给予落实。如果成功了,那就是有所发展,如果没有成功,可能就没有达到我父亲的标准和要求。我父亲有很多成功的创造,我仍在学习、体会。尽管我见过、学过这些戏,但每个人的条件还是不完全一样的,我父亲设计表演的时候,是根据他的条件来的。有的条件我就达不到,再努力可能也达不到他的水平。比如说我父亲的立音,我的嗓子比我父亲的宽,宽有宽的优势,但是立音和亮音方面就达不到他的水平。我父亲有的音非常结实,我有的时候也达不到。观众希望青出于蓝胜于蓝,但也要分情况。比如我创造的新戏《洛神赋》,这是原来叶派艺术没有的,我父亲根本没演过,而我是用我父亲创造的叶派艺术的艺术手段进行创作的,在这部戏中有我的创演成绩,但是不能笼统地说我已经超越了我父亲,我还是要不断地继承父亲创下的表演艺术。我父亲几十年天天在舞台上,他所有的剧目都是千锤百炼过的。我则没有,这说明我还没他的功力。可能有的剧目我熟练一些,但还要努力。一个人无论做人做艺,要活到老学到老,学无止境。“音配像”的戏我演过,还有很多戏我没演过。现在因为年岁大了,有些想演也演不了了,还是寄希望于接班人,希望他们刻苦努力,好好地继承。但是,无论如何,有了“音配像”,我父亲很多东西总算留下来了,最起码有这些录音。
“音配像”的伟大工程与精神永放光芒。(叶少兰口述 高芳整理)
本文选编自政协全国委员会办公厅主管,中国文史出版社主办《纵横》,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作者叶少兰,京剧表演艺术家。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全国政协京昆室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