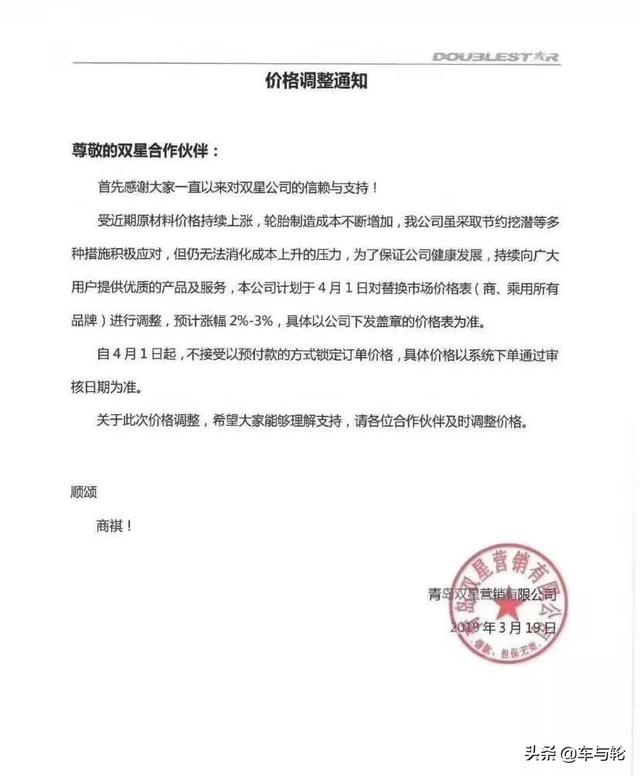来源:河南日报网
作者:邵丽
有言“书为心画”,大体意思是,一个人写的字能反映其德行品性。所以,古人能从一个人的说话写字上判断此人是君子还是小人。此言虽然有点以偏概全,但也不是一无可取。由此而生发开去,是不是也可以说“画为心书”呢?至少在画家李明的作品里,我觉得这句话是适用的。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山水画家,他的作品就是他最好的话语,也是他最好的心书。
对于书画,我虽然不是圈外人,但也知之不多,对相关作品的评价大多数情况下是凭直觉。当李明这个从来不对朋友提任何要求的画家,提出让我评论一下他的作品,我觉得虽在情理之中,但也颇感意外。掐指算来,李明作画几十年,相与书画评论者,大家名家当数不胜数,应该找一个权威人士。而我,虽因为工作关系参加过不少次书画展,却从不接受采访,怕说外行话惹人笑话。做人要有自知之明,面对他们的作品,实在是隔行如隔山,我只不过是以个人感觉,歪着脑袋说好看或者不好看的人。李明的画明朗、大气、率真,青山绿水,意境悠远。视觉效果让我喜欢。
好像只是一眨眼的工夫,与李明从相识到共事已经二十多年了。在这二十多年里,我们都在各自的领域里劳作和成长,也都在用自己的作品发声。日常生活里的李明,是个讷言敏行,冲淡谦和的人。虽然我们交流的并不多,但我对他的作品还是比较关注和喜爱的。尤其是他的山水画作,代表了一种风格和高度。李明是一个有着严谨的创作态度和艺术思考的人,也是一个在行走中去不断发现美的人。他不畏艰辛,踏遍了中原乃至祖国的山山水水,以沉稳内敛的艺术姿态潜心向内,厚积薄发,创作出一大批有着丰富精神内涵的作品。这些作品或大气磅礴,或端庄秀雅,或豪放飘逸,的确是“中原画风”的扛鼎之作。
我之所以喜爱山水画,可能也与性格和写作有关。山水画发轫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我觉得那个时期是文人活得最自我、也是最自信的时期。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体认和追问,也是那个时期最为显著的特点之一。我不懂画,绘画与诗歌是不是相辅相成也不是甚为清楚,但谢灵运的山水诗是不是对绘画起到了足够大的引导作用,我觉得值得深究。甚至就今日而言,从谢诗里汲取创作灵感也未尝不可,他的诗作就是一幅幅山水卷轴。此之前,孔子曾说过“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其实文人雅士真正沉浸于山水田园之中,就是从汉末到魏晋时期为炽。智与仁都是君子的品相,以水为性,以山为德,则是这种品相的内在修为。外化于方寸之间,造成一种胸中河山、咫尺天涯的盛大气象,不啻一场视觉盛宴,这就是中国画的魅力之所在。你说它是画,它的确是画。你说它是诗、是歌、是一场禅修,我觉得都不过分。所以有人说,中国山水画是中国文化的集大成者。其实它就是中国的哲学、宗教、世界观和处事的方法论。
李明是“中原画风”的提出者和身体力行者。与“文学豫军”这个地域文化概念一样,我觉得“中原画风”必定有它独特的且引人入胜的文化含量。宋以前,中原地区始终是中华民族的文化高地,宋朝也是文学和绘画创作的一个高峰。虽然宋室南迁曾经导致中原文化的衰微,但这种文化血脉在一些文人志士的坚守下,始终薪火相传,不绝如缕。如果今天能将其发扬光大,再创辉煌,既有必要,亦是必然。其功德无量,善莫大焉!
李明的绘画作品兼容并包,既蕴含着中原大地的人文精神,形质并重,于正大庄严之中饱含宠辱不惊的笃定和淡远。也吸收了现代绘画技术,使作品更加厚重饱满,异彩纷呈。李明的书法与绘画相得益彰,书法功力甚是了得。书法本身就是国画造型的语言,离开了书法谈中国画,其实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李明对此二者的心法和实践,给画家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范本。
李明有着超然物外的散淡,其实这既是性格,也是品格。他没有某些艺术家的那种张狂,反而是朴素得从不显山露水,有着那种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的气概,也许他的豪放都浓缩到自己的山水作品里了。虽然他不故作惊人之语,但作品却四处开花。这是艺术的力量,真正的作品会自己走路。而且我也深知,一幅山水画要耗费多少体力和时间。为此我感佩李明的默默奉献,他是用他的作品说话,也是用作品代河南发声。艺术创作虽然是非常个人化的事情,但它背后所代表的却是一个地域的文化标高。
有一分耕耘,便有一分收获。作为河南省美协副主席、书画院院长的李明,既是河南书画家的带头人,也是中宣部“四个一批”人才、“中原文化名家”、中国美协理事、中国人民大学特聘教授。他用自己的硬实力,彰显了河南书画家独有的艺术风格。
既期待李明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也希望他发挥登高一呼的作用,为中原文化崛起,为打造河南的艺术高地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本文刊登于2020年4月30日河南日报中原风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