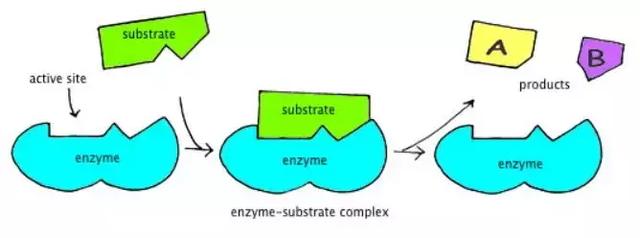牲口,指牲畜的俗称。专指供人役使的家畜,如牛、马、骡、驴等。过去是集体饲养,包产到户后由各个家庭饲养。
在生产队时,每个生产队都有自己的牲口屋,有专门的饲养员。每个生产队的牲口屋一般只安排两个饲养员管理。牲口是生产队里最大的一笔财产,因此,饲养员掌握着生产队的半壁江山,责任重大,队里选用饲养员是很慎重的。一定要挑选那些有饲养牲口经验、为人踏实可靠、吃苦耐劳、热爱集体、责任心强的人担任。饲养员一般同时也是队里的车把式,他们象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精心地照料着牲口。队里耕地、种田、碾场等农活全靠牲口,离开它们啥也不好干。
我的老家蒋班枣是典型的农耕村落,世代居住于此的先祖对牲口都有着深厚的感情。在生产队,各队饲养最多的是牛,当然也有马、骡,印象中饲养的驴不多。耕地时用牛的居多,马、骡、驴等腿脚快,多用来拉农作物,负责运输工作。每个生产队还有几辆马车,生产队的马车,一般由三匹马,一匹马是辕马,在中间,另外两匹马拉套,在辕马的两边。一年四季,每一天都不消停,农忙时送粪、拉种子、拉秸秆、进县城拉化肥、交公粮,农闲,还要负责结婚时送闺女接媳妇。

农村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后,土地分给了农户,生产队的牲口也随之分给了各家各户。生产队的牲口,有牛、有马、有骡、有驴,有大有小,有好有差,数量又少,每家一头显然是不可能的。分牲口时,只好让各户派代表抓阄。我家的手气不错,抓阄抓了一头膘肥体壮的骡子。一家一头牲口,没法耕地,于是两家自由结合,组成小的生产互助组。我堂敊家也分到了一头骡子,我们两家决定搭伙一起耕地。分地之前,我父亲先是在马庄公社拖拉机站,后又到班枣公社拖拉机站工作,一直在开大型拖拉机。记得小时候,经常坐父亲开的拖拉机跟他一起犁地,常常加班到深夜。所以分地时,父亲既不会使牲口耕地,也不会使牲口播种。我堂叔则是生产队的车把式,种地时正好教我父亲耕地。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分领到的骡子被变卖了,父亲买回了一头小毛驴,而且还是一头腿有毛病的瘸驴。从此,堂叔家种地不再和我家合伙用牲口耕地了,这件事被我母亲埋怨了好久。
父亲很快又找到了新的耕地合伙人,村东头的冬山家养了一匹白马,看起来不是很健壮,于是两家凑合在一起,竟然也把几十亩地耕种完,并且在村里还不算落后。
再后来,父亲又卖了瘸驴,买了个川马。川马个子很小,性情比较温顺,送粪、犁地、耙地,凡是大牲口能干的活一点也不拉下。在接下来的岁月,川马陆续诞下了好几头骡子,都长得高大威武。后来,川马也被父亲卖了,只留下一头健壮的骡子,一直养到家家户户都不再养牲口。

牲口吃的是草,从事着繁重的农活,农民把牲口看作是自家的成员。那时农村居住条件差,几乎每家每户的牲口都喂在厨房里。小小的厨房,一边是喂牲口的槽,一边是做饭的灶台,灶台的后面一般都有一个大土炕,做饭的时候把土炕烧得热乎乎的,在严寒而漫长的冬天,是个取暖的好地方。
夏天的时候,要给牲口吃新鲜的青草,把草割回家不能直接喂,还要用水淘淘,把土淘净、控水,如果草很长,还要把草用铡刀铡短,再喂给牲口吃。农忙的时候,牲口出力大,需要添加饲料,喂它一些有营养的豌豆、玉米、麸皮、棉籽饼等精料。在当时,牲口同样是家庭中最大的一笔财产,家家户户都把它们宝贝一样的精心饲养,如同对待孩子一样疼爱,和牲口有着深厚的情感。赶会、走亲戚,都是坐牲口拉的车,那时觉得特别幸福。
农闲的时候,也会到地里放牲口,让它们吃上新鲜的青草。记得有一年,父亲让我妹妹边锄地边放那头瘸驴。不料妹妹锄地锄累了,躺在树下睡着了,醒来一看,没看见驴影,赶紧到处去找,没有找到。天黑了,妹妹只好扛着锄回家。父母赶忙喊人到处去找,结果无功而返,想着肯定是让别人拾走了。谁也没有想到,晚上,驴竟然自己踱着方步,慢慢悠悠的回到家,径直走向牲口槽,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老马识途”一点也不错呀,它记得回家的路。

随着农业生产机械化的推广普及,手扶拖拉机、小四轮拖拉机、收割机、播种机、奔马车等小型实用农业机械逐渐进入了农村的千家万户。牲口渐渐地从收种、碾打等农业生产环节退出了历史舞台,村里养牲口的人家越来越少,养牲口的只剩下老年人,牲口拉车是他们的代步工具,用牲口耕地、拉粪的也寥寥无几。头脑灵活的年轻人率先买了大型的农业机械,现在农村电动车、汽车也普及到每家每户,在村里很难见到牲口。牲口曾是农村劳动的“主力军”,但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快速发展,老百姓种地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规模化,牲口被淘汰也是历史的必然。
现在政府鼓励发展养殖业,养牛的农户逐渐增多,但养牛的目的不是为了耕地,有的养的是奶牛,大部分养的是肉牛。养牛的目的是为了增加农民的经济收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马、骡、驴在农村都很少见,现在农村的孩子想看到这些牲口,还需要到动物园。看到各种各样的牲口(动物),孩子们纷纷给它们拍照、请陪伴的父母发朋友圈,高兴得不亦乐乎。
过去,家家都养牲口。下午放学回家,挎个篮子或者背个箩筐,去地里割草,边割草边玩耍,天不黑不回家。免费天然的游玩胜地,是那时农村孩子们放飞梦想的乐园。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题,一代人有一代人成长的生活痕迹。牲口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心里有不可磨灭的时代烙印,但对现在的孩子们来说,那却是梦幻般的童话世界。

作者简介:段志洁,河南省延津县马庄乡蒋班枣村人,毕业于河南省计划统计学校,现就职于延津县文岩街道办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