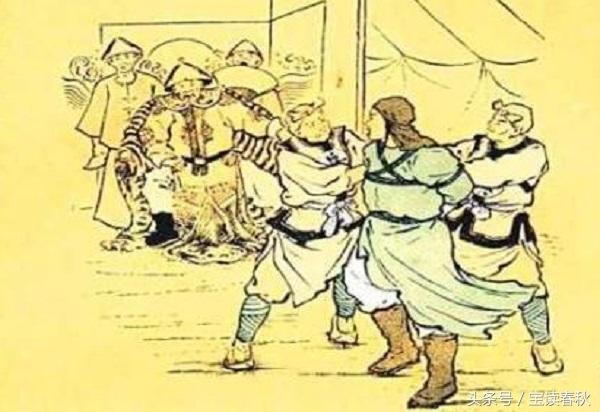张廷玉在《明史》中一句“明之亡,非亡于崇祯,实亡于万历”将万历推向了无底深渊,一口大黑锅愣是背了三百多年。
到了现代,百家讲坛某位明清史阎姓专家专门为神宗编织了几宗罪“酒色财气”,“宦官肆虐”,“长期怠政”。
先说“酒色财气”,这大概源于雒于仁那封著名的《酒色财气四箴疏》中对万历的破口大骂。
在讨论这点前,有必要先说明一下明朝的言官。
明朝的言官非常善于捕风捉影,夸大和歪曲事实,比如高拱自辩上班回家拿东西是因为“家贫无子,没有帮手”,愣是能被浮想联翩的言官诬陷成“高拱没有儿子,上班打完卡就翘班回去玩女人以图生个儿子”。
这就是明朝言官的作风,一些小道消息,就极尽耸人听闻,夸大其辞,完全不管所说的是不是真的,而是为了能出名,说白了,就是搏出位,被骂的人官越大,就越容易一举成名,以获得自己的政治资本。
所以对于这篇奏疏,到底其夸大其辞的成分有多少?

万历
先说一个“酒”字,笔者翻过了明实录和各类史料,似乎能说明神宗酗酒的只有万历八年那次醉酒以后被张居正勒令写检讨的事,其他没有任何资料显示万历酗酒成性,对于这个问题,明实录里万历自己是这么说的:
“他说朕好酒,谁人不饮酒?”
且不说万历时期士大夫好饮酒已成风,就说咱们现代人,逢年过节,和朋友亲戚畅饮,喝醉一两次不正常吗?可笑的是,阎姓专家却大放厥词,说万历“经常喝的酩酊大醉”,难不成他在乾清宫装了一个摄像头?
再说一个“色”字,依据大概是万历十四年,神宗生病连日罢朝,症状主要为头晕眼黑,四肢无力,身体虚弱。
于是这些言官马上又联想到万历是因为“耽于女色,房事过密”。
把什么病都喜欢和好色联系在一起,在中国由来已久,鲁迅曾经说过自己因为牙痛,被长辈斥责为不自爱,后来自己去翻中医书,才发现,原来中医说牙齿属肾,牙损的原因是阴亏。
这些言官大抵和鲁迅的长辈差不多,其实万历身体不好很正常,从小开始吃饭就很精细,又缺乏运动,长期呆在深宫里,身体虚弱多病难道不正常吗?(这点清朝的皇帝的确要好的多,普遍比明朝的皇帝都要长)

郑贵妃
更何况,万历至始至终都只喜欢郑贵妃一个人,即时年纪大了,郑贵妃年老朱黄了仍然不离不弃,死后也合葬在了一起,如此专情,居然被说成好色,如果他真的好色,何必抱着年老色衰的郑贵妃不放?笔者很好奇,康熙几十个妃子,儿女多的数不胜数,六十五岁还在生儿子,却没有人说他好色?
接着是一个“财”字,这个字就显得非常可笑了,奏疏里说万历收受了司礼监太监张鲸的贿赂,万历是这样回复的:
“朕为天子,富有四海,天下之财皆朕之财,朕若贪张鲸之财,何不抄没了他?”
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照理说天下的财富都是皇上的,皇上去收一个太监的贿赂,这不显得很可笑?如同万历所说,我要他的钱,干脆把他家抄了得了。
诚然会有人拿万历开矿监说事,可是有没有人想过,既然皇上富有四海,“以六合为帑藏”,为何还要与民争利?
因为明朝皇帝的收入并不多,某些地方还要受户部的掣肘,万历毕竟没有嘉靖那么强势,也没有严嵩这样的首辅,国库的钱其实他根本动不了。
明朝皇帝所得收入基本都是来自子粒田。阎姓专家曾指出“万历自己的皇庄加上他赏赐给他弟弟和儿子的,加起来是810万亩,而万历六年时,全国的土地为5.1亿亩,万历一家占了全国总田数的6.3%”
嘉靖二年,明世宗曾下旨“止照新册改为官地,不必称皇庄名目”,其实皇庄这个词在嘉靖年间就应该已经消失了。当然无论是官地也好,皇庄也罢,总归是给皇上提供收入的,那么这些收入到底有多少?
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里有记载:“皇庄每年 4 万 9000 两子粒银的收入用以供应几 位太后的开支。李太后所得大半用于北京郊外的石桥建筑和捐给宗教寺院”。也就是皇上每年可以用的银子大抵也只有5万两左右,这是啥概念?隆庆年间两广总督李延吃一年的空额大概就有十万两银子,更别说那些盐商,茶商,人家一个月或许挣的都比万历多。

李太后
这其实就是明朝一个很奇特的现象,百姓很穷,国家很穷,皇上也很穷,只有中间的皇亲国戚和文官集团富得流油。
顺带说一句,按阎姓专家说的810万除以5.1亿,结果是1.6%,不知道这6.3%是怎么计算的。
所以,万历开矿监大抵也是因为手头实在太紧,不得不想方设法弄点私房钱。对比后世光绪结婚消耗550万两白银,慈溪60岁生日一千万两白银,万历自身的私生活根本谈不上骄奢淫逸。
堂堂大明天子,手中的钱恐怕还不如一个富商来的多。
最后说一个“气”字,这个字充分反映了这些言官纯粹是为黑而黑,夸大其辞。这个气字说的是万历经常打死太监。好嘛,对太监太松又说是阉党太盛,要打压,太严又说皇上气太盛,要打压。嘉靖一朝打死的人多的去了,为何言官屁都不敢放一个?还不是欺负万历好说话,而万历对这事反应如下:
“且如先生每也有童仆家人,难道更不责治?如今内侍宫人等或有触犯及失误差使的,也曾杖责,然亦有疾疫死者,如何说都是杖死?”
太监作为皇上的仆人,有错误打几下,变成了虐待太监。何况很多太监是病死的,也被雒于仁说成是被万历打死的。而且內宫之事,笔者很好奇这些言官从哪里得到的消息,仿佛他们就在现场看着万历打死太监一样。
对比清朝的皇帝,万历可以说不能够再仁慈了.
举个例子,嘉庆时有个编修洪亮吉说了一些朝廷的弊政,刺痛了嘉庆,嘉庆准备把他拉出去斩了,中途又改流放,于是称颂嘉庆的仁德。
而万历呢,田大益把他和“夏桀、商纣王、周幽王、厉王、汉桓帝、 灵帝、宋徽宗等昏君“并列一起,结果这位仁兄一点事都有,还升了官。
又比如在争国本的时候,礼部都给事中李献可等人联名上疏,结果把弘治的年号写成了“弘洪”,这种犯大忌的事放到清朝大约全部会被砍头,而万历仅仅是“为首的姑 着降一级调任外用,其余各罚俸六个月”。
谁仁德谁暴戾一目了然,何况嘉庆在清朝皇帝里并不算一个残暴的皇帝。
可以说,雒于仁所说的酒色财气基本都站不住脚,无非是言官好名,好捕风捉影之事,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酒色财气”说完了,那所谓的“宦官肆虐”又是怎么回事呢?
这点大概源于明朝首辅朱赓的同乡给事中喻安性,为朱庚推卸责任所说“今日政权不由内阁,尽移于司礼”。然而他的话其实并没有人信,甚至连他自己给事中的同僚也不相信他,联名弹劾他,明史说:“遂交章劾安性,复侵赓”。
至于万历年间司礼监的权力,能说的上号的无非就三个:冯保,张鲸,张诚。

冯保
其中权力最大的无非是冯保,但那时权力掌握在张居正的手中,冯保虽然贪财,但在政事上是全力支持张居正,而张居正一死,冯保就被赶去南京种菜了,最后上吊自杀。
而张鲸、张诚下场比冯保好不了多少,万历十六年,何出光弹劾张鲸,张鲸就被万历疏远,最后被罢黜。至于张诚,明史没有专门的记载,仅说明在万历二十四年被突然斥退,然后抄家发配。
而在张诚之后,《明史·宦官二》是这么记载的,自冯保、张诚、张鲸相继获罪后,司礼监注意收敛,不敢放肆,万历同样讨厌阉党太盛,即时司礼监有空缺也不补充,东厂荒凉的青草满地,后来司礼监人实在太少了,连皇上的膳食都应付不了,不得不让乾清宫的管事太监常云独自承办,自此内廷外廷都相安无事。
可见,所谓宦官肆虐,完全是子虚乌有。
最后,就是经常被人诟病的“长期怠政”。
其实不上朝这事,嘉靖就干过,时间不比万历的短多少,但是似乎也没人说嘉靖怠政。
主流观点认为,嘉靖虽然不上朝,但国家的权力还掌握在他的手中,而万历则不然。

嘉靖
但笔者认为,掌权不等于勤政。
嘉靖一朝,党争比万历严重的多,嘉靖借用严嵩达到控制朝局的目的,大权的确是掌握了,明史说他 “张弛操纵,威柄不移”。但结果呢?东边倭患不断,北边俺答入侵,差点打到了北京城,严嵩毫无办法,明朝国力严重衰退。
海瑞言“嘉靖嘉靖,家家皆净也” ,并非空穴来风。
而嘉靖不上朝的理由,纯粹是因为和文官集团不和,就是不想见他们了,全靠严嵩徐阶传达消息。
而相比嘉靖的不上朝,万历不上朝的理由更为充分。
从定陵被挖掘出来以后,对万历的尸骸做出了严格的分析,得出结论:
万历不仅是个跛子(左右脚长度不一),腰上也有严重的疾病。

万历骨架
实际万历也仅仅活了五十八岁,寿命并不长。说明万历的身体的确很差,更何况没哪个皇帝愿意给臣子见到自己是个跛子吧?
万历也曾经给出过自己的解释“朕病愈,岂不欲出!。。。。只是腰痛脚软,行立不便”
虽然万历对于权力的掌控不如他爷爷,但是整个明朝的机关单位运转自如。《万历十五年》是这么描述的:
““皇帝的放弃职责并没有使政府陷于瘫痪。 文官集团有它多年来形成的自动控制程序。......北京的会试、殿试照旧举行;地方官和京官 按时的考核也没有废止。派遣和升迁中下级文官,用抽签的方法来决定。......对于这些例行 公事,皇帝照例批准”
樊树志在晚明明史中也说道,神宗在此后的二十多年中,处理朝政的方针是透过批阅奏疏,发布谕旨来进行的,他始终牢牢地把持住朝廷的大政方针,这从“万历三大征”的全过程可以看到很清楚。
万历在三大征的作用史料实在太多,在这里不再赘述。
当然不必否认,有很多折子万历也常常留中不发。然而就如上面所说,万历对于国家大政,重要职位的举荐罢黜都了若指掌,说怠政实在荒谬。
大概万历也没有想到,自己死后不仅成为最有争议的皇帝之一,还背上了如此一口大锅。万历不能算多么了不起的一个皇帝,他没有魄力延续张居正的改革,但绝非一个荒淫无度,懒政怠政的皇帝。
把一个朝代的灭亡强加在某个皇帝上本来就是错误的,明朝走下坡路是无可避免的,这在明初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只不过明初时问题并不明显,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弊政已经根深蒂固,尾大难掉了,即时有张居正这样的救时宰相,也难以撼动这些弊政的既得利益者,要改革更是千难万难。
明朝之亡,非亡于某人,而亡于其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