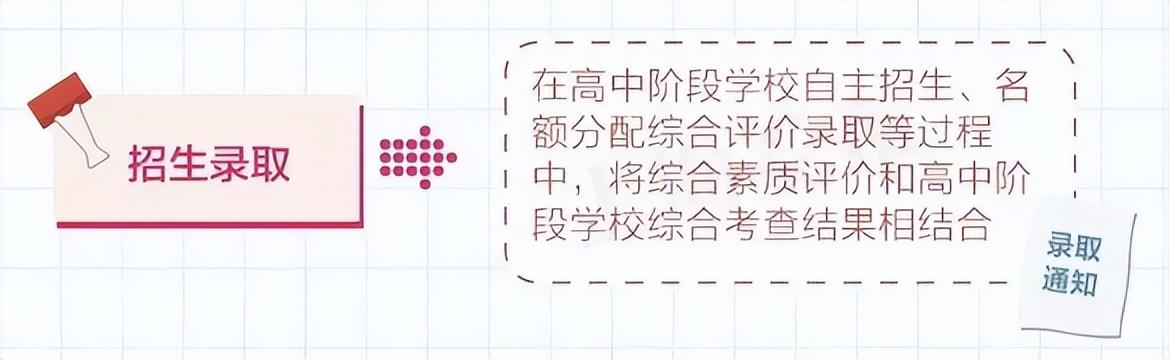乾隆时期,中国的人口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短短六十年的时间里,人口数量增加了一倍,到了乾隆晚年,数量已经突破三亿人。或许这个数字放在今天不足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可是在封建小农经济时代,三亿人就是三亿张嘴,要养活这么多人,显然是无法想象的。

乾隆皇帝批阅奏疏
提到吃饭问题,最绕不开的就是粮食产量和粮食储备。那么,乾隆时期的情况又是如何呢?
一,粮食产量
封建社会历朝历代都没有留下过全国粮食产量的数目,主要是当时的统计手段有限,无法得到确切的数字。不过,我们可以从全国耕地面积来进行一个大致的估算。而关于耕地面积方面,留下的史料还是很丰富的,乾隆时期这个数字在大约在10.5亿亩。
不少专家学者对清代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作了深入的研究,大体来说,江南省份单位面积产量高,而耕地面积小;华北等省份单位面积产量小,而耕地面积大。
如江浙为高产地区,据苏州织造李煦向康熙汇报的情况来看,苏州、扬州的亩产量可达到四石(每石120市斤),双季稻亩产量可高达五六石。但需要说明的是,这是条件较好的实验田,一般农家达不到这个标准。
在《钦定授时通考》中也有记载,说“江南水田,亩多二三石,次一二石”。方苞说:南京的土地一般亩产三石,但也有更高的。南方其他省区,农业种植条件较江浙稍差,以江西为例,中田三石,下田二石。

清代的粮仓
南方种植多以稻米为主,品种较为单一,估测起来比较容易。而北方多种杂粮,有麦、豆、谷子、高粱、玉米、甘薯,品种不一,产量悬殊,因此估算较难。以河南为例,上田亩产两石,下田亩产不及一石,少的只有三四斗。至于高寒地、盐碱地,其产量更低,估计全国这类低产地不在少数。
如果把全国的10.5亿亩耕地,除去种植棉、麻、烟、蔗等经济作物约5000万亩以外,粮田总数约为10亿亩。按其产量,分成四等,其中一等的仅占一亿亩,产量为3.5石,二、三、四等地各三亿亩,产量分别为2.5石、1.5石与1石。以此估算,则粮食产量共为17亿石。以每石折合120市斤,共为2040亿斤,此数大致就是乾隆晚期全国粮食的总产量。
如此算来,全国3亿人口,人均粮食为680斤,这个数字就是乾隆盛世最重要的经济支柱。不过,以上算法都是按正常年景估测,但当时旱涝虫等自然灾害,几乎每年都有,十分频繁且严重。如果考虑因自然灾害而减产,则粮食产量还要降低。在减去饲料、酿酒、制酱等附属农产品,每人每年的平均口粮则低于600斤。
对于农民来说,每人有600斤口粮确实不算少,但还有一个大头没有计算在内,那就是须上缴的赋税,正常情况下,赋税要占到一半,而且这还是对于自耕农而言。若是地主的佃户,即便是丰年,恐怕也得喝粥度日了。
上面的粮食产量是根据乾隆晚期的耕地面积和粮食生产的情况作出的推算,由于缺乏详细精确的数据,其误差难以避免。但基本上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在乾隆盛世阶段,温饱依然是最高统治者面临的最大难题。

乾隆出巡图
二,粮食储备及应对措施
1,设立常平仓、社仓、义仓
广大农民能不能吃饱饭,这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饥饿的民众,是威胁统治权最可怕的力量。清政府非常重视这一点,它的许多有关粮食的政策,都可以归结为利用有限的粮食资源,调剂余缺,努力保证口粮必须,以求得统治的稳固。
为了防止饥荒,清朝继承古代的传统,设立常平仓、社仓、义仓,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其贮藏和调剂粮食的仓贮系统。常平仓设于各州县,为政府所建,仓粮由官民捐输、拨帑采购或赎罪罚俸所得;社仓设于乡村,义仓设于市镇,均为民办,由绅商士民集资兴建,自行管理,实为绅办官督。
仓贮的作用,平常年份,青黄不接之时,出贷粮食,收获季节,粮食丰盈之时,买补还仓。若遇灾荒之年,则开仓放赈,抵御饥荒,以免饥民慌乱引起社会骚乱。
仓贮系统在清初即已建立,但规模和作用还不大,至雍正、乾隆时规制完善,积谷大量增加。康熙时,常平仓初建,“直省常平仓所贮米谷,康熙年间未经定额,或定额无多”。雍正时已增加很多,全国常平仓积谷2000多万石。乾隆帝对贮备粮食更为重视,他认为:“朕实代天以子民,督抚大臣又代朕以子民,均有父母斯民之任也”。

清代的义仓
乾隆即位后对粮食贮备抓的很紧,国库也有充裕的财力,一度库存粮谷达4400万石。这个数字虽然只占到全年粮食产量的2.5%,相对而言,数量不大,不会引起粮食的连年涨价。
乾隆十三年(1748年),朝廷为了平抑粮价,决定减少采购量、降低常平仓的贮存量,此后,常平仓额保持在3370万石左右,加上社仓、义仓的积谷,估计约为4000万石,合50亿斤左右。
常平仓、社仓、义仓在抗灾备荒、防止饥民骚动,稳定社会秩序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乾隆时,御史万年茂就说:“倘遇地方一时乏食,他处之米接济不及,乡民嗷嗷,万千成群,入城呼吁,地方官或赈或贷,小民各得升斗,即时立散。俟他处接济米来,人心易安,使小民有恃无恐。”
2,京师漕粮
清朝定都北京,18世纪北京已发展成为百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为了供应北京贵族、官吏、士兵、旗民、匠役的食用,从江、浙、皖、赣、鄂、湘、鲁、豫征收漕粮,年额400万石,由运河运往北京。这是保证京师口粮供应、稳定政治中心的“天庾正供”,至关重要,一旦漕运阻绝,北京的官吏士兵将人心慌乱,朝廷势必涣散。

清代各州县设立的常平仓
为此,清廷大力组织漕粮北运,特设以漕督、仓督为首的专门机构,拥有大批船只和运丁,耗费巨大,不惜成本。漕米的运输十分昂贵,成为财政上的沉重负担,所谓“河运剥浅有费,过闸过淮有费,催趱通仓有费。上既出百万余漕项,下复出百余万帮费,民生日蹙,国计日贫。”乾隆中叶,漕粮的价格十分惊人,达到每石六七两不等,运费超过米价的四倍以上。
由于漕运是维系清王朝统治的生命线,虽弊端严重,经济上极不合理,但是仍要千方百计维持,越到后来越变成沉重包袱。漕粮虽属官征、官运、官为分配的自给性消费。但官吏士民所得俸米,允许在北京市场上出售。灾荒地区,往往也会奉旨截漕,留供本地赈济。所以,部分漕粮也成了商品粮。
乾隆朝截漕是经常性措施,数量很大,乾隆十二年(1755年)以前共截漕1320万石,平均每年截漕66万石,占全年漕粮征收的16%,主要用于灾区的赈济。
3,粮食商品化
由于人口增长不平衡带来了压力,全国已形成大范围的余粮区和缺粮区,粮食商品化已成必然趋势。在官方政策的倡导、鼓励下,全国形成了规模颇大的粮食市场,促进了粮食的长距离运输。

《天下粮仓》剧照
当时,除400万石漕粮每年北运以外,最大的粮食流向是从四川、湖南、湖北,由长江东下,流往江苏、浙江,并由海路运往福建。此外,东北的麦、豆由海路运往北京、直隶、山东,湖北,河南的米粮由汉水或陆路运往陕西,广西米粮运往广东,台湾米粮运往福建,湖南、四川米粮运往北京、直隶、贵州,大体上形成了粮食长距离流通的固定渠道。
有专家估计,清代中叶,进入长距离流通的商品粮约有4000万石,基本和常平仓粮数持平,约占全国粮食产量的2%左右。但村镇之间的短距离粮食交易极多,这个数字当远远超过4000万石之数。
4,鼓励粮食进口
由于本国粮食产粮不足,特别是广东和福建,山多地少,一向就是缺粮重灾区,如果靠国内长距离运输,不但费用高,数量亦有限,所以不得不鼓励洋米进口。
暹罗、安南出产大米,极为丰富,从乾隆年间,大批洋米输入。乾隆八年(1743年)下谕:“朕畛念民艰,以米粮为民食根本。是以各关米税,概行蠲免,其余货物,照例征收。至于外洋商人,有航海运米至内地者,尤当加恩,方副朕怀远之意。”

乾隆皇帝南巡颁谕
按朝廷的定制,洋船若带米一万石以上者,可免其船货物十分之五,带米五千石以上者,可免十分之三。这是一项十分优惠的政策,外商贩米进口,不仅可以减免船货税银,而且如果米粮滞销,还由官府出面收购。
不过,从实际情况来看,东南亚国家产米虽多,米价亦贱,但海运来华,费用甚大,获利微小,且有风波之险,因此运米进口者往往都是中国出洋贸易商人在回国途中带入,并非是外商专做粮食交易。
乾隆十六年(1751年),朝廷批准内地商民,自备资本,购米回国者数量在二千石以内者,由地方督抚分别奖励;如运二千石以上者,按数分别给与监生,并可奏请赏给职衔顶戴。这一措施极大地鼓舞了商民携资出洋的积极性。此后,经常有运米较多的商人获得八品或九品顶戴,东南亚的大米也源源不断流入广东、福建等省,解决了粮食危机。

乾隆皇帝视察粮仓图
整体而言,清政府十分重视粮食的贮备、调剂与流通,以有限的粮食资源供应高速增长的人口。在“民以食为天”封建社会,在至关重要的粮食问题上,清代的最高统治者尤其是乾隆帝努力承担其民生食用的责任,尽可能从宏观上做好控制和调剂粮食的工作,这也是乾隆供养三亿人口吃饭的奥秘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