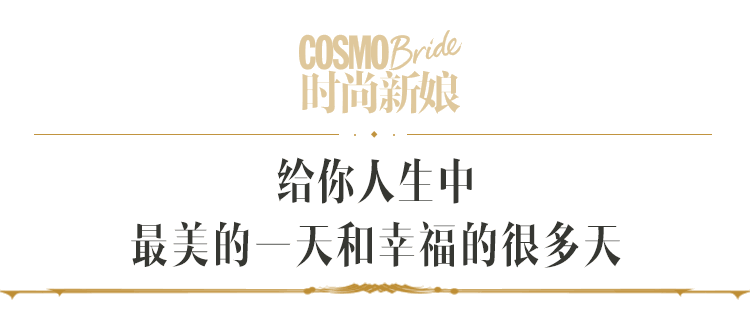我不是一个职业的写作者,但是我的工作却又一直离不开写作。我是一名研究者,研究的结果总是要以文章的形式体现。开始是为企业研究经济、行业,后来又独立地研究历史、文化。
总结近二十年的写作经验,我总结出了一条基本原则:写作就是表达自己内心的最真实想法。我不是在写作,我只是想真实表达自己。
当看到今日头条在举行“无条件写作日”,我欣然参与,因为这与我的写作原则相契合。“无条件”的中的“条件”,应该是指对写作的技术性限制条件。“无条件”就是没有限制,自由发挥。其目的无非也是激发和保障写作者的最真实的想法和情感。
活动所给出的线索性的题目是朴树的一首歌《生如夏花》,而且是郑重地邀请清华大学的一个合唱队现场演唱。
说句实话,我此前并不知道这首歌的存在,更不知道其歌名正是来自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的一首诗的名字。当然,朴树、泰戈尔是听说过的,尽管了解甚少。
于是就检索了一下,认真研究了一下泰戈尔和朴树两个版本的《生如夏花》。然后就确定我此次写作的思路和题目:生命当不以夏喜,不以秋悲,素位而行。
以我一个文化研究者的视角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研究题目:中国和印度文明的比较,或者更精确一些,是儒家和佛教的比较。
关于儒家和佛教,一个非常流行的误解是,儒家没有考虑死的问题,不会处理死,因此是一个缺陷,而佛教则是主要考虑和解决死的问题,因此,填补了儒家的空白。
事实是,正是因为佛教太看重死了,认为对生命而言,不仅存在一个死后状态,而且这个死后状态甚至比生前状态更重要,导致佛教陷入一个误区和歧途,去虚构死后的生命,虚构不灭的灵魂,并且认虚构为实有,花费巨大的精力对虚构的东西去研究和辩论。

而儒家的关注点则是生的状态,因为这是人所能够体验感知的。对于死后的状态是消极的,甚至否定的,因为那时人无法体验和感知的。
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篇)
就是孔子和儒家对人鬼生死的态度。其实质是对“鬼”、“死”进行了否定,而只承认“人”和“生”的存在,并教导人们应该把关注点放在实实在在的“人”和“生”上,而不应浪费在莫须有的“鬼”和“死”上。
孔子的另两句话也同样表达这个意思:“敬鬼神而远之”,“祭神如神在”。孔子并没有绝对地否定鬼神的存在,而只是强调要“敬而远之”。对本来就不存在的东西去证明其不存在,是浪费和不明智。而且鬼神这些概念,尽管是虚构的,但也并非全无用处。对鬼神的祭祀,可以激发人之“敬”,可以让人收敛和体认自己的内在心性。
孔子之所以要强调“祭神如神在”,就是为确保通过祭祀所激发出的“敬”是真实的。
也就是说,孔子实际上是讲对鬼神的祭祀当成了一种修心手段。这样鬼神就成为工具,而非目的。《周易 观卦》说:“神道设教”,就是这个道理。

泰戈尔的《生如夏花》,正是基于佛教和整个印度文明对生命的理解而写:更重视死后的生命,而轻视生前活着的生命。其实质就是以虚构的生命为真为贵,而以真实的生命为假为贱。
泰戈尔在诗中说:“生来如同璀璨的夏日之花不凋不败,妖冶如火承受心跳的负荷和呼吸的累赘”。“不凋不败”的,就是虚构的不灭的灵魂,也是虚构的死后的生命。“心跳的负荷和呼吸的累赘”就是真实的生前活着的生命。
泰戈尔将虚构的死后生命看成“璀璨的夏日之花”,却将真实的活着生命当成“负荷”和“累赘”。
流行的谬见认为,佛教超越了生死,完美地解决了死的问题,给予了人们一个正确地对待死亡的态度。其实,佛教那不是超越生死,而是混淆生死,甚至颠倒生死,既没有搞明白死,更没有搞明白生,而导致了巨大的理念上的混乱。正如孔子说说“未知生,焉知死”。
佛教之所出现生死错乱,根源在于一种巨大的恐惧,被这种恐惧所支配。这种恐惧并非是一般人所认为的对死的恐惧,恰恰相反是对生的恐惧。所谓的对死的恐惧,源自对生的恐惧。正是因为对生充满巨大的恐惧,因此就幻想一个没有恐惧的世界,认为死后的世界就是这样一个世界。
因此,佛教和印度文明对死并不恐惧,恰恰相反,而是一种巨大的渴盼,因为死意味着摆脱充满恐惧的生的世界,而进入一个没有恐惧的极乐世界。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泰戈尔在诗中最后说:“般若波罗蜜,一声一声,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
“般若波罗蜜”是佛教用语。“般若”是“智慧”,“波罗”指“彼岸”,“蜜”指“到”,整个的意思是凭借智慧到彼岸。“彼岸”就是不生不灭之灵魂,就是涅槃,就是没有恐惧的死后世界。
这里的“生如夏花”和“死如秋叶”,其实都是不生不灭的永恒之死。看似超越生死,其实是鲜活绚烂之生进行了残忍地否定,而仅剩下虚构的“如秋叶之死”的“静美”。
朴树的《生如夏花》,较之泰戈尔,则有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做作。做作也是一种虚假,这种虚假原则泰戈尔,却又不同于泰戈尔,可以说是一种“东施效颦”虚假。
泰戈尔是在否定生,而讴歌死,这与以儒家为基础的中国文化格格不入。于是,不知什么原因,一定要嫁接泰戈尔的朴树,就将关注点转移到对生的赞美和哀怜上。
哀怜,是哀怜生的艰难和生的短暂。朴树说:“也不知在黑暗中究竟沉睡了多久,也不知要有多难才能睁开双眼”,这是对生命诞生之艰难的哀叹。
然后又说:“我为你来看我不顾一切,我将熄灭永不能再回来”;“惊鸿一般短暂,像夏花一样绚烂”。这是对生命之精彩的赞美,以及对生命之短暂的叹息。
需要强调的是,朴树的“夏花”,与泰戈尔的“夏花”有着本质不同。泰戈尔的“夏花”,真正所指的并非生,而是死。泰戈尔的“夏花”是“不凋不败”的永恒,意指不生不灭之灵魂,也是死后的生命状态。而朴树的“夏花”尽管也象泰戈尔一样“绚烂”,但是却“惊鸿一般短暂”,而非“不凋不败”。
“不凋不败”的,是死;“惊鸿一般短暂”的,是生。显然,朴树和泰戈尔分别跑在了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跑道上。
也因此,泰戈尔的诗是“秋叶”与“夏花”并存的。在泰戈尔看来,“夏花”还代表着生,不过这种生是虚幻的,不重要的,而“秋叶”则代表着死,尤其开始进入死后的生命,进入极乐世界。
而在朴树东施效颦的歌词中,则仅仅有“夏花”,而删去至关重要的“秋叶”。因为中国文化更在乎的生,人死如灯灭,保留“秋叶”是无意义的。

下面,我们将进入本文的核心部分:印度、佛教为什么对生充满如此的恐惧?儒家则为何没有这样的恐惧,并形成合理对待生死,合理对待生活的正确态度?
问题的关键在,在于人格的独立,而人格的独立的核心又在心性独立。
要而言之,中国文明在文明伊始,就形成了心性的独立和人格的独立。而印度文明,则自始至今,都没有能够形成真正的心性独立和人格独立。
唯有真的心性独立了,人格独立了,人才能真正建立对自身的信心,消除对外界的恐惧。人就成为一个独立的心性主体,而外境、外物,则成为人的心性的判断和选择对象。
心性的核心职能就是独立地进行判断和选择,即进行“思考”。人心就是一个思考主体,是人的一切思考活动的发出者。即孟子所说的“心之官则思”。
要思考,要判断和选择,就必须有所依赖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就是“理”、“义”,“义理”等,现在我们统一称之为“道义”。
但是,这个“道义”并非存在于人心之外的条文,而是存在于人心之内的,而且是人天生就具备的,是“不学而知”、“不学而能”的“良知良能”。这就是是孟子说的“义内”。
这样,“道义”就成为人心的基本属性,是存在于人心之中的,天然的思考原则、行事原则。这就是后来宋明理学所总结的“性即理”、“心即理”。“理”就是“心”之“性”,或者就是“心”之本身。
这就是意味着,只要遵循和顺应人自然的本心本性,人就能够做出正确的思考,做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最终其行为也是正确的,合理的,合乎道义的。
因此,儒家思想的核心,就是在教导人们去认知自己之独立之心性,并维护心性的独立,即维护心性的独立的主体性。
心性容易受到外物的影响和干扰,而执着和沉溺于物,这样就失去了独立性,而物化了。因此,维护心性独立的关键,消除人心对因外物的影响,而产生的执念、妄念。
因此,孔子说:“勿意、勿必、勿固、勿我”;“无适无莫,义之与比”。这两句话都是在强调消除心中的成见,不要这些成见影响自己的判断,从而保持心性去独立地进行判断和选择。
《中庸》则直接说:“率性之谓道”。顺应、遵循人之本性就是“道”。还说:“诚者天之道”,“诚”就是顺应和保持最真实的自己,即让自己免除一切外界之干扰。
从文献上,看这种思想源自《周易》。《周易》最核心的思想是“贞”,就是“守正”。所谓“正”关键在人心,是“心”之正。心之正,就是心之常态、正太,心之本然状态。因此“贞”实际就是“诚”,就是“率性”,而且更在强调则不利的环境之下去坚守、固守本性。
《周易 坤卦》说:“直方大,不习无不利”,“直”、“方”都是顺应和遵循自己真实本心,这样就是“大”,“大德”之大。“不习”,就是不要刻意地去学习、练习。刻意地学习,就是形成成见。
《周易》还有一卦叫“无妄”,就是顺应自然,不要额外的想法。其中有两句爻辞非常值得研究。第二爻是:“无妄之疾,勿药有喜”。意思是有时候即便得了病,也无需担心,不要有过多的想法,自然会好的。
第六爻是:“不耕获,不菑畲”。“不耕获”,就是不耕而获。“菑畲”是最原始的耕作方式。这里是将人为的耕作,看成是对粮食的非自然的渴求。粮食的自然状态,就是野生状态。“不耕获”,就是采集野生的粮食。
最明确和形象指出这种人生态度的是《中庸》的“君子素其位而行”章: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
“素”,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无条件接受现实,不抱怨,不狂喜,不产生情绪波动。“素其位而行”,就是对现有的环境进行独立的思考,进行独立的判断选择,按最合理的思考结果去行事。
以儒家的标准,以《周易》的标准,泰戈尔贱生贵死,是一种极大的妄念。朴树讴歌生命的精彩,哀怜生命的短暂,同样也是妄念。这都是对心性独立的偏离,或者是未能实现心性独立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