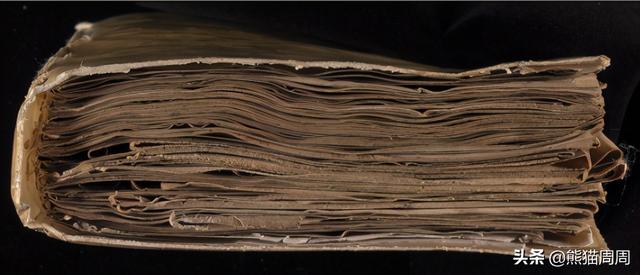(闫记平)
每当进入腊月二十,城镇的街道上就会出现红红黄黄的摆摊的,远远望去,就知道是卖春联的。我虽是匆匆赶去上班,但心里是暖洋洋的,这一天心里总是惦记着那个摆摊的,因为春联里窖藏着少年岁月的温暖。可是,当我下班后走到地摊前却发现:春联全是印刷出来的,纸张质量差不说,虽是红纸,却有许多是烫金字,甚至还有带金边的,这又不是故宫紫禁城,镶什么金边呢?徒增一种俗气,少了简洁的美。这不是我心中那个年代的春联。我小时候关于春联的印象是这样的:

写春联
小时候,每到腊月二十八左右,我会受父亲之托,到村供销社买来红表(写春联的红纸),回到家用小刀割成若干副春联大小的长条,最后还特意多割几张“四方联”,多多益善,为的是多写几个“春”字。然后就将割好红表送到会写春联的老师家。我们生产队会写春联的只有两家,一家是南边的教中学的老师,一家是东边的教小学的老师,两位老师我都称为叔叔。每次到老师家,都见到络绎不绝求写春联的。老师是免费写,不要任何报酬,还得搭上自己的墨汁。有的放下红表就走,写什么内容老师说了算,等两天再来取。有的人有时间,当场等老师写完就拿走。我也观看过老师当场书写,下笔不假思索,若有神助,一气呵成,煞是羡慕。 后来有一天,我不甘心,发誓自己也要学会写春联。买来红表和毛笔,偷偷试了一次,笔手就是不听使唤,写出的不像书法,倒像柴火棍。晚上躺在被窝里,暗自叹息:“老师挥毫如神助,学生下笔鬼捉手”。从此,不再跟别人提学写春联的事。现在想想那个年代,两位老师辛辛苦苦忙乎好几天,也不知道利用写春联的机会挣个零花钱,也算是奉献了。

贴春联
贴春联对于春节来说是一项重要的仪式,贴上春联就意味着春节开始了。农家旧舍一年到头,喜庆不喜庆,全靠春联打扮了。现在的农村房子都是红砖房、黑漆大门,有的还装饰得富丽堂皇,平时不过年也是光彩耀眼。那时候我们村都是破旧的蓝砖房,有的房外面砖经过常年风雨侵蚀已经碱透了,里面露着土坯。还有的人家是泥土和着麦秸的围墙和栅栏门。这些寒陋的农舍,只有到春节大门小门都贴满火红的春联,才给人们一种春意盎然的生机,一种寒冬里的温暖感。 古代对于贴春联,还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封印”,即封闭已经扫除干净的家室,拒绝妖气进入的意思,虽有迷信的成份,却也似乎有些道理。
我们贴春联一般都是在大年三十晚上。母亲用白面给熬好了半锅糨子,我穿上棉衣,一手持着蜡烛,一手端着糨子锅,咯吱窝夹着春联,开始喜气洋洋地忙活了。赶上雪天,会踏着“吱吱嘎嘎”的积雪,烛光映照着寂静的院落,虽然是滴水成冰的时候,脸上还被雪花打着,但心里装着无限的愉悦,感到整个世界充满了温暖。先贴街门,再贴院内东西屋,最后是堂屋。然后还要在每个春联的眉上和横批上分别贴上两到三张“花纸”。“花纸”是我奶奶自己剪的剪纸,有浅红、浅绿、浅黄三种颜色,像筷筒子大小的长方形, 每个“花纸”有公鸡、兔子、老鼠、石榴、花卉等图案。贴完“花纸”才觉得更丰富,更热闹。最后是贴“春”字。院子里有一棵和我父亲年龄差不多的大槐树,必须贴上一个“春”字,影壁墙上贴一个“春”字,水缸上,甚至独轮车上也要贴一个,直到把所有的“春”字贴完为止。
贴春联意境,甚至成为我的一个心灵的港湾。1979年秋,我以优异的成绩被远近闻名的永年二中录取,还被分到重点班。正当我沉浸在喜悦氛围之中时,不到一周,学校却重新考试“数理化”(抛开语文、政治)并以此成绩调整班次。我被调到普通班(到高二又调到中班),这使我感到莫大的不公,因为语文、政治是我的强项。为此,我颇有情绪,学习成绩也受到影响。在一个冬日,老师在讲台上讲课,我的思绪早已飞到故乡的童年的贴春联的意境中。我重新拾起小时候画画的嗜好,在作业本上画起了故乡春节贴春联的情景来。画中有堂屋、西屋、东屋,还有老槐树、水缸、独轮车,更有洁白的雪、寂静的院,到处贴满春联、春字........。我知道,那是想逃避什么,是朱自清写《荷塘月色》时的心境。但是,那白雪映衬下的贴着火红春联的寂静如昨的故园,至今是我魂牵梦绕的灵魂的港湾。可惜,那幅充满温暖的《春联下的家园图》没有保留下来,是个遗憾。

赏春联
贴上春联,第二天就是春节。小孩子跟着大人挨家挨户去给长辈拜年。每到一家,都会注意到人家的春联。有:“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这都来自毛泽东的诗词。还有带着明显时代色彩的:“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战天斗地学大寨,快马加鞭赶昔阳”。还有一次,正赶上在县检察院工作的三叔回家过年,三叔给街门写过一副对联,至今我还清清楚楚记得:“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出自毛泽东的题词)。现在的年轻人可能难于理解这些春联的主题,但这是那个年代特有的文化印记。至于“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这样的春联,在那个时代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而我最喜欢这样的春联:“冰消河北岸,花发树南枝”,对仗工整,富有科学道理,预示着春天很快就要到来了。
春联(广义概念也叫对联、楹联),是一种古老的汉文化,源于古代的“桃符”。据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敦煌遗书记载:公元723年唐人刘邱子撰写的“三阳始布,四序初开”,是最早的春联记载,较之《辞海》记载的五代后蜀主孟昶在寝门桃符板上的题词“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还早240年。作为春联,在我国宋代开始发展,明代盛行。
春联,有诸多讲究。在内容上,要抒发美好愿望,要积极健康,欢乐祥和。春联分上下联和横批,上下联之间,必须讲究对仗工整、平仄规律。对仗,要求上下联字数相等、词性相同、词义相关(相对或相反)。平仄规律,一般要求是按照平声韵,上联尾字为仄,下联尾字为平(当然也有例外)。
我参加工作后,曾经要求单位的一个师傅给我写一副春联,内容是我指定的(毛泽东《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诗句):“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贴出来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但现在想起来,这虽然体现了我的个性愿望,但依照对仗要求,则不能算是合格的春联。 “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这本来是副挺好的春联,但古时候有一个人为了表示孝顺母亲,就让先生将上联的“人”字改为“娘”,先生告诉他对联讲究对仗,上联有“娘”,下联就应该有“爹”,最后就成了:“天增岁月娘增寿,春满乾坤爹满门”。

在上下联之间,如果虽然字数相等但词义无关,也不能算是春联。比如像侯宝林相声里讽刺的一个没有学问却附庸风雅的诗人作的诗:“胆大包天不可欺,张飞喝断当阳桥。虽然不是好买卖,一日夫妻百日恩。”这四句之间是不成对仗也毫无关联的,不能成为诗,当然也不能成为对联,却是极好的相声段子,据说毛主席听了笑得弯下了腰。还有,如果仅讲究对仗,上下联之间甚至本联之内文理不同,也会闹出笑话。比如“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这本来是在民间流传甚广的写给灶王爷的对联,但在马三立相声里,捧哏的赵佩茹一个字一个字蹦出上联:“上、天、言(盐)好、事(士)”,马三立也一个字一个字对下联:“下、地、醋、逮(歹)、炮”。观众哈哈大笑。
我们村也发生过上下联贴错了的事:“五湖四海皆春色,多积肥五谷丰登。”虽然字数相同,但怎么看怎么别扭。这不是先生写错了,而是家里没有一个文化人,贴的时候自己搞乱了。
短句对联尚好办,长对联也要遵循对仗规律,就有点难度了。还是在《对联》这段相声中,赵佩茹出了十八字的上联:“空树藏孔孔进窟窿窟窿孔孔出窟窿窟窿空",马三立答对:“日吧嗒哐哗啦喀嚓扑通哎哟噗噗噗滋滋滋”,也是十八个字。马三立还有详细解释:“日吧嗒”——一只屎壳郎撞我家纱窗上了,“哐哗啦”一一我一害怕把茶杯淬了,“喀嚓”——把沙锅砸了,“扑通”——我从炕上掉地下了,“哎哟”——硌着我腰了,“噗噗噗”——我摔出仨屁,“滋滋滋”——压死一只耗子。这段相声告诉大家,至少上下联字数相等这一要求在对联中是一种铁律(至于词性词义是否相同相关则就不管了)。每当回味马三立的相声,我心中就充满了愉悦与温暖。扯远了。

为什么那个年代故乡的春联会给我留下温暖的记忆?我们希望回到那个年代吗?这个问题我探究了好久才明白,是因为那年代物质和文化生活太贫乏了,是因为春联带给我们的短暂而温暖日子是由无边的文化贫瘠的日子所承载的。正如我为什么唯独赞美在村西的那棵遗世独立而雪花怒放的杜梨树而不赞美承载它的那无边旷野一样。
2021年1月6日 邯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