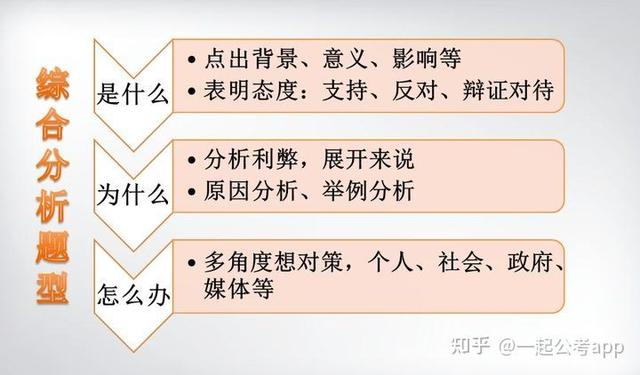母亲对于自己当年第一天去哈尔滨啤酒厂上班所经历的事情仍记忆犹新,她在回忆时写的文字也比前几章要多一些,记述得也比较清楚,还挺生动的。下面就是母亲写的原文:
今天是我上班的第一天(1960年4月6日,这个日子我记得很清楚)。上午8点,我仍去人事股。进到办公室,还没容等我开口,就见一位30多岁的大姐忙站起来问我:“你是昨天报到的吧?”我说:“是的”。她又说:“你就在我们这里上班吧。欢迎你!”随后,她就给我介绍办公室里的其他人员。

1960年夏,母亲(16岁)摄于哈尔滨
有一位叫徐文章的同志,人们都叫他徐老师;还有一位叫李全孝的同志,还有一位是李股长(这位李股长的名字我已记不清了)。刚才这位大姐姓唐,叫唐桂兰,是人事股的股长。我就随着唐大姐的介绍,逐一地向其他几位打招呼。之后,唐大姐说:“你先熟悉一下周围的环境吧。”

当时的哈尔滨啤酒厂人事教育股股长唐桂兰(此照片是唐股长在1960年12月10日赠给母亲的,母亲珍藏至今)
临近中午的时候,有一位小姐姐突然来找我,叫我到他们那里去,我就跟着她去了。
随后,她把我带到了工会办公室。我看见在办公桌旁坐着一位身材高大的男人。那个小姐姐向我介绍说:“这是咱们的工会主席,郭主席。”她又告诉我,她叫陶淑清,是哈尔滨人,她家离工厂很近。她还亲切地对我说:“你就叫我小陶吧!我叫你小苏子!”(我母亲姓苏)

这一座连体建筑是啤酒厂原工会和动力车间办公室,左侧的小办公室就是工会,母亲当年的办公桌就靠着窗子。
母亲接着又写道:这位郭主席是山东人,他正直、爽快、对人很好。郭主席随后告诉我,以后我就在工会工作了。
——最初看到母亲写到这里,我有点疑惑:人事股的那位唐股长不是让我母亲在人事股工作吗?怎么又被拉到工会办公室工作了?我就问母亲这是怎么一回事。母亲说,当时她也不知道。后来她猜测,很可能是工会缺人,得知人事股新来了一个女孩子,就把她要过去了。
母亲接着写道:
过了一会儿,郭主席从外面拿来一张报纸,上面有一段材料,让我先看看,然后广播一下。扩音机就在工会办公室里。
我一听可吓坏了,迟疑了一下说:“我说不好普通话,一口老呔儿味啊(旧时,人们称冀东一带的昌黎、滦南、滦县、乐亭、唐海人为老呔儿,我们这五个县的人性格相近、习俗相同、语音几乎是一样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我们乐亭人说话的语音,我们说话就如同半吟半唱,尾音长而婉转,人们称我们的口音为老呔话。外地人往往一听我们说话,就会被逗得哈哈大笑,觉得我们说话的发音很有意思。)”
母亲接着写道:
我又对工会主席说:“再说了,这个广播用的机子我也不会用啊。”
郭主席说:“我把扩音机给你打开。我们就是要听听你的声音。”
既然郭主席都这么说了,我也不能再推辞了,我就说:“那、那好吧。你把机子给我弄好,我就照您的吩咐念吧。”
这时一旁的小陶也安慰我说:“别紧张,念吧!我去食堂给咱俩打饭。”
随后,郭主席也走了,因为到了午饭的时间。
此时,办公室里只剩我一个人了。没办法,我只能是硬着头皮念了。我尽量让自己的口音标准一点,但还是乡音难改。最后不管怎么说,我还是把那段材料坚持念完了。

厂里的广播员(照片源自网络)
不一会儿,小陶用饭盆把饭打回来了。她一进门,就笑得喘不上气来,说:“你可把我逗死了!全厂都是你的声音!食堂吃饭的人们乐得都吃不了饭了!都说,这声音一听就是个小女孩,她的口音太有意思了!——还挺好听的!就让她天天给我们广播吧!”

在职工食堂打饭(照片源自网络)
小陶还说,食堂里有两位做饭的老师傅,都是河北人,一个是保定的,一个就是我们乐亭人。他们对小陶说:你明天把她带过来吃饭,我们要见见这个小老乡,这是我们家乡的亲人啊!一听她的声音我们就感到亲切,我们很想见见她。

职工食堂里的师傅们(照片源自网络)
小陶又对我说:“你真是福大呀,食堂半年都没吃煎饼了,今天竟然有煎饼!还第一次吃西葫芦炒粉条!”我也觉得很新鲜,那时我们老家还没有西葫芦这种蔬菜。

西葫芦炒粉条
我第一天上班就是在工会办公室吃的饭,都是小陶姐给我买的。因为我刚到哈尔滨,还没有办临时户口,所以厂里暂时不能发给我饭票。当时我心想:等我的饭票发到手,我就给小陶姐打饭。
这一天我很高兴,而且在工会还有一个小姐姐,这太好了!她喜欢我,我更喜欢她。小陶人好,话不多,对我就像大姐姐一样。——我好开心啊!

1961年7月1日,母亲(17岁)摄于哈尔滨
——以上就是我们母亲所写的原文,我也是边打字边笑。似乎看到了一个懵懵懂懂的女孩子,既高兴又好奇地走进啤酒厂,东看一眼西瞄一下,既好奇又小心。而随后她遇到的每一个人都对她很热情、很友好,而且还都很关爱她。她的紧张感就一下子消除了,觉得踏实、亲切、满足,还暗自为自己感到庆幸。

第一天进厂上班(图片源自网络)
而接下来,那位工会郭主席让她在扩音机上念报纸,她又为难又无奈,但还是硬着头皮读完了,估计脑门子上也冒汗了。
而小陶姐打饭回来,一进门就笑得直不起腰来,告诉她,全厂的人听了她的声音都乐得吃不下饭了。——母亲当时肯定是有点不好意思了,自己也是哭笑不得。
可吃到了煎饼和西葫芦炒粉条,她又觉得很幸福,很满足。
上班第一天就遇到了同一个办公室的年龄相仿小陶姐姐,而且这个小姐姐还很关心她,她也很喜欢这个小姐姐,她当然很高兴了。所以,母亲在本章的最后一句话就是:好开心啊!
此时,我似乎看到了16岁的母亲高兴地要跳起来,或高兴地哼唱着歌儿要在原地转几个圈儿。——现在,在我这个50岁的儿子的眼里,文中的母亲就是一个孩子,一个对即将展开的新生活充满无限遐想的女孩子。

1961年6月25日,母亲(后排左二)与啤酒厂的姐妹们摄于哈尔滨兆麟公园
当年母亲到了哈尔滨,所碰到的人、遇到的事,总是让她感到惊喜而温暖。能够进入哈尔滨啤酒厂工作就让她够高兴的了,而且令她没想到的是,上班第一天就被留在了人事股工作,不久又被厂里的工会要过去了——这样就不用下车间干活了。这是多么好的事情啊!
母亲身高大约1.65米,看她在哈尔滨时的照片,我感觉母亲年轻时还挺好看的。虽然母亲也就是初中一年级的文化水平,但她的字却写得挺漂亮的。估计母亲报到的时候,人事股的同志对她很满意,加之母亲年龄又小,也挺招人喜欢的,所以就想把她留在人事股。

1960年夏,母亲(16岁)摄于哈尔滨
但是,她很快就被工会要走了。后来母亲还被厂里派到哈尔滨轻工业产品展览会上,作为啤酒厂的解说员向参观的人们介绍哈尔滨啤酒。之后,她又回到了人事股。看来,母亲当时年纪虽小,但应该是挺中用的。

坐在办公桌前的姑娘(照片源自网络)
至于她上班第一天广播的事情,我看了她写的这段情节也感到挺逗乐的,但也有点奇怪,我就问母亲:“当时为什么让你广播啊?当时厂里没有播音员吗?”
母亲说,她后来才知道,厂里广播的事情都是由工会负责的,也不是天天都定时广播,就是隔三差五地广播一次。当时的广播员生孩子,在家休产假了,所以有时候就让那个小陶姐广播。可能工会的郭主席也想让母亲试一试,看她行不行。结果,母亲把全厂人逗得都吃不下饭了,后来也就没让她再广播。
但是通过这次广播,却让厂里的很多人知道了母亲这个“小老呔儿”,尤其是食堂的两个河北老乡,他们以后对母亲格外照顾。
——母亲从进厂的第一天就很开心,很高兴。

1961年6月25日,母亲(右)与好友张淑媛(河北人)摄于哈尔滨兆麟公园

我与母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