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齐白石:一息尚存要读书
二十四史之中,《元史》修得太粗糙,《明史》又夹带了太多的私货,有二十五史之称的《清史稿》,更是等而下之,故原本均不足观。老人家就曾有评判:“《明史》我看了最生气。明朝除了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不识字的两个皇帝搞得比较好,明武宗、明英宗还稍好些以外,其余的都不好,尽做坏事。”
《明史》虽然不佳,但也并不能表明朝的历史就不精彩。同样的故事,能否吸粉,最终还得看这故事是由谁来说。比如,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就比陈寿的《三国志》更拉风,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比《明史》畅销得多。现在而今眼目下,还有几人愿意凭一部《明史》来对明朝历史来一番盲人摸象般的探索呢?
幸好有当年明月的寓教于乐。
虽然神圣罗马的查理曼皇帝早就说过:“学会第二种语言,就拥有了第二个灵魂”,但还得等当年明月翻出了明末农民军与关宁铁骑对砍时鸡同鸭讲的精彩段落,才让我等深刻理解了学习语言的重大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很久以前,我以为所谓战争,大都是你死我活,上了战场,管你七大姑八大姨,都往死里打,特别是明末,但凡开打,就当不共戴天,不共戴地,不共戴地球,打死了算。
后研读历史多年,方才知道,以上皆为忽悠是也。
按史料的说法,当时的作战场景大致如下:
比如一支官军跟民军相遇,先不动手,喊话,喊来喊去,就开始聊天,聊得差不多,民军就开始丢东西,比如牲口,粮食等等,然后就退,等退得差不多了,官军就上前,捡东西,捡得差不多,就回家睡觉,然后打个报告给朝廷,说歼敌多少多少,请求赏赐云云。
应该肯定的是,在当时,有这种行为的官军,只占绝大多数,认认真真打仗的,只占极少数,所谓“抛生口,弃辎重,即纵之去”。
现象也好理解,因为当时闹事的,大都是西北一带人,而当兵的,也大都是关中人,双方语言相通,说起来都是老乡,反正给政府干活,政府也不发工资(欠饷),即使发了工资,都没必要玩命,这么打仗,非但能领工资,还能捞点外快,最后回去了还能领赏,非常有利于创收。在史料中,这种战斗方式有个专用名词:打活仗。
因为活仗好打,且经济效益丰富,所以大家都喜欢打,打来打去,敌人越打越多,局势越来越恶化,直到关宁铁骑的到来。
其实关宁铁骑的人数没多少,我算了一下,入关作战的加起来,也就五千来人,卢象升、洪承畴手下最能打的,基本就是这些人,最厉害的几位头领,都是被他们打下去的。
之所以能打,有两个原因,首先,这帮人在辽东作战,战斗经验丰富,而且装备很好,每人均配有三眼火铳,且擅长使用突袭战术,冲入敌阵,势不可挡。
而第二个原因,相当地搞笑,却又相当地真实。
我说过,每次打仗时,民军都要喊话,所谓喊话,无非就是谈条件,我给你多少钱,你就放我走,谈妥了就撤,谈不妥再打。
但每次遇到关宁铁骑,喊话都是没用的,经常是话没喊完,就冲过来了,完全不受收买,忠于职守。
我此前曾以为,如此尽忠职守,是因为他们很有职业道德,后来看的书多了才明白,这是个误会,套用史料上的话,是“边军无通言语,逢贼即杀”,意思是,辽东军听不懂西北方言,喊话也听不懂,所以见了就砍。
所以我一直认为,多学点语言,是用得着的。
高迎祥就是吃了语言的亏,估计是屡次喊话没成,也没机会表达自己的诚意,所以被人穷追猛打了几个月,也没接上头。
精辟,透彻!
江湖可不只是打打杀杀呀,电视剧《少帅》里的张作霖不是曾经如此教诲小六子么——“江湖是什么?江湖就是人情世故啊!”
欲论人情事故,倘若彼此语言不同,如何能称呢?相较而言,李自成的运气要比老闯王高迎祥好些,他的部队在潼关南原遭遇孙传庭、洪承畴与贺人龙、曹变蛟等的围追堵截时,幸好与一路紧追而来的贺人龙的陕军还能打上乡谈,对此情景,在姚雪垠先生的长篇小说里,有相关精彩的描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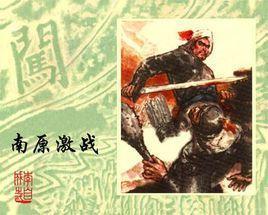
连环画《李自成》之“南原激战”
贺人龙立马阵前,破口大骂。他仗恃人多,又乘着酒力,简直不把田见秀等放在眼里。田见秀正同郝摇旗商议如何出战,贺金龙飞马来到。他把闯王的计策说出以后,郝摇旗还有点怀疑,而田见秀主意已定,说:“摇旗,就用闯王的计策吧,目前咱们倘若能不损伤人马取胜,就是上策。”他随即用鞭子向小松林中一指,对贺金龙说,“老弟,令侄贺国英在那里绑着,你去做个人情放他回去吧。”
田见秀把主力凭险埋伏,只派出两百名骑兵在小山前一字儿排开,叫郝摇旗和几位战将隐藏在这一排骑兵背后,他自己立马在大旗下边。贺人龙看见田见秀的人马如此单薄,十分轻视,挥剑跃马,直对田见秀奔来,大声喝道:“田见秀,赶快投降!”田见秀只带了几名亲兵,态度从容,缓辔出阵,拱拱手,面带微笑说:“贺将军,我有几句话想与将军一谈,谈过后再同将军见个高下。”
“好,有话快说!”
“将军是米脂人,与我们李闯王同乡同里,应有同乡情谊,何苦逼人太甚?”
“呸!我是朝廷大将,你们都是流贼。我是为朝廷剿灭流贼,岂能管什么同乡情谊!”“将军出身穷秀才,只因同义军作战有功,不满十年,升至大将。如果起义军被剿灭,以后就没有立功机会。将军平时带兵不严,所到之处,民怨沸腾。一旦义军战败,将军对朝廷已无用处,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时候就要到来。那时将军不惟无处立功,恐怕朝廷还要治你扰害百姓、杀良冒功之罪。因深知将军性情爽快,故敢冒昧直言,还请将军三思。”
贺人龙心里说:“怪道都说田见秀在贼中很受尊重,果然有一套子!”他觉得田见秀说的话不无道理,有些话自己在平日也同样想过。但是,他没忘自己是朝廷大将,对田见秀大声喝道:“休得乱说!赶快下马投降,免得我一剑刺死!”
田见秀毫不在乎,接着说:“再说,将军即使不讲乡谊,也应该讲讲族谊和戚谊。贵宗族参加起义的人很多,十三家里边就有两家的首领出在你们贺家。像赫赫有名的革里眼贺一龙是将军族弟,左金王贺锦是将军族侄,他们如今都在河南和湖广一带。我这里也有将军的近族和亲戚不少,他们都常想同将军一见。我田某决不投降,将军休作此想。等贵本家和令亲戚同将军见面之后,我愿同将军决一死战。”
田见秀说完话就退后几步。立刻从阵后走出来几十个骑马的将士,为首的一员青年将军在马上向贺人龙欠身作揖,亲热地呼唤说:“四哥!好几年不见面,没想到在这儿看见四哥!”
贺人龙怔了一下,望着来将问:“你是金龙?听说几年前你入了贼伙,还没有死?早该死啦,畜生!”
“别骂,四哥。几年不见,我做梦都在想着四哥。今日乍见面,好歹是你自家门儿里的兄弟,算来才出五服,门头并不远,有什么值得老哥生气的?干吗一见面就吹胡子瞪眼睛?难道咱弟兄们还要拿刀弄杖,杀得你死我活,叫祖宗在地下心中难过?”
“胡说八道!”贺人龙大声说,“你身入贼伙,罪不容诛,我不是你的四哥!看在祖先面上,我不杀你。快叫田见秀跟众贼将前来投降,不要执迷不悟,自走绝路!”
贺金龙从容地笑着说:“四哥把话说岔了。咱两个各行其是,各保其主,我不想劝你投降,你也不要劝我投降。可是兄弟还是兄弟,这是天生的宗族之亲,往上推几代,还是在一个锅里吃饭,同一双爷娘养的哩。四哥可以绝情,不认我这个弟弟,我可不能绝情,跟着四哥学。至于四哥说我身入贼伙,这话也不对。当年朱洪武打江山时,朝廷不也说他是贼么?朝廷无道,民不聊生,人们不造反有什么路走?我要是留在家里做庄稼,四哥,我同我妈怕早就饿死啦。即令我不饿死,也会给官兵炮制死啦。当然,四哥如今混阔啦,小百姓的死活,四哥是不关心的!”
说到这里,贺金龙冷笑一声,接着说:“四哥是穷秀才出身,十年前穷得没办法才投笔从戎,可是四哥,你一升了官就把穷人的苦处完全忘掉,到处纵兵害民,斩良冒功。我这几年跟随着李闯王打富济贫,剿兵救民,活着心安理得,死后见得祖宗。四哥,咱们各自拍拍心口窝里四两肉,你休要责备我啦!”
“混蛋!尽是狗屁!”贺人龙向左右大喝,“快!替我把这个小畜生绑了!”
贺金龙满不在乎地对贺人龙的左右笑着说:“都别动手,我的话还没说完哩。”他又向贺人龙正色说:“四哥,你虽无情,我可有义。我不能跟着你学。你想想,倘若你绑了我向朝廷献功,国英侄儿还能够活得成么?”
“国英在哪里?快快放回来饶你不死!”
“我们义军从来讲义气。大家一听说国英是我的侄儿,已经把他放了。”贺金龙回头向阵上一招手,说:“国英,快回去吧,不要怕四哥责备!”
万人敌从田见秀的大旗后边走出,羞惭地往官军阵上走去。挑战骂阵的时候他是那样的狂暴和无赖,如今却低着头,没精打采。刚才他还在为自己的突然得救而庆幸,如今要他回营,他却感到无脸见人,同时也担心会受责罚。贺人龙背后的将士们看见万人敌被放回来,大出意外,连贺人龙心中也有点吃惊了。
贺金龙趁着这时候丢开了贺人龙,向着人龙手下的两员青年将领亲热地招手叫道:“国贤二侄,国勇六侄,你们近来都好吧?呀,我的天,今日是咱们贺家大团圆!没想到在两军阵前会看见这么多的亲人!”
他把缰绳提一提,想越过贺人龙往前走几步,但是他又怕万一贺人龙翻脸不认亲。于是他没有挪地方,又向贺国贤等一群人招着手儿,笑着说:“来呀,往前来几步,叙叙家常。别害怕,让四哥怪罪我一个人好啦。”
他又看着贺人龙,说:“四哥,你别生气。连朝廷老子还爱他一族一姓,何况咱们!”
跟在贺人龙身后的亲兵爱将,大部分是姓贺的,其余的虽不姓贺,但不是沾亲,便是带故,不然也是同乡或近邻。至于贺国贤和贺国勇的亲兵们也是一样。有人说过这话:如果把贺人龙麾下的老营将士几百口子人加以盘问,都可以找出来亲戚瓜葛,或者是血亲,或者是拐弯抹角的亲戚。按照贺人龙的说法,这是照顾乡亲,也是打不散的子弟兵。照他手下人的说法,这就是俗话所说的“朝里有人好做官”,“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因此,经贺金龙一招呼,大家一拥向前,在两军阵上你呼我叫,纷纷谈话,互相寒暄,争着打听亲故消息。田见秀的骑兵也有许多米脂人,也不时搭腔说话。贺人龙喝禁了自己的将士,但是也明白在这样的情形下很难厮杀。他对田见秀大声说:“田贼,你不敢同我交战,快去叫闯贼前来!”说毕,拨马自去。
贺国贤和贺国勇,以及贺人龙的左右将士,不敢多停留,也跟着去了。但是多数官兵并没跟着走。他们看见上边头头儿走后,越发没有顾忌,同农民军谈话更加亲热。有些不是米脂人的官兵也拉扯陕北延安府同乡关系,互相打听家乡情况,熟人音信。谈了一阵,贺金龙和他的亲兵们把身上的包袱解下来,取出金银、绸缎、首饰和其他贵重东西,分送给本家、亲戚和同乡作为礼物。田见秀也命令手下的将士们搬出来一些值钱的东西,送给乡亲。最后,贺金龙从腰里解下来高夫人给他的那把短剑,交给贺人龙帐下的一名姓贺的小校,说:“这是我三年前打开凤阳皇陵时得的一把宝剑,你看,这剑柄是象牙的,镶着黄金,剑鞘是鲨鱼皮的,镶嵌着黄金、宝石和钿螺。据几位内行看过,说这是宫里边的东西,至少值三百两纹银,务请贤侄费心,替我呈给我四哥,说这是我的一点点小意思,不成敬意。日后遇见更好的宝物,另外孝敬。”姓贺的小校因为已经接受了金龙的礼物,对这件委托满口答应照办,他把短剑拿在手里,笑嘻嘻地打量着,看见剑锋闪着寒光,而剑柄和剑鞘装饰的黄金、宝石和钿螺光彩耀眼,不觉连声叫道:“嘿!嘿!我还是第一次开这个眼界!”一股口水啪哒落下来。
贺金龙赶快从口袋里取出一只金钗,说:“老侄,这个你也收下。”
“不,不。刚才八叔你已经给我不少东西了,哪能再要你的!”
“这不是给你,你收下以后我告诉你。”等到对方把金钗收下,贺金龙接着说,“我知道你已成了家,遇顺便人回家乡时把这只金钗带给你媳妇,就说是我金龙八叔的一点小意思。”
收到礼物的官兵们皆大欢喜,没收到礼物的人们除羡慕外也很欢喜。在一片欢喜的气氛中互相恋恋不舍地道了别,各回本营。田见秀料定贺人龙不会马上对他进攻,立刻又抽出来三百名骑兵交给张世杰和贺金龙率领,往正面战场上支援李过。
贺金龙如不死,日后定是个当政委的好材料。您看,这哪里还是你死我活的战场嘛,分明都搞成了陕西乡党的联谊会了么!可远在北京紫禁城里的崇祯皇帝,哪里能明了个中曲直呢?
您瞅,如此多会一种语言,哪怕只是方言呢,岂止是仅仅“拥有第二灵魂呢”那么简单?有时候,甚至还直接性命攸关呢。朋友,大家都熟知《水浒传》里的郑屠是被鲁达三拳打死的,可我总是怀疑,这郑屠可能死得有些冤枉:人家明明是叫“郑(zhèng)关西”嘛,虽有点僭越,也还不至于冲撞了鲁提辖的门面。可他哪里能料得到,这鲁提辖可能也是因为酒喝得多了的缘故,根本就分不清有鼻音与否,硬是给听成“镇(zhèn)关西”了,这下子可是无意间惹怒了鲁达:
“呸!俺知道那个郑大官人, 却原来是杀猪的郑屠!这个腌臜泼才,投托着俺小种经略 相公门下做个肉铺户,却原来这等欺负人!”
“洒家始投老种经略相公,做到关西五路廉访使,也不枉了叫做‘镇关西’!你是个卖肉的操刀屠户,狗一般的人,也叫做‘镇关西’!”
接下来自然免不了被“踏住胸脯”,还被“那醋钵儿大小拳头扑的只一拳,正打在鼻子上,打得鲜血迸流,鼻子歪在半边,却便似开了个油酱铺,咸的、酸的、辣的一发都滚出来。”
冤枉么,哥!

自称“民间匠人”的戴敦邦先生水浒人物:拳打镇关西。这幡上的“郑屠”二字,有点意思。应该不会这么写吧?
就算是一个馒头也可以引发血案,但这郑屠无论如何也未曾想想像得到,就因普通话没有过关,竟然也会招来杀身之祸。早知如此,当初跟先生学拼音时真应该再上点心才是。
可世上哪有后悔药可吃呢?这不,等郑屠觉悟了正待喊冤,却早已经被鲁提辖“提起拳头来就眼眶际眉梢只一拳,打得眼棱缝裂,乌珠迸出,也似开了个彩帛铺,红的、黑的、紫的都绽将出来”了。
民国时在阎锡山手下混,就有“会说五台话,便把洋刀挎”的说法,而对张作霖的奉军而言,竟然“妈拉个巴子是路条”了。这语言的功效,可谓不可小觑吧?试问,当今高考,当真就可以不考英语了么?我想,如果高迎祥、郑屠等辈能够复活再世,一定会坚决不答应的。
一息尚存要读书啊,同学们!
,




